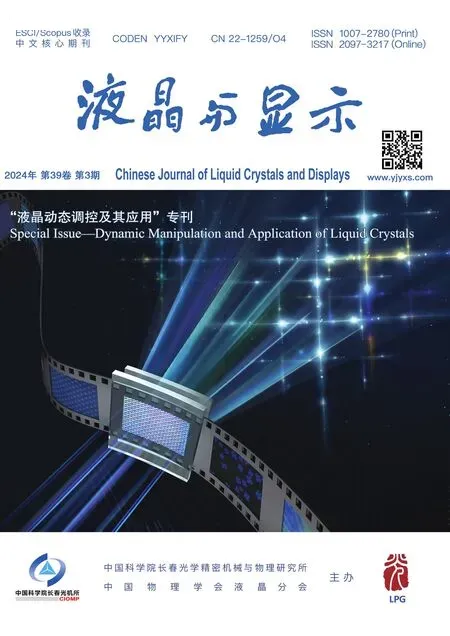藍相液晶對聚集誘導發光分子熒光性能的影響
陳影, 段然, 許子言, 唐瑞琪, 童穎萍, 趙東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化學學院, 北京 100191)
1 引言
藍相液晶由于其高度有序的自組裝三維晶格結構被看作為一種三維光子晶體,具有可見光范圍內的光子帶隙。同時憑借其固有的液晶特性,藍相液晶具有對外部刺激的高度可調諧性,包括其晶格取向[1]、光子帶隙[2]、晶體結構[3]和雙折射在內的性質均可在外場的作用下被調制。基于上述優點,藍相液晶被認為是最有潛力的光子晶體材料之一[4-6]。然而,藍相液晶結構的不穩定導致了其較窄的穩態溫域,嚴重限制了藍相的應用。為拓寬藍相溫域,研究人員提出一系列方法[7-9],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通過聚合物網絡穩定藍相液晶[10],這一方法進一步開拓了藍相液晶在防偽、傳感、刺激響應材料等方面的應用前景[11-14]。在過去的幾年里,研究者們一直在努力研發基于藍相液晶的軟光子晶體材料,旨在創造出能在機械力、電場和光等外部刺激下改變其結構色的智能材料。然而,很少有研究將熒光物質引入藍相液晶體系以拓展其應用領域。此外,熒光強度的可調諧性對于主動發光顯示器等設備至關重要。光子帶隙的調節可以影響熒光發射強度,因此,具有可調諧光子帶隙的藍相液晶在這些應用中展現出巨大的潛力。
傳統的有機發光材料通常在溶液狀態下展現出卓越的發光性能,然而在聚集狀態下,它們的發光性能會急劇下降。這種由聚集引起的發光猝滅現象被稱為聚集誘導猝滅(Aggregation-Caused Quenching, ACQ),這一現象嚴重限制了有機發光材料的實際應用[15]。2001年,唐本忠課題組發現一系列的噻硌分子在溶液狀態下沒有熒光,但在聚集狀態下具有明顯的熒光現象,并將其總結為聚集誘導發光(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AIE)[16]。在稀溶液中,分子幾乎不發光。但當它們聚集在一起時,發光顯著增強,熒光量子產率也有所提高。具有這種性質的發光基團被定義為AIE基元(AIEgen)。一些典型的AIEgen包括四苯基乙稀(Tetraphenylethene,TPE)和六苯基噻硌(Hexaphenylsilole,HPS)等具有特定螺旋槳狀結構的化合物。基于分子內運動受限(Restriction of Intramolecular Motions,RIM)機理[17]及分子結構剛硬化 (Structural Rigidification,SR)原理,AIE體系已得到很大發展。由于AIE材料獨特的聚集發光性質,它們已被廣泛應用于光電器件、生物成像及熒光傳感等領域[18-20]。
一般而言,液晶分子是由剛性單元與柔性基團連接而成,具有AIE性質的發光液晶的設計通常也遵循這一原則。因此,將柔性的烷基鏈或烷氧基鏈與剛性的AIE核連接起來是構建具有AIE性質的發光液晶的有效手段之一[21-23]。在AIE熒光分子中,四苯基乙烯因其較高的固態發光效率和多功能性,已被廣泛用于構建AIE液晶。
我們在前期工作中發現,膽甾相液晶對于AIE分子具有一定的熒光增強作用[24]。基于AIE分子的分子內運動受限機理以及膽甾相液晶和藍相液晶分子排列的相似性,本文將AIE分子TPE-PPE引入藍相液晶體系,系統研究并歸納了手性添加劑含量對藍相液晶相轉變行為和光子帶隙位移情況的影響,同時探究了藍相液晶對TPE-PPE熒光性能的影響,并提出了相關熒光增強效應的假說。這在目前的研究中鮮有報道,對更好地理解藍相液晶以及其相關應用發展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 實驗
2.1 材料及表征設備
本文所采用的材料包括以下成分:二氯甲烷、四氫呋喃、氫氧化鈉溶液以及常見分析純試劑,來自北京化學試劑公司;向列相液晶HTG-135200,由江蘇和成顯示有限公司提供;向列相液晶BHR20400,由北京八億時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可聚合液晶單體C6M,由江蘇和成顯示有限公司提供;手性化合物R811、R5011,由石家莊誠志永華顯示材料有限公司提供;非液晶性可聚合單體1,1,1-三羥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TMPTA),由梯希愛(上海)化成工業發展有限公司提供;光引發劑安息香雙甲醚(I-651),由百靈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聚集誘導發光熒光分子TPE-PPE由本實驗室成員合成。上述材料結構式如圖1所示。

圖1 所用實驗材料的化學結構式Fig.1 Chemical structural formula of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used
實驗采用偏光顯微鏡(Olympus BX51)搭載THMS600型精確控溫冷熱臺,并通過復享光學CMS光譜擴展口搭載光纖光譜儀ULS2048x64,可在精確控溫條件下觀察液晶織構和相變行為并實時測量樣品的反射光譜。熒光光譜儀(FS5)搭載mK2000B型精確控溫冷熱臺,可在精確控溫條件下測量樣品升降溫過程中的熒光光譜。
2.2 樣品制備
取用兩片未經過取向處理的ITO玻璃基板,將導電面相對,中間用兩片厚度約為20 μm的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薄膜隔開,用以控制液晶層厚度。而后用膠水封住邊框并留出液晶灌注口,得到無取向層的空液晶盒。
將混合物材料以一定的比例稱量,放入10 mL玻璃瓶中,加入適量的二氯甲烷溶劑,在超聲波清洗機中超聲10 min,使混合物中分子完全溶解。再將玻璃瓶放入真空干燥箱中干燥10 h,溫度設定為60 ℃,使二氯甲烷完全揮發,最終得到均勻混合的藍相液晶前驅體。
將液晶混合物與液晶盒加熱至清亮點以上溫度,用移液槍或針管取適量液晶混合物涂在液晶盒的灌注口處,液晶混合物將在毛細作用和壓力差的共同作用下被均勻吸入液晶盒中。最后用膠封住灌注口,完成樣品的灌注。
將灌注藍相液晶的液晶盒放置于精確控溫冷熱臺上。首先加熱至清亮點以上的溫度,以3 ℃/min的速度降溫至接近藍相相態的溫度,再以0.1 ℃/min的速率降溫至藍相。待藍相的織構穩定后,在需要的溫度下,以365 nm的紫外點光源照射樣品,光照強度為20 mW/cm2。
3 結果與討論
3.1 不同手性藍相液晶體系的相轉變行為及光子禁帶的溫度依賴性
本實驗采用的聚合物藍相液晶體系由4部分組成:向列相液晶、手性添加劑、液晶性的可聚合單體以及非液晶性的可聚合單體。其中,液晶性的可聚合單體C6M在體系中的作用相當于向列相液晶,可參與藍相雙螺旋柱結構的自組裝。液晶性的可聚合單體不參與雙螺旋柱結構的自組裝,而是位于藍相液晶結構的缺陷處,起到穩定藍相結構并拓寬溫域的作用[25]。由于藍相液晶的晶格常數在數百納米的量級上,與可見光波長相當,因此其可被視為一種三維光子晶體,其反射波長,即光子帶隙(Photonic Bandgap, PBG)可用式(1)表示:
其中:n為平均折射率,a為藍相簡單立方結構或體心立方結構的晶格常數,d為晶面距離,θ為入射光與晶面[hkl]之間的角度,h、k、l為米勒常數。
在藍相液晶體系中,手性添加劑是影響其光子帶隙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制備了具有不同手性添加劑含量的藍相液晶體系,來探究手性添加劑含量對于藍相的相轉變行為和光子帶隙的溫度依賴性的影響。將樣品從略高于清亮點的溫度開始以0.1 ℃/min的速率冷卻,通過偏光顯微鏡實時觀察樣品的相態變化,并通過顯微鏡搭載的光纖光譜儀對樣品的光子帶隙進行同步監測。如表1所示,對于手性添加劑R5011濃度(質量分數)為3.2%、3.4%、3.6%、3.8%的4種藍相液晶預混物,其藍相溫域范圍基本保持一致。

表1 樣品HTG135200/R5011/C6M/TMPTA/TPE-PPE復合體系的成分組成及藍相溫域Tab.1 Composition and blue phase temperature range of sample HTG135200/R5011/C6M/TMPTA/TPE-PPE composite system
我們對這一系列藍相復合物體系的織構及反射性質分別進行討論。其中,樣品T8N32的手性添加劑含量(質量分數)為3.2%,隨著溫度的下降,于79.3 ℃進入藍相。藍相Ⅲ在光學織構上顯示出如同烏云狀的深色陰影,反射不遵循布拉格定律,反射較弱,在反射圖譜中觀察不到明顯的反射峰。隨著溫度下降,T8N32在78.5 ℃時開始出現藍相Ⅱ的織構,如圖2(a)所示。藍相Ⅱ的反射波長隨溫度的降低逐漸藍移,至77.5 ℃時藍移了約20 nm,同時藍相Ⅰ在此溫度下開始出現,其反射波長約為575 nm,此時藍相Ⅱ與藍相Ⅰ的織構并存。繼續降溫至74.5 ℃時,藍相Ⅱ織構完全消失,藍相Ⅰ較剛出現時略有藍移。由于藍相Ⅱ完全轉化為藍相Ⅰ,藍相Ⅰ的反射強度有了顯著增強。但至藍相結束前的71 ℃時,藍相Ⅰ的反射波長又從564 nm紅移至616 nm,如圖2(b)中紫色曲線所示。

圖2 樣品T8N32: (a) 降溫過程中的POM圖像;(b) 反射波長的溫度依賴性;樣品T8N34: (c) 降溫過程中的POM圖像;(d) 反射波長的溫度依賴性;樣品T8N36: (e) 降溫過程中的POM圖像;(f) 反射波長的溫度依賴性;樣品T8N38: (g) 降溫過程中的POM圖像;(h) 反射波長的溫度依賴性。Fig.2 Sample T8N32: (a) POM images during cooling process; (b)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reflected wavelength;Sample T8N34: (c) POM images during cooling process; (d)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reflected wavelength;Sample T8N36: (e) POM images during cooling process;(f)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reflected wavelength;Sample T8N38: (g) POM images during cooling process; (h)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reflected wavelength.
樣品T8N34的手性添加劑含量(質量分數)為3.4%,如圖2(c)和(d)所示,其藍相Ⅱ織構于77.6 ℃時出現,此時反射波長約為470 nm。繼續降溫至74 ℃時,反射波長輕微藍移至452 nm,同時在該溫度下藍相Ⅰ出現,其反射波長位于約520 nm處。隨著溫度持續降低,藍相Ⅱ織構在72.5 ℃時消失。至70.5 ℃時,藍相Ⅰ的光子帶隙從531 nm位移至573 nm。
兩種樣品對比可以發現,系統手性的增加使得藍相Ⅰ出現的溫度降低,但對藍相Ⅱ的存在溫域無明顯影響,藍相Ⅱ的反射波長在其存在溫域內有小范圍藍移,這可能與手性添加劑的螺旋扭曲力(Helical Twisting Power,HTP) 隨溫度變化的依賴性有關。隨著溫度降低,手性添加劑R5011的螺旋扭曲力逐漸增大,導致藍相晶格常數減小,進而使反射波長發生藍移。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兩個體系在藍相結束前的較窄溫度區間內均出現了藍相Ⅰ對應光子帶隙紅移的現象,這可能要歸因于降溫過程中藍相Ⅰ的晶格結構產生的形變。由于此時體系內僅存在藍相Ⅰ的結構,隨著溫度降低,其晶格常數增大,導致反射波長紅移。
對于樣品T8N36,當系統中手性添加劑質量分數升至3.6%時,如圖2(e)、(f)所示,在整個降溫過程中,藍相Ⅱ織構于76.8 ℃時出現,反射波長約為440 nm,至72.5 ℃時略有藍移,約為425 nm,并且藍相Ⅰ在該溫度下出現,其反射波長約為478 nm。在71.7 ℃時,藍相Ⅱ消失,藍相Ⅰ的反射波長隨著溫度降低逐漸紅移,在70 ℃時約為525 nm,較剛出現時紅移了約50 nm。在70 ℃后,其反射波長略有紅移,但趨勢較之前已大為減緩。
樣品T8N38的手性添加劑含量(質量分數)提升到了3.8%,從圖2(g)、(h)可以看到,其藍相體系的相轉變行為出現了較大變化。在降溫過程中,進入藍相溫域后并未觀察到藍相Ⅱ的織構,至73.0 ℃時在POM圖像中出現了藍相Ⅰ的織構,并且在反射圖譜中觀察到了對應的反射波長。至藍相溫域結束前,觀察到了藍相Ⅰ反射波長的紅移,這與上述樣品的行為類似。
綜合上述樣品的結果來看,隨著手性添加劑含量的提高,藍相體系的藍相Ⅰ及藍相Ⅱ的反射波長范圍均向短波長方向移動,如圖3所示。此外,當手性添加劑含量提升到一定數值,即體系的手性到達某一值時,會出現由藍相Ⅲ向藍相Ⅰ的直接轉變,而在整個藍相溫域內不出現藍相Ⅱ。

圖3 不同手性添加劑含量的藍相體系對應的藍相Ⅰ及藍相Ⅱ的反射波長的溫度依賴性Fig.3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the reflection wavelength of blue phase Ⅰ and blue phase Ⅱ corresponding to the blue phase system with different chiral dopant
在以往的研究中,關于藍相系統的手性對其相轉變行為和光子禁帶的影響很少被探究,尤其是忽略了手性添加劑的含量對藍相Ⅰ和藍相Ⅱ的相轉變及光子禁帶的影響。實驗發現,具有不同手性添加劑含量的藍相體系,其藍相Ⅱ的存在溫域基本一致。在降溫過程中,其反射帶隙在存在溫域內有約20 nm的藍移。然而,藍相Ⅰ的行為與系統手性大小密切相關。以樣品T8N32為例,在進入藍相溫域僅1.8 ℃后便出現藍相Ⅰ。在降溫過程中,藍相Ⅰ表現出與藍相Ⅱ類似的輕微反射帶隙藍移。但當藍相Ⅱ反射帶隙完全消失,系統中僅存在藍相Ⅰ后,其反射帶隙表現出較大幅度(約50 nm)的紅移。對于其他組分含量相同的藍相體系,手性添加劑的含量影響藍相Ⅰ在整個藍相溫域內出現的溫度。隨著系統手性的增加,藍相Ⅰ出現的溫度降低。當手性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如樣品T8N38,在降溫過程中,系統中不出現藍相Ⅱ,而是直接出現藍相Ⅰ。
3.2 藍相液晶體系對聚集誘導發光分子熒光性能的影響
具有AIE性質的熒光分子TPE-PPE被引入藍相液晶體系,使該體系不僅具有了結構色的特征,同時也獲得了熒光特性。此外,作為四苯基乙烯類熒光分子,TPE-PPE的4個苯環由單鍵連接至中心的乙烯基元上,苯環可以相對乙烯雙鍵旋轉或扭轉,這些分子內旋轉充當了將激發態以非輻射性質衰減至基態的弛豫通道。然而,在聚集態下,上述分子內旋轉被束縛,阻斷了非輻射弛豫通道,從而使得熒光增強。因此,在液晶分子的自組裝結構,尤其是高度扭曲的藍相雙螺旋柱結構中,TPE-PPE可以獲得顯著的熒光增強。此外,TPE-PPE作為具有液晶性的熒光分子,其液晶特性使其與液晶分子的相容性較高,從而在液晶體系中的溶解度較普通熒光分子有所提升。
通過穩態熒光光譜與POM圖像探究了TPEPPE在該藍相液晶體系中的溶解度。如圖4所示,隨著TPE-PPE含量的升高,體系的熒光發射位置基本沒有變化,均位于約500 nm處。此外,當TPE-PPE的質量分數≤1.2%時,體系的熒光強度隨著TPE-PPE的含量增加呈線性增強的趨勢,在TPE-PPE質量分數為1.2%時熒光強度達到最大。當TPE-PPE在體系中的質量分數進一步增加至2%時,體系的熒光強度反而較TPEPPE質量分數為1.2%的體系有所降低。

圖4 (a)具有不同含量(質量分數)TPE-PPE的藍相液晶體系的PL圖譜 (λex=365 nm);(b) TPE-PPE含量(質量分數)與藍相液晶體系熒光強度的關系;(c) 具有不同含量(質量分數)TPE-PPE的藍相液晶體系在365 nm紫外燈下的照片。Fig.4 (a) PL spectra (λex=365 nm) of BPLC system with different content (mass fraction) of TPE-PPE; (b) Relationship between TPE-PPE content (mass fraction)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BPLC system; (c) Photos of BPLC system with different content (mass fraction) of TPE-PPE under 365 nm UV light.
通過圖4(c)可以看出,在TPE-PPE質量分數為2%的熒光圖像中有部分較為明亮的斑點,這與TPE-PPE析出導致的局部熒光強度增強相對應。應該注意的是,結晶后的TPE-PPE雖然具有更高的熒光強度,但并不利于整體熒光強度的提升,反而會導致體系的熒光強度下降。為了探究藍相液晶體系對具有AIE性質的熒光分子熒光性能的影響,我們選擇了0.8%的TPE-PPE摻雜濃度(質量分數)。同時,結合藍相液晶體系的相轉變行為和光子禁帶,對該復合體系的熒光性質進行了綜合研究。
首先,對具有不同含量手性摻雜劑的藍相體系熒光強度進行了探究。當藍相體系中手性添加劑的含量(質量分數)為3.2%時,從圖5(b)可以看到,在85~79 ℃的降溫過程中,體系的熒光強度逐漸增強。這是由于TPE-PPE的熒光強度高度依賴于溫度,隨著溫度的降低,激發電子通過無輻射衰變返回基態的可能性降低,從而導致熒光強度增強。在剛由各向同性相轉變為藍相時,最先出現的是藍相Ⅲ,盡管其沒有形成規則的晶格結構,但相對于各向同性相來說,仍限制了AIE分子的分子內運動,從而具有一定的熒光增強效應。在接下來的降溫過程中,熒光強度呈現逐漸增強的趨勢,但當藍相轉變為膽甾相時出現了熒光強度下降的現象,這可以證明相對于膽甾相來說,藍相的自組裝結構對于該熒光分子的熒光發射有著一定的增強作用。

圖5 樣品T8N32: (a) 不同溫度下的PL光譜;(b) PL強度的溫度依賴性;(c) 77.5 ℃和 (d) 74.5 ℃時的熒光圖譜和反射圖譜 ;(e) 藍相Ⅰ光子帶隙與熒光強度的關系;(f) 降溫過程中藍相Ⅰ和藍相Ⅱ的光子帶隙位置與熒光強度增速 (λex=365 nm)。Fig.5 Sample T8N32: (a) PL spectr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b)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L intensity;Fluorescence and reflection spectra at (c) 77.5 ℃ and (d) 74.5 ℃; (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oton band gap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blue phase Ⅰ;(f) Photon band gap position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growth rate of BP Ⅰand BP Ⅱ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 (λex=365 nm).
如圖5(c)和(d)所示,在77.5 ℃和74.5 ℃時,在熒光圖譜對應的波段觀察到一定的強度降低,并且其兩側熒光強度有一定的增強,此時其光子帶隙分別位于508 nm(藍相Ⅱ)和560 nm(藍相Ⅰ)處。可以看到,藍相液晶體系的光子帶隙對熒光強度有一定的影響。在光子帶隙中心,熒光發射被抑制,而帶隙兩側的熒光強度增強。根據費米定律,自發輻射速率與光子態密度成正比。在光子禁帶的內部,其對應頻率的光子態密度降低,自發輻射速率減緩,導致發光強度降低;在光子禁帶邊緣,由于光子態密度的增加,熒光強度增強。
對于該樣品,其藍相Ⅰ的光子帶隙調諧范圍遠離熒光發射峰,而藍相Ⅱ的光子帶隙出現在熒光發射峰附近,可以觀察到不同相態下光子帶隙對于熒光強度的影響。同時,在降溫過程中,整個藍相溫域內均呈現較高的熒光增速。由于相態重疊溫域較寬,各相態下熒光強度的增速難以進行直觀比較。由圖5(e)和(f)可知,77.5 ℃時藍相Ⅰ出現,其光子禁帶位于熒光發射峰的邊緣,在約76 ℃時熒光增速明顯提高,這可以歸因于光子禁帶對于其邊緣熒光發射的增強效應。可以觀察到,藍相Ⅰ的光子禁帶在570 nm附近體系的熒光強度增速要小于光子禁帶紅移時的增速,也就是說,伴隨著藍相Ⅱ的消失,藍相Ⅰ紅移,體系的熒光強度會有一個明顯的上升。
樣品T8N34在降溫過程中的熒光強度變化與T8N32類似,整體呈現遞增趨勢,如圖6所示。當液晶從藍相轉變為膽甾相時,熒光強度先下降,隨后隨著溫度降低而增強。這表明藍相液晶體系對AIE分子的熒光有增強效應。對于該樣品,藍相Ⅰ和藍相Ⅱ的光子禁帶分別位于熒光發射峰的兩側。由于藍相Ⅱ的光子禁帶位置的熒光發射較弱,因此沒有觀察到明顯的熒光增強或抑制效應。但在穩態熒光圖譜中,可以觀察到藍相Ⅰ的光子禁帶產生的熒光增強或抑制。在藍相溫域內,T8N34的熒光強度增速隨著溫度降低而逐漸提高,見圖6(c),在約76 ℃附近觀察到了與圖5(f)中約77 ℃處類似的熒光強度增速提高,這可能歸因于藍相Ⅱ的出現。較之藍相Ⅲ的雙螺旋柱結構,藍相Ⅱ的由雙螺旋柱進一步自組裝的簡單立方結構對于具有AIE性質的熒光分子的分子內運動有著更強的限制作用,從而其熒光強度增速有一個較為明顯的升高。73 ℃時的熒光增速提高可歸因于藍相Ⅰ的出現。離開藍相Ⅱ溫域后,藍相Ⅰ的光子帶隙紅移,此時熒光強度增速明顯提高。

圖6 樣品T8N34: (a)不同溫度下的PL光譜;(b) PL強度的溫度依賴性;(c) 降溫過程中藍相Ⅰ和藍相Ⅱ的光子帶隙位置與熒光強度增速 (λex=365 nm)。Fig.6 Sample T8N34:(a) PL spectr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b)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L intensity;(c) Photon band gap position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growth rate of BP Ⅰ and BP Ⅱ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 (λex=365 nm).
當體系中手性添加劑濃度(質量分數)增加到3.6%時,藍相Ⅰ的光子帶隙調諧范圍與TPEPPE的熒光發射峰相匹配。從圖7可以看到,在降溫過程中,進入藍相后的熒光增速有明顯的上升;隨后藍相Ⅱ出現,熒光強度增速有所放緩;至藍相Ⅰ出現時,光子帶隙正處于最大熒光發射波長中心,其抑制了熒光強度的繼續增強,整體的熒光強度有一個短暫的平穩階段。由圖7(c)可知,在71 ℃時,藍相Ⅰ的光子帶隙紅移至510 nm,隨后熒光強度增速顯著提高,并且與光子帶隙重疊區域的熒光發射均受到了抑制。同樣,在69.2 ℃時也可以觀察到光子帶隙對于熒光發射的影響。總體來看,藍相Ⅱ階段的熒光強度增速要低于藍相Ⅰ階段。并且在降溫過程中,離開藍相溫域,體系轉變為膽甾相后,熒光強度有一個明顯的下降,隨后緩慢上升。在圖7(d)中,在藍相Ⅱ出現后的約76.2 ℃處,可以觀察到與T8N32和T8N34類似的熒光增速提高。對于該體系,藍相Ⅰ與藍相Ⅱ重疊溫域較窄,在藍相Ⅱ溫域結束前的0.8 ℃時藍相Ⅰ出現并迅速紅移,相對應的熒光強度增速也迅速提高,這與樣品T8N32和T8N34在降溫過程中的熒光行為一致。

圖7 樣品T8N36: (a) 不同溫度下的PL光譜;(b) PL強度的溫度依賴性;(c) 在74.5 ℃時的熒光圖譜和反射圖譜;(d)在降溫過程中藍相Ⅰ和藍相Ⅱ的光子帶隙位置與熒光強度增速 (λex=365 nm)。Fig.7 Sample T8N36: (a) PL spectr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b)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L intensity; (c) Fluorescence spectrum and reflection spectrum at 74.5 ℃; (d) Photon band gap position an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growth rate of BP Ⅰ and BP Ⅱ during cooling process (λex=365 nm).
由圖8可知,當體系中手性添加劑濃度(質量分數)為3.8%時,與手性較低的系統相比,該藍相體系對于TPE-PPE的熒光增強效應減弱了許多,在藍相階段的熒光增速與其余相態下的增速沒有明顯差異,僅在剛進入藍相溫域以及藍相Ⅰ出現時觀察到一定程度的熒光增速提高;并且在離開藍相區間進入膽甾相時,有一定程度的熒光強度下降。

圖8 樣品T8N38: (a) 不同溫度下的PL光譜;(b) PL強度的溫度依賴性 (λex=365 nm)。Fig.8 Sample T8N38: (a) PL spectr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b)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L intensity (λex=365 nm).
為了進一步確認光子帶隙紅移與熒光強度增速的關系,我們研究了另一種溫域較寬的藍相液晶體系BHR20400/R811(表2),并向其中引入0.8%(質量分數)的TPE-PPE。結合穩態熒光光譜與反射圖譜研究了其由各項同性相緩慢降溫至藍相溫域以及膽甾相溫域時的光子帶隙和熒光強度的變化。隨著系統中手性添加劑R811量的增加,藍相溫域有所拓寬,并且整體溫域向室溫方向移動。

表2 樣品BHR20400/R811/TPE-PPE復合體系的成分組成及藍相溫域Tab.2 Composition and blue phase temperature range of sample BHR20400/R811/TPE-PPE composite system
由圖9可以觀察到,R30在進入藍相區間后,其藍相Ⅰ與藍相Ⅱ幾乎同時出現。由于藍相Ⅱ的光子帶隙強度較弱且存在溫域較窄,其對于熒光強度的影響可以忽略。在55 ℃時,藍相Ⅰ的光子帶隙紅移,體系的熒光強度增速有所提高;并且在52.5 ℃時,光子帶隙穩定在約645 nm,熒光增速趨于穩定。在樣品R35中,同樣可以觀察到,在藍相Ⅰ的光子帶隙紅移后,體系的熒光強度增速迅速提高,并且位移幅度大于R35,增速提高的趨勢也更為明顯。

圖9 樣品R30: (a) PL強度的溫度依賴性;(b)在降溫過程中藍相Ⅰ的光子帶隙與其熒光強度增長速率的關系;樣品R35: (c) PL強度的溫度依賴性;(d)在降溫過程中藍相Ⅰ的光子帶隙與其熒光強度增長速率的關系;樣品R8N34: (e) 不同溫度下的PL光譜;(f) PL強度的溫度依賴性 (λex=365 nm)。Fig.9 Sample R30: (a)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L intensity;(b)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oton band gap of BPⅠand its fluorescence intensity growth rate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 Sample R35: (c)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L intensity; (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otonic band gap of BP Ⅰ and the growth rate of its fluorescence intensity during the cooling process;Sample R8N34: (e) PL spectr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f)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PL intensity (λex=365 nm).
最后,通過將傳統ACQ分子R6G引入藍相體系,進一步確認了藍相內的熒光增強來自于熒光分子的AIE性質。基于HTG135200藍相液晶體系,配制了引入R6G的液晶預混物,記為R8N34,其配比與T8N34一致,僅將TPE-PPE替換為了R6G。如圖9(e)和(f)所示,測試了R8N34在降溫過程中的PL光譜,體系的熒光強度與溫度呈線性關系。隨著溫度下降,熒光強度線性增強,在藍相溫域內沒有觀察到熒光增強現象。
由上述內容我們提出假設,如圖10所示,AIE分子部分參與藍相液晶體系的自組裝。參與雙螺旋柱組裝的TPE-PPE分子由于RIM效應,較未參與自組裝的分子,其熒光強度有所提高。同時,藍相的晶格常數增大,表現為光子帶隙的紅移。伴隨著該過程,有更多的TPE-PPE分子參與雙螺旋柱結構的自組裝,進而使得熒光增強。TPE-PPE分子在藍相體系中參與自組裝時,存在對應的光子帶隙范圍。當螺旋扭曲力過大時,藍相的晶格常數較小,使TPE-PPE分子無法參與自組裝,從而使得熒光增強效果不明顯,這在樣品T8N38中得到了體現。

圖10 藍相液晶體系對TPE-PPE的熒光增強效應示意圖Fig.10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luorescence enhancement effect of BPLC system on TPE-PPE
4 結論
本文探究了手性添加劑含量對于藍相液晶體系相轉變行為和光子帶隙位移的影響,及具有不同手性添加劑的藍相液晶體系對于AIE液晶熒光分子TPE-PPE的熒光增強效應。從實驗結果可以得出:一方面,在藍相的自組裝過程中,對于具有不同手性添加劑的體系,藍相Ⅱ的存在溫域基本一致。伴隨降溫過程,在其存在溫域內有著輕微的藍移。隨著系統手性的增加,藍相Ⅰ出現的溫度降低,但當藍相Ⅱ反射帶隙完全消失,系統中僅存在藍相Ⅰ后,其反射帶隙表現出在較窄溫域范圍內較大幅度的紅移。另一方面,藍相液晶體系對TPE-PPE有著一定的熒光增強效應。這是由于藍相液晶高度扭曲的分子排列限制了TPE-PPE的分子內運動,阻斷了非輻射弛豫通道,從而使熒光增強。在整個藍相溫域內,藍相Ⅰ反射帶隙紅移,體系的熒光強度明顯增強。由此我們提出假設,TPE-PPE分子部分參與藍相液晶體系的自組裝。參與雙螺旋柱組裝的TPE-PPE分子由于RIM效應,其熒光強度有所提高。同時,藍相Ⅱ消失后,藍相Ⅰ光子帶隙紅移,即藍相Ⅰ的晶格常數增大,使更多的TPEPPE分子參與雙螺旋柱結構的自組裝,進而體系的熒光發射增強。以上實驗分析為今后聚集誘導發光分子摻雜藍相液晶體系的建立進行了有益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