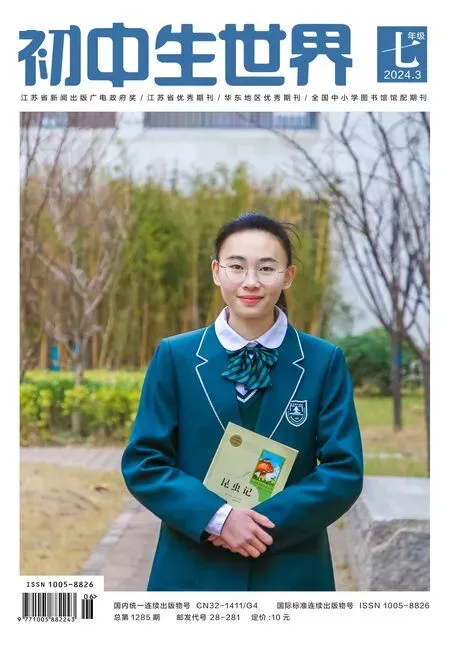中國文化中的獨特“水性”
文/張強
水,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最重要資源,早在中華文明之始,便已進入先民的認知視野。
出土的史前陶器中,瓶、甕、盆是最常見的水器。器身也常能見到水波紋、蒲紋、蛙紋等紋飾,它們既取象于水,又透露出與繁殖、生死相關的抽象意味。
無疑,水作為文化符號,早已與其物質實用性相伴共生。接下來的數千年,水更是全方位滲入中國文化的根莖葉脈,滋養出中國文化的獨特“水性”。
不忘本始的“明水”
先秦時代,祭祀是向神靈表達敬意,維系國家命脈的禮儀活動。《禮記·郊特牲》標舉“明水之尚”,指出“明水”是等級極高的祭品。“明水”,其實就是水的雅稱。
為什么要用水作為代表與至高的神靈溝通?這是出于不忘本始的緣故。禮的最初形態,源于飲食。“污尊而抔飲”生動描繪了人類創始時期飲水之艱難,先民們只能在地上挖泥坑收集雨水,用手掬水飲來維持生存。即便如此,他們仍不忘感恩自然的饋贈,以坑為尊,以水當酒,禮敬自然對人類族群的眷顧。水從食物到祭品,無疑承載了人類虔誠堅韌的最本始品質。所以,用水祭祀,其實是對先民艱苦生活的追憶,而更重要的,是在守護那顆永恒不變的虔誠之心。
水是生命之源,古人不僅早已認知,其中“不忘本始”意義的揭示,更是留給后世頗為珍貴的遺產。
變易與永恒交織的“逝水”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2000 多年前孔子面對泗水時發出的感慨。“逝”,寫出了河水一去不返的自然面貌,也傳達出時光易逝、生命短暫的人生況味。孔子這一臨水之嘆,激發出中國文學中用水來象征人生苦短的傳統。李白曾嘗試跳脫人生無常,但也只能接受“抽刀斷水水更流”的現實。李清照獨上蘭舟,見到“花自飄零水自流”,禁不住感嘆青春易老。
雖然時光如逝水,但是“不舍晝夜”的流淌,卻傳達出鍥而不舍的勃勃動力。變易的另一面,正是那永不停息的永恒。于是,時光易逝的悲情之外,奮斗不止的生命豪情撲面而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這是直面未來的激昂告白;“星漢燦爛,若出其里”,這又是擁抱宇宙的壯闊胸懷。
水將變易與永恒的矛盾之兩面融于一身,顯示出無盡的張力,這正是“上善若水”之道的本有之義。
妙趣萬般的“山水”
魏晉六朝被譽為中國歷史上審美大發現的時代。《文心雕龍》中的一句“老莊告退,山水方滋”,宣告自然山水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水的聲色、氣韻、風姿,無不令人神往。
謝靈運被尊為山水詩鼻祖,他對水的喜愛,溢于言表。“池塘生春草”,水邊的春色,靈動活潑。“云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水天之色澄明如一,鮮亮誘人。王維也是寫水高手,“行至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水汽曼妙無邊,足以物我兩忘;“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水聲悠悠,禪意無限。
不僅水自身的性質備受關注,各種類型的水也紛紛演化成中國詩歌地圖上的各路水系。如“春江”,就有張若虛“何處春江無月明”,蘇軾“春江水暖鴨先知”,寫盡勃然生機。如“西湖”,就有白居易“綠楊陰里白沙堤”的清雅怡人,蘇軾“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嫵媚動人。
對水的種種審美觀照,無疑促成人與自然兩相融合,成見被捐棄,心與物同游,在澄懷中領悟人生、歷史、宇宙真諦,其妙無窮。
從“明水”到“逝水”再到“山水”,水經歷了由物質性向審美性的轉化,這種局面的形成,與水自我更新的文化張力密不可分。而在新時代水文化的發展浪潮中,中國文化的傳統“水性”,必將涓涓不塞、生生不息地澤被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