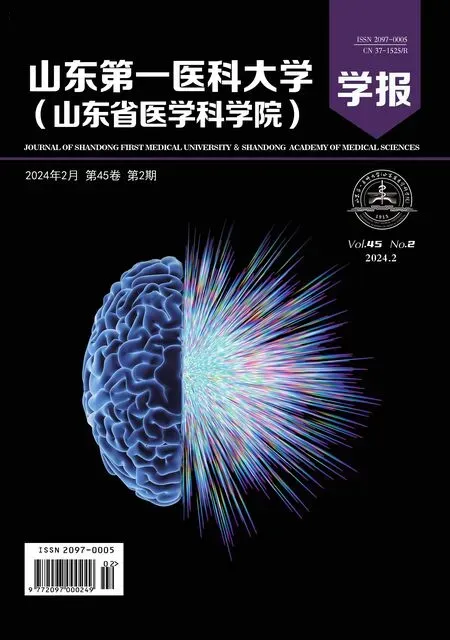旅游與焦慮、抑郁的關聯性研究:一項基于中國老年人的調查
李倩 董華蕾 郭政 侯海峰 王嵬,4
1. 山東第一醫科大學(山東省醫學科學院)公共衛生與健康管理學院,山東 濟南 250117;2. 山東省泰山醫院療養中心,山東 泰安 271099;3. 范德比爾特大學醫學中心流行病學系,美國 田納西州納什維爾 TN37235;4. 伊迪斯科文大學精準健康中心,澳大利亞 郡德勒普市 WA 6027
焦慮癥以焦慮情緒體驗為主要特征,表現為無明確客觀對象的緊張擔心,可同時伴有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癥狀,如頭痛、頭暈、出汗、心悸顫抖、坐立不安等[1]。抑郁癥以心情低落為主要臨床特征,對通常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并伴有無法進行日常活動至少2周,同時可出現思維遲緩、意志活動減退、認知功能受損和軀體癥狀。病情嚴重者可出現自殘甚至自殺行為[2]。
焦慮、抑郁易受外界環境等因素影響,導致病情遷延反復,是全球精神健康相關疾病負擔和全球導致殘疾的主要原因[3-4]。2019年WHO報告顯示,全球約2.8億人患有抑郁癥,3.1億人患焦慮癥[4-5]。2022年中國心理健康調查顯示,在19萬不同年齡段人群中,抑郁檢出率為10.6%,焦慮檢出率為15.8%[6]。截至202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5%[7],針對老年人群開展焦慮和抑郁等常見的精神疾病的預防任務重大,如處理不當將會嚴重危害老年人的身體健康,造成巨大的疾病負擔[4-8]。
旅游,是美化現代生活的一種方式,能提供積極的生活體驗[2]。作為一種多維度的休閑活動,旅游讓游客在享受自然美景愉悅心靈的同時,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精神壓力;還能通過身體活動、社會參與、探求知識等對身體和精神健康形成積極影響[9]。研究表明,參與旅游可以促進老年人的身體健康[10]。相比于年輕人,老年人更有機會和意愿參與旅游[11]。
盡管已經有研究表明,經常參加旅游活動的人比不參加旅游活動的人心理健康狀況更好[12]。但是,旅游和老年人焦慮癥、抑郁癥之間關系的研究尚不透徹,本研究利用2018年的《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數據庫(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相關數據,探索我國年齡在60 ~ 90歲之間的老年人旅游經歷與焦慮癥、抑郁癥之間的關系,為預防或延緩老年人焦慮、抑郁癥狀的發生發展提供參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2018年度CLHLS調查的數據庫。CLHLS是由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研究院組織的老年人追蹤調查,調查范圍覆蓋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2018年總調查對象為15 874例,為確保研究的質量,本研究排除了6 555例在焦慮、抑郁以及旅游經歷變量中存在缺失值或答案為“我不知道∕不知道”的樣本,最終納入9 319例樣本。描述研究對象篩選過程的流程圖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對象選擇流程圖
1.2 調查指標
1.2.1 旅游經歷 數據來自于CLHLS問卷中“近兩年里您外出旅游過多少次?”。為了研究旅游經歷對抑郁和焦慮的影響,對象被分為2組:旅游組(至少有1種旅游經歷)和對照組(沒有旅游經歷)。為進一步分析旅游頻次與抑郁和焦慮的相關關系,按旅游頻次將研究對象分為4組:0次(無旅游經歷)、1次、2次和 ≥ 3次。
1.2.2 抑郁和焦慮 (1)抑郁:本研究采用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10)評估個體抑郁狀況。該量表共10個條目,每個條目有4點分值,范圍從0 ~ 3(0 = 從不∕很少,1 = 有時,2 = 經常,3 = 大多數時間),存在反向計分條目,CESD-10分值范圍0 ~ 30[13]。分值越高表明存在抑郁的可能性越大,總得分 ≥ 10分判定為存在抑郁癥狀,總得分 < 10分則不存在[14]。(2)焦慮:焦慮狀態由廣泛性焦慮癥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進行評估,此量表包括7個條目,每個條目的分值0 ~ 3(0 = 從不,1 = 幾天,2 = 超過一半天,3 = 幾乎每天)。GAD-7的總分范圍為0 ~ 21,大于4的臨界值定義為有焦慮癥狀的個體,5 ~ 9分為輕度焦慮;10 ~ 14分為中度焦慮;≥ 15分為重度焦慮[15-16]。
1.2.3 其他變量 本研究中,可能和抑郁、焦慮存在相關的因素被提取和分類:(1)社會人口學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居住地區、居住模式);(2)生活狀況[當前吸煙、飲酒狀況,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睡眠時間];(3)家庭年收入。
1.3 統計學分析
本研究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率(%)表示,采用卡方檢驗進行率的比較。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檢驗旅游與焦慮和抑郁的相關性;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旅游經歷與抑郁和焦慮的關聯。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和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CI)表示旅游經歷對焦慮和抑郁的影響情況。
建立了3個模型進行敏感性分析,以及對結果的穩健性進行檢驗。(1)模型1:單變量模型;(2)模型2:對社會人口學資料進行矯正;(3)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對吸煙、飲酒、BMI、家庭年收入進行矯正。此外,在模型3中,進行了亞組分析以檢驗旅游經歷與其他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
運用R Studio(版本4.1.0, R Projec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和SPSS 26.0(IBM Corporation, NY, USA)對研究進行了分析。檢驗水準α= 0.05。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基線特征
本次研究共納入年齡在60 ~ 90歲之間的老年人9 319例,男女占比接近(男性:49.5%;女性:50.5%);平均年齡(77.87 ± 7.35)歲,1 554例(16.7%)老年人在過去2年間存在旅游經歷。根據量表判定結果,約有1 113例(11.9%)老年人被判定為存在焦慮癥狀,1 762例(18.9%)存在抑郁癥狀。
另外,接受過教育4 977例(63.4%),居住在城市5 173例(55.5%),和家人一起居住7 346例(79.9%),已婚5 487例(59.4%),不吸煙7 543例(81.8%),不飲酒7 633例(83.1%),BMI正常5 393例(59.0%), 6 199例(67%)的睡眠時間在6 ~ 10 h。研究對象的基線特征見表1。

表1 不同特征老年人旅游經歷比較 [n(%)]
2.2 旅游經歷與焦慮之間的關聯
在1 554例有旅游經歷的老年人中,有134例(8.6%)檢出焦慮癥狀,而沒有旅游經歷的7 765例中有999例(12.9%),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對焦慮狀況和旅游頻次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旅游經歷與焦慮狀況存在相關(r=0.049,P< 0.01)。旅游頻次不同,焦慮的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3),隨著旅游頻次的增加,焦慮的檢出率總體呈現降低趨勢。

表2 不同旅游經歷老年人焦慮、抑郁檢出率[n(%)]

表3 不同旅游頻次老年人焦慮、抑郁檢出率[n(%)]
以是否焦慮(是 = 1,否 = 0)為因變量,旅游經歷(是=1,否=0)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單變量模型中,旅游經歷與焦慮之間存在著顯著關聯,有旅游經歷的老年人焦慮的發生率降低了36%(OR= 0.64, 95%CI: 0.53 ~ 0.77,P< 0.001);模型2對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居住地區、居住模式等協變量進行矯正,在有旅游經歷的人中也觀察到較低的焦慮風險(OR=0.68, 95%CI: 0.55 ~ 0.83,P< 0.001);在調整所有相關協變量(模型3)后,旅游經歷組的焦慮風險也較低(OR= 0.77, 95%CI: 0.59 ~ 0.99,P= 0.04)。
根據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居住地、婚姻狀況、居住模式、吸煙狀況、飲酒狀況、BMI、家庭年收入等進行分層,在模型3的基礎上,發現旅游經歷與焦慮風險的關聯性結果是穩定的(表4,圖2)。分析發現,性別、婚姻狀況、睡眠時間和家庭年收入與旅游經歷存在交互作用(P< 0.05)。發現男性(OR=0.56, 95%CI: 0.36 ~ 0.88,P=0.01)、已婚(OR=0.59, 95%CI: 0.41 ~ 0.83,P< 0.01)、睡眠時間 < 6h(OR= 0.56,95%CI: 0.34 ~ 0.91,P=0.02)、家庭年收入 > 80 000元(OR= 0.09, 95%CI: 0.01 ~ 0.80,P= 0.030)的老年人的焦慮風險較低。在其他亞組中沒有觀察到交互作用(表4)。

表4 旅游經歷和焦慮、抑郁相關因素的亞組分析

圖2 旅游和焦慮亞組分析
2.3 旅游經歷與抑郁之間的關聯
參與過旅游的老年人中,有180例(11.6%)研究對象被檢出抑郁癥狀,無旅游經歷者有1 582例(20.4%)被檢出。有旅游經歷的老年人抑郁檢出率較低,不同旅游經歷抑郁癥狀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表2)。抑郁與旅游頻次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旅游經歷與抑郁狀況之間存在相關(r= 0.087,P< 0.001)。抑郁的檢出率隨著旅游頻次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結果,即抑郁檢出率隨著旅游頻次增加呈現下降趨勢(表3)。
在模型1中,抑郁與旅游經歷之間存在顯著關聯,旅游組老年人抑郁的發生風險較低(OR= 0.51,95%CI: 0.43 ~ 0.60,P< 0.001)。在模型2和模型3對協變量進行矯正后,得到同樣風險降低的結果(模型2:OR= 0.66, 95%CI: 0.55 ~ 0.79,P<0.001;模型3:OR= 0.67, 95%CI: 0.54 ~ 0.85,P< 0.001)(表4)。
在亞組分析中,旅游經歷與抑郁之間的關聯同樣是穩定的(表5,圖3)。旅游經歷與居住地區以及體質指數之間存在交互作用(P< 0.05)。居住在農村(OR= 0.45, 95%CI: 0.29 ~ 0.72,P< 0.01)與BMI正常(OR= 0.63, 95%CI: 0.46 ~ 0.85,P<0.01)的參與者抑郁發生風險較低。交互作用在其他亞組中并未被發現。

圖3 旅游和抑郁亞組分析
3 討論
在本研究中,焦慮癥和抑郁癥的總體檢出率分別為11.9%和18.9%;與沒有旅游經歷的老年人相比,參與過旅游的老年人兩種癥狀的檢出率降低;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在調整了混雜因素后,旅游經歷對焦慮和抑郁存在保護作用,即有旅游經歷的老年人焦慮和抑郁的風險降低。
本研究焦慮和抑郁檢出率與2022年中科院心理所測得的結果有所差距,可能與研究人群選擇不一致有關。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的年齡在60 ~ 90歲之間,而中科院選取的調查人群為成年人。研究表明,旅游可以改善心理健康狀況,緩解負面情緒[17-19]。這與本研究的結論一致,旅游經歷可降低焦慮抑郁的發生風險。
基于旅游經歷與焦慮的關聯,亞組分析中發現,相比于女性參與者,男性焦慮的風險更低,這與目前的研究現狀是一致的[20]。同時,已婚老年人,相較于未婚和喪偶的參與者,風險也較低,這可以解釋為,已婚老人有伴侶的陪伴,有更多的機會與人交流,減少焦慮的可能性。睡覺時間 < 6 h在本研究中被認為可以降低焦慮的風險,但有研究表明,睡眠時間 < 7 h會增加焦慮的發病風險[21]。睡眠時間對于抑郁的作用呈現相反的結果可能與自變量的選取有關,本研究自變量為旅游經歷,睡眠時間作為協變量進行矯正,與睡眠時間為自變量的研究可能存在差異。在本研究中,家庭年收入 >80 000元被認為是焦慮的保護因素,符合低收入水平被認為是焦慮的危險因素的研究結果[22]。基于旅游經歷與抑郁的亞組分析中,本研究發現居住在農村的老年人患抑郁的風險較低,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相同[23]。BMI對抑郁的影響與現有研究存在差異,現有研究顯示,超重和肥胖相比BMI正常的人群對抑郁有保護作用[24]。但本研究顯示,正常組老年人的抑郁風險較低,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與健康生活方式、研究對象的差異有關。
自然旅游是現代旅游的主要組成部分,訪問自然景觀,體驗風土人情,可以減輕壓力并保持愉快的精神狀態[25]。作為一種多元的身體活動,旅游對機體的健康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參與旅游,能體驗不一樣的風土人情,增長見識,放松身心,激發樂觀和愉快的情緒,這對緩解焦慮、抑郁有重要作用。
旅游活動中,老年人可以在戶外進行適度身體活動。身體活動對心理健康有積極影響,能有效減少不良結果[26-27]。參與旅游,在體驗自然、享受風情文化的同時,會增加身體活動量,能有效調動身體機能,進而改善心理健康,緩解焦慮抑郁狀況[28-29]。
與長時間在室內生活相比,在旅途中,能接觸到更多的陽光。研究表明,陽光可以促進血清素釋放,緩解壓力,有助于改善心情[30]。陽光還能促進血液循環,增加免疫功能,調節中樞神經,使人體感到舒適,這對防止焦慮和抑郁有重要作用[19]。
社交范圍小、社交頻率低、自我孤立、社會認知失調是老年群體普遍存在的現象,會導致老年人孤獨,自我封閉,過分關注自我,進而增加老年人抑郁、焦慮的患病概率[31-34]。旅游可以增加社會參與度。旅游為老年人提供與子女、與同齡人乃至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交流的機會,增加了社交頻率和范圍,進而改善心理健康[35]。同時,與子女之間良好的旅游體驗會改善家庭氛圍,良好的家庭氛圍能有效防止老年抑郁狀態的產生[36]。參與旅游可以打破老年人封閉在日常家庭中的界限,還能減少過度關注自我的不良情緒狀態。研究認為,行為的改變會導致不良認知狀態的變化,進而緩解或消除不良情緒,改善焦慮和抑郁狀況[37-38]。
本研究基于CLHLS的數據,在老年群體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焦慮、抑郁癥狀的檢出結果并非明確的臨床診斷,而是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可能會存在夸大事實的情況,增加陽性檢出數量;其次,旅游體驗的數據較為單一(缺乏旅游類型、旅游長度等數據),在進行深入探索方面存在困難;第三,盡管設立了多變量模型來矯正旅游經歷對焦慮、抑郁的影響,但仍舊存在其余混雜因素無法被控制。因此,基于目前數據的現狀,旅游經歷對焦慮、抑郁的影響,未來仍需要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旅游經歷與焦慮、抑郁存在著顯著關聯,有旅游經歷的老年人焦慮、抑郁癥狀的發生風險降低。在焦慮和抑郁患病率居高不下的現代社會,旅游經歷可以被認為是消解現代人精神危機,增進健康的重要途經。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