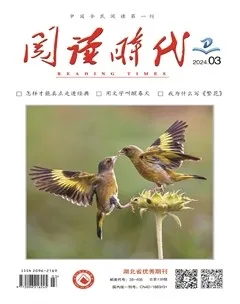舊書(shū)碎事
陶靈
書(shū)不是用來(lái)收藏的。至少我是這樣認(rèn)為。
有次在舊書(shū)網(wǎng)上淘了一本書(shū),店主很負(fù)責(zé),打來(lái)長(zhǎng)途電話說(shuō):“剛準(zhǔn)備發(fā)貨時(shí),發(fā)現(xiàn)書(shū)上有水漬,如果不要,可退錢給你。”我回答,只要不影響閱讀就行。
購(gòu)《費(fèi)拉爾手稿》時(shí),我選了一本價(jià)格十元的,沒(méi)想到這么便宜。店主很快發(fā)來(lái)消息,說(shuō)是掃描的電子版。更好,連郵寄時(shí)間都免了,他用電子郵件發(fā)給我,馬上就能讀。
舊書(shū)網(wǎng)上的書(shū),都有品相標(biāo)注,同一種,往往品相越好越貴。我每次搜索出書(shū)名后,直接點(diǎn)擊從低到高的價(jià)格排序方式,一目了然,再選價(jià)格最低的那本。舊書(shū)郵寄費(fèi)一般由讀者付,我只選掛號(hào)印刷品方式,便宜。有時(shí)店主懶得上郵局寄,故意把這項(xiàng)價(jià)格定得比快遞還高,或者干脆不設(shè)這項(xiàng),讓你選不成(舊書(shū)店主告訴我的)。發(fā)快遞是上門(mén)取件,或就近到菜鳥(niǎo)驛站去寄,便捷。大宗業(yè)務(wù)還可講價(jià)。但店主并不把優(yōu)惠讓給讀者,自己賺價(jià)差。
也有店主十分愿意寄掛號(hào)印刷品,是因?yàn)樗苜I到大量帶郵資的舊“賀年封”或“首日封”“紀(jì)念封”,每個(gè)只要幾角錢,帶的郵資最高可到九元。如果“帶資封”裝不下一本書(shū),就拆開(kāi)中縫,另用紙加寬幾公分,原樣粘好就可以了。
這也可看出,國(guó)營(yíng)郵政公司為什么競(jìng)爭(zhēng)不過(guò)民營(yíng)快遞公司的原因。
在石橋鋪舊書(shū)攤碰到一個(gè)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手里拿著一本舊版名著與攤主討價(jià)還價(jià),攤主就是不松口。我插嘴,對(duì)年輕人說(shuō),名著又不是稀缺書(shū),買新版的好,價(jià)格便宜不說(shuō),印刷精致,閱讀舒適感強(qiáng)。舊版書(shū)紙張和印刷技術(shù)與質(zhì)量都差,讀起來(lái)不爽,還費(fèi)眼力。
年輕人聽(tīng)從我的建議,放下了手里的書(shū)。攤主卻瞪大眼睛看著我,我趕緊溜了。
偶然在網(wǎng)上看到一本我的舊著賣,說(shuō)是簽名本。好奇心促使我請(qǐng)店主拍張扉頁(yè)簽名圖片發(fā)來(lái)看看。結(jié)果是二十八年前我送給鄭州一位文友的,他比我大二十一歲。猜想,文友是不是已“走”了?家人清理舊物時(shí)處理了這書(shū),然后輾轉(zhuǎn)到了舊書(shū)店。不然,二十多年里為何一直留著?
這書(shū)定價(jià)兩元,雖說(shuō)是當(dāng)時(shí)的市值,但店主現(xiàn)在標(biāo)出一百元的賣價(jià),我覺(jué)得有點(diǎn)小貴。書(shū)確實(shí)是舊書(shū)了,不過(guò)我手里還有十來(lái)本。于是,給店主發(fā)消息,說(shuō)想要這本書(shū)做個(gè)紀(jì)念,用手上同種書(shū)交換,并簽名鈐印后先寄給他。我拿“紀(jì)念”做幌子,看能不能換得店主的“情懷”。店主直接回復(fù)不行。
幾年過(guò)去了,書(shū)一直在網(wǎng)上掛著。
本地一文友,下鄉(xiāng)采風(fēng)時(shí)突患腦溢血“走”了,同城的幾個(gè)文友去送行。其中一女文友見(jiàn)他留下很多書(shū),本想問(wèn)他妻子怎么處理,但覺(jué)得不是這時(shí)候該問(wèn)的事。誰(shuí)知文友的后事一辦完,其妻把書(shū)全部賣給了廢品收購(gòu)店。女文友聽(tīng)說(shuō)后,拉著文友妻去追,卻早已被造紙廠拉走。女文友惋惜道:“要是賣給舊書(shū)店,興許我心里好受點(diǎn)。”
不知怎么我就想到網(wǎng)傳的一則“不是段子的新聞”:一人盜竊上萬(wàn)元的飲料,忙了幾天才全部倒掉,然后賣塑料瓶得二百多元。
有一天,我從舊書(shū)網(wǎng)上又淘了幾本書(shū),收到后馬上讀起來(lái),心里非常高興,情不自禁地對(duì)妻子說(shuō):“這次我買了幾本好書(shū)。”她隨口一答:“那原來(lái)買的都不是好書(shū)喲?”我頓時(shí)無(wú)語(yǔ)。
坐飛機(jī)時(shí),前排座椅的后背袋里都有讀物,不可帶走,循環(huán)閱讀。受到啟發(fā),我平時(shí)讀后的雜志不再丟棄,每次坐動(dòng)車時(shí)帶上一兩本即將讀完的,好在車上看。下車時(shí),順便插在后背袋里。算是一種分享吧!
隨意翻看1981年的一本《青年佳作》,這是當(dāng)年文學(xué)名刊《青年文學(xué)》選編的年度小說(shuō)集。突然發(fā)現(xiàn)里面夾著一張紙片,上面寫(xiě)著:“我們一起坐火車去看海吧!”那個(gè)時(shí)候火車和大海,對(duì)于一直生活在下川江邊的年輕人有著無(wú)比巨大的吸引力。
字條沒(méi)落名,也不認(rèn)識(shí)字跡(能認(rèn)也早忘了)。什么時(shí)候放進(jìn)去的?當(dāng)時(shí)是誰(shuí)借了這本書(shū)?一概不知。
我唯一能做的,是把紙片放回書(shū)里。
(源自“上游新聞”)
責(zé)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