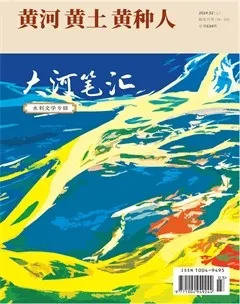在淄觀水
簡默



我真的沒想到,10天之內,竟然來了這座城市兩次。
這座城市和我現在居住的城市,在歷史血脈和精神氣質等方面有些類似之處,比如,它們都曾作為
片綠葉,點綴在春秋戰國這棵繁茂大樹的枝頭;它們都有超過120年以上的煤炭開采歷史,因煤而建,也因煤而興,最終都走向了煤炭枯竭的宿命,屬于典型的資源型城市。
我到外地去,經常被人面對面地問:你們那兒是不是出產棗子啊?每逢此時,我都像一個饒舌婦,恨不得費盡口舌地解釋清楚。來到這座城市,我最關心的是曾經嚴重缺水的它,如何在這片土地上找回水流充沛的歷史,枕著水波蕩漾的現實安居樂業。
我的父母在黔南山間的東方機床廠工作時,他們一個是廠職工醫院的醫生,一個是廠配電室的電工,都是在后方為生產一線服務,間接地與堅硬的機床打交道。回到山東,他們走向了與鐵相反的溫柔一面,雙雙成為與水打交道的水利工作者。即使是小時候說自己長大后的理想是打鐵的弟弟,也在長大后追隨他們的腳步,成了一名水利工作者。他們仨打交道的是一條姓淮的河。我家住在淮委南四湖管理處院內,出大門,向右拐,過大堤,上石橋,橋下是一條河,窄得甚至能夠抬腿從河的這邊邁到那邊,短到流著流著就不見了蹤跡,大家都叫它沿河。后來,經過疏浚,它變寬、變長了,據說可以一路暢流匯入微山湖。這讓它與他們仨的日常工作產生了必然聯系,也讓自淮委南四湖管理處院內出來的每一個人,在嗅著它的氣息、聽著它的水聲的同時,總是覺得它每天都淺吟低唱地漫過他們的心胸,仿佛是自來水管中嘩嘩流淌出的日子。
而我選擇了文字,在方塊字和標點符號的叢林中穿行,30年如一支箭,一剎那悄無聲息地沒入時間深處。我是一個蹩腳的手工藝人,面對那些表情生動、內涵豐富的方塊字和標點符號,壘砌不起自己的文字城堡。雖然我不像我的父母他們那樣天天與水打交道,卻不妨礙我關注河流,狂熱地熱愛河流。在我看來,關注河流是關注人類的生存質量,熱愛河流則是熱愛人類自身。一條河流,在大地上奔流,流過了歷史,流過了典籍,也流過了歲月。我們常說,紙壽千年。其實真正長壽的是河流。一條河流,有著一個古老的名字,它先于人的腳步從遙遠的地平線流來,在遇見人之前,它沒有名字,是條無名氏的河,直至遇見了人,被人命名了,但相對于它動輒成千上萬年的壽命,人仍是它兩岸搖籃間的嬰兒,我們習慣叫她母親河。是河留住了人流浪的腳步,人偎依在她的臂彎里,逐水而居,臨水而生,被她哺育和養大,又看著她一步一步地、頭也不回地,從一條河流走向另一條河流,重新開始在異鄉尋找故鄉。每一條河的流向,都是一條生命線,也是一條文明線。面對一條河,先哲們生發出“上善若水兮”“逝者如斯夫”之類的感喟,他們深入河的內心,洞悉河的秘密,由滾滾流淌的河水,在柔軟能夠摧硬的瞬間,在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剎那,悟出了世道人心、興亡盛衰,在水天相接處,先哲的思想成為人類天空上燦爛的群星。
我沒有哲人的智慧和慈悲,我只是一個凡夫俗子,我甚至淺薄地在想,先哲們臨水或望川的感喟,其實都不干河的事,你發你的喟嘆,關我河啥事?這只是你們人類的思考,我不會發笑,更不會停下向前奔流的腳步。一條河有它自己的倫理道德和美學追求,它從古流到今,河床漂浮著浪花般的閱歷與思索,像一個先知,以潺潺的抒情和浩蕩的吶喊,在前面引領著我們,它的選擇就是我們的選擇,我從一條河看見了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未來。我常常將一條河想象成一棵樹,一棵很大很老的樹,但我清楚,無論一棵樹怎么大怎么老,都無法與一條河相比。晝夜立于大地上的樹,與晝夜在大地上奔騰不息的河,在短暫地對視過后,首先悄然敗下陣來的永遠是一棵樹。我也的確在河的身體上看見了樹的形狀,這與歷史和壽命無關,它們都是生命力的象征。
比如,面前這條河,與眼前這座簡稱為“淄”的城市同一個姓,就叫淄河。淄水是它的前身,至清代,始改為淄河,又名淄川。它從南向北流淌,穿山區,過平原,無論叫啥名,都離不了水,汨汨奔涌的仍是那一河床甘甜的乳汁。自春秋戰國時期一路逶迤流來的淄河,雖隨季節而豐枯,卻常年流水,是古臨淄城也是今天這座城市的母親河,養育了一代又一代齊地子孫。我想起讀小學時的課本上,晏子出使楚國,楚王羞辱晏子,問:“齊國沒有人可派了嗎?竟然派你來當使者。”晏子答:“齊國的都城臨淄有七千五百戶人家,人們一起張開袖子,就能遮住天;揮灑汗水,就是在下雨;街上行人肩膀靠著肩膀,腳尖碰到腳后跟,你怎么能說齊國沒有人呢?”這段問答當時給幼小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過去了近40年,仍讓我一直記憶深刻。我看過復原的古臨淄城模型,里里外外,各種建筑鱗次櫛比,一條淄水環繞,護佑著臨淄城,好一座東方大城!不知為啥,我老是覺得淄水是千萬個齊人一起揮汗如雨“流”出來的。
這一次,我不是捋著歷史的脈絡來尋找淄河的,我是來看中國古車博物館而不經意地與它擦肩而過。它在我的左邊,河面闊大碧清,平整如鏡,風兒輕輕吹過,蕩起一圈一圈漣漪。這僅是它日常溫柔的一面,它還有另一張暴躁的面孔,到那時它水流湍急,水勢洶洶,水聲浩蕩地裹挾著樹枝、泥沙、石頭甚至羊群沖向下游,匯入小清河,最后投入大海的懷抱。一只一只白鷺翩然飛起,像一片一片白云,閃亮了我的眼,復落到河面上,怡然自得地浮游,照著河水啄理羽毛,間或探出長喙,沒入水中叼出一尾魚,魚兒拼命地在喙間掙扎,瞧上去有些驚心動魄,很快便沒了聲息……
我是第一次來到山東水利技師學院。說到技師,我理解是工匠,過去是手工藝人,現在則是操作信息化技術設備的工人。這所學院簡稱水院,因為父母和弟弟水利工作者的身份,我對它很是親切,也興趣盎然。說到水,居然就看見了水,還是一條河,在高高矗立的大禹治水塑像背后。請原諒我孤陋寡聞,我之前從未在哪個校園里遇見過一條河,這是一條真正的河,而不是那種有河之名無河之實的所謂河,它叫萌源河。我來水院是參加采風活動和黃河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揭牌活動。黃河是中國人共同的胎記和血型,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和血管里都奔騰著一條黃河,我們黃種人的生命也由黃河始,至黃土終。到達水院的當晚,我們沿著水邊,踱上陶然橋,背倚石欄,其樂陶然。橋下水面本平靜,聽見我們的說笑聲,魚兒紛紛浮上水面,傾斜著身體,探頭朝向我們。聽說是水院的師生常在飯后手捧剩飯來這兒喂它們,久而久之,只要聽見腳步聲和說笑聲,它們便立即像得了號令,爭先恐后地探頭等待從天而降的食物。
這時,我還認為這片水面像許多地方養在深閨的水面一樣,僅是一汪遍布著人工痕跡的水系,但我很快發現自己錯了。第二天一早,我站在同濟橋上,東望萌山,萌源河就發源于此。萌山不高,唯多紅砂石沉積巖,不易滲漏,留住大量地表水,積累涓涓細流,匯成一條河。萌源河不長,千米以內,卻為天然山溪性河流,一路接納一口口清泉,地表水與地下水互補交融,水源豐沛,水量漸大,水色清碧,滋潤得水院瀲滟靈動起來。我自東向西繞著萌源河走了一圈,這大概是我走過的最短的河流,待到額頭和背上沁出微汗,河也走完了。一路上,金雞菊和月季相伴;河上借勢筑壩,高低不同,水流跌落,和聲喧嘩,至平緩處水平浪靜,逍遙自在。一只初雪一樣的白鷺似乎受了我的驚嚇,撲棱棱地踏水飛起,就在我以為它會飛得更遠時,它卻僅僅前進了一米左右,又垂直落入水中,這是一眨眼的工夫發生的,甚至沒等它飛起時水面的漣漪與落下時水面的漣漪天衣無縫地重合到一起,因此,我有理由懷疑它像是在故意戲弄我,我哭笑不得,卻拿它沒辦法。一只灰色的鳥兒,比白鷺大,卻比白鷺膽小,它不認識我,我也叫不出它的名字,聽見我的腳步走近,它自水邊的灌木叢中驚慌地張翅飛出,落到下游的樹林深處。萌山與萌源河,都姓萌,仿佛是兄妹,又像是母子,多么美好的姓啊,叫起來心都被融化了。萌是萌態,是童年,是天真爛漫,是活潑可愛,是生命懵懂開始時的本真狀態。看著迎面走來的一張張年輕光潔的面孔,我想到,水院有萌源河穿校園而過是何其有幸:萌源河與孩子們朝夕相伴,它奔涌的脈搏應和著那么多強勁的心跳,又是何其有幸。其實最幸運的是孩子們,他們像一個個翠綠的芽兒,在水院尋找到了一條河之源,也開始了自己人生啟航之源。沒有任何藩籬能夠擋住一條河流浪的腳步,萌源河也終于流過水院,匯入文昌湖,成為孝婦河的支流。
孝婦河是一條源遠流長的河。這是一條姓孝的河,與孝婦顏文姜有關,這條河傳說是顏文姜的孝道感動上天而引來的神水。傳說歸傳說,但在顏文姜祠中,傳說卻以塑像的形式被凝固下來,仿佛一部立體的連環畫,在無聲地講述著孝婦河的故事。我隨著女導游,從頭走到尾,一邊小心提防著頭頂的巖石,一邊用眼睛翻閱著一幅幅畫面,很快便翻完了。我最感興趣的是祠中的一眼泉,叫靈泉,為孝婦河的主要源頭。靈泉在顏文姜祠下,整座祠像是顏文姜手中的尖底木桶,晝夜不停地涌出清清亮亮的泉水,仿佛是文姜的淚水,汨汨滔滔,一瀉百里。世上有許多大江大河,若上溯其源頭,不過是一脈涓涓細流,就像是一掛珠簾臥在地上。我想靈泉也如此,但我左看右看,就是看不見它的蹤影。祠前挖出一方正方形池子,連通著靈泉,一年到頭泉流不斷,順著地下流到祠外,流出一條孝婦河;池中央立著一個小男孩的石像,他站在蓮葉間,雙手捧壽桃,光著屁股,像是一個小沙彌,面朝祠外,天真無邪。據女導游說,趕上天降大雨,泉水旺時,池中水位居高不下,曾經漫至小男孩的脖子處。
因為顏文姜,孝婦河成為一條女性之河,也是這座城市的母親河,但它卻曾經是發展工業經濟的犧牲品,成了排污河道,雖曾屢屢治理,均未達到理想效果,水質一直較差。8年前當地提出圍繞構建“八河聯通、六水共用、清水潤城”主城區生態水系,實施孝婦河全流域綜合治理。讓我們想一想,一座老工業城市通過借助黃河和長江客水進行調蓄,每天有8條河流互相連通、彼此交融,引來一城活水和清水,環繞與滋潤著這座城市,是怎樣的一幅景象吧!那簡直是水跡淋漓、水光妖嬈了,開窗就能看到一條條綠水,這水自天上來,也來自地下:出門就能遇見一條條河流,與四面青山相映出山光水色。我沿著孝婦河,循著它安詳的呼吸,親近它美麗的身影。
隨后看見了一家凈化水公司,其實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城市污水處理廠,負責收集處理周圍8個鎮的工業和生活污水,處理后的水質優于《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一級A標準,注入張相湖國家濕地公園作為生態補水。站在污水處理池前,看到池中污水暗黑如夜,不安分地扭動和翻滾著,泛著泡沫,我不忍更不愿多看一眼。再看面前的桌子上,一字擺開三個玻璃瓶,分別裝著進水、出水和處理后的再生水,進水是污水處理池中黑而渾濁的水,出來已經變得清澈透明,而再生水則像淚水一樣純凈。聽介紹者說,這種再生水能夠端起來直接飲用。我相信他說的話,因為在排污口的生物指示池中,注滿了經過一次次技術處理后的再生水,它重新獲得了新生,可以直接對外排放,一尾尾魚兒在其中暢快地游來游去,仿佛這方池子就是它們的河流和樂園。這方池子甚至“招惹”來了白鷺,它們在空中一個俯沖,就從水中叼起一尾魚。自從這池子中養了魚,它們就不愿費勁到河里抓魚,而改到這兒“偷”魚了。人和魚同為地球上的生命,人能夠給魚以平安和幸福的再生水,魚也能被人類安全食用。
在張相湖國家濕地公園,有郁郁蔥蔥的蘆葦和蒲草,大方舒展的睡蓮,還有各種各樣的水生植物,它們被分區域密密麻麻地種植下來,對城市污水處理廠處理后的尾水進行深度降解和凈化,這采用的是“潛流濕地+表面流濕地+河道濕地”的組合工藝,就像打出的組合拳。經過治理的濕地公園水草豐茂,在陽光照射下,閃爍著粼粼波光,仿佛無數尾魚一齊亮著鱗片。水好則有魚蝦蟹相伴樂游,水清則有水烏出沒往返,水美則有人休閑乘涼,而這一河水的宿命就是流浪,它永不放棄自己東流的腳步,最后的歸宿仍是大海。它滾滾向前奔騰,兩岸給了它最大程度的寬容與接納,一條河生來如此,前赴后繼,執著不合。從一滴水開始,回到一滴水中,就像風生來沒有翅膀,河也沒有故鄉,只有流處,找不到歸路。
來到馬踏湖,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微山湖。它與數百千米之外的微山湖在風俗習慣和氣息氣質上有許多相通之處。走近馬踏湖,猛然聽到“拿魚”的說法,我覺得很新鮮,不知微山湖有無此說法。我想到的是需要湖里有多少魚,有多好捕,才能讓馬踏湖區人將捕魚看得如此簡單,簡單到不用花力氣去捕,而直接探手到湖里去拿就行了。馬踏湖是一個多功能湖泊濕地系統,也是小清河中游唯一的天然湖泊,由烏河、潴龍河、孝婦河等河流匯聚而成,水域面積96平方千米,被稱為小清河之腎。
20世紀末,伴隨著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三條主要入湖河流遭到嚴重污染后被截流改道,馬踏湖失去了穩定水源補給,加上人們圍湖造田.湖區面積銳減至不足20平方千米,湖泊生態功能幾乎喪失殆盡。當地痛定思痛,按照以治控源、以保促凈、以用減排的“治保用”思路,對馬踏湖及其上游河流進行科學整治,在污水處理廠下游、主要入湖河流河道和入湖口建設人工濕地與生態河道,凈化入湖水質,逐步恢復三條主要入湖河流的歷史走向,使馬踏湖重新獲得了穩定水源補給。
失去方覺彌足珍貴,復得才會倍加珍惜。湖區人逢人便興奮地說:“俺馬踏湖明晃晃的大水面又回來了!”由于時間緊,我無法劃著湖區特有的小溜子進入湖中領略村村靠湖、家家臨水、戶戶通船的北方水鄉風貌,只能乘著觀光車沿著湖堤邊走邊看。來到湖堤最高處,觀光車停下來,我下車在湖畔信步瀏覽,看見水中優雅舞蹈的笮草。我吃過用它炸的丸子,它的驚艷現身是水環境質量良好的標志之一。還有蘆葦、香蒲、菰、水蔥、芡實、睡蓮、蓮等許多我叫得出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水生植物,它們與形形色色的鳥類形影不離,一起在這片擁有2700多年歷史的巨大水面上生息繁衍,重新找回它們的祖先曾經擁有的野性而快樂的日子。
住在酒店,我早晨沿著附近的漁洋湖散步,看見了令我焦慮和心痛的一幕:靠近岸邊,一片片睡蓮葉如一個個茶盤,遮得水面密不透風,一條銀白色的魚兒自水中蹦到了睡蓮葉上,它太頑皮了,想都沒想,攢足勁兒就跳到了睡蓮葉中央。睡蓮葉太大太密了,它在上面就像一片柳葉,太小太窄了,徒勞地蹦著高兒,打著挺兒,幻想重新跳回水中,終于筋疲力盡,癱軟到了睡蓮葉上。眼看頭頂驕陽越升越高,它快耗盡了最后一絲氣力,身體內最后一滴水也要干涸了。我一直嘗試著解救它,可那一片睡蓮葉離我太遠了,它也承受不了我哪怕一只腳的重量。我到處尋來泥巴往睡蓮葉上扔,卻無濟于事,想找一根竹竿撥魚兒入水,可掃視四周,只有一棵棵粗壯的柳樹和楊樹挺拔站立。我也終于放棄了努力,不忍回頭地繼續向前走去。
一連幾天,這條魚兒都浮現在我腦海中,像是刻下了一般。我清楚,它渴死被曬成魚干的結局是肯定的。不知為何,大概是愛魚及人的共情緣故,我老是將它想象成我們人類;如果我們生活的生態環境被徹底破壞了,地球瀕臨毀滅的邊緣,最終河流干涸了,我們沒了水源,淚水也流干了,變成了睡蓮葉上的那條魚,接受越來越毒辣的烈日暴曬,又有誰能夠解救我們?
這樣想著,我有些心神不寧起來。如此說,在這座姓淄名博的城市觀水,觀的不僅是生態環境,還有人類自身命運。(作者系棗莊市作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