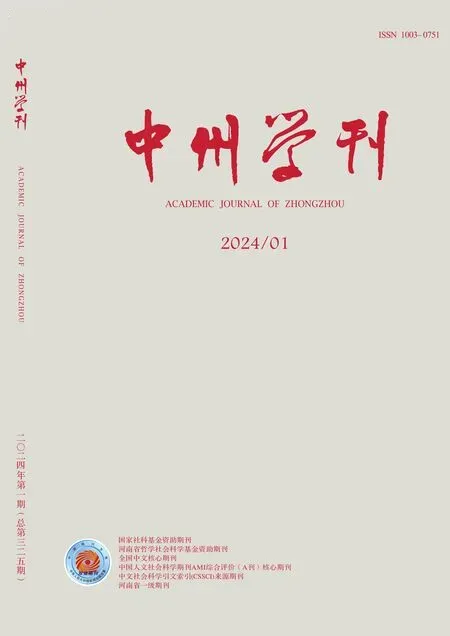唐宋審美轉(zhuǎn)型中佛禪“空”境的文學(xué)書寫新變
——以王維和蘇軾為中心
楊吉華
在“唐宋變革論”的總體性歷史場(chǎng)景中,從唐音到宋調(diào)的審美轉(zhuǎn)型,以及唐音與宋調(diào)兩種不同時(shí)代審美范式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領(lǐng)域中的自然呈現(xiàn),為深入理解唐宋文人心態(tài)變化及唐宋文學(xué)新變,提供了一個(gè)有效的美學(xué)闡釋視角。在佛禪之風(fēng)盛行的唐宋時(shí)期,作為佛教義理最高范疇的“空”觀,將“諸法皆空”的判斷奉為世界萬物與人生本質(zhì)的普遍真理;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特點(diǎn)的禪宗,則在緣起性空的世界實(shí)相中,把對(duì)事物絕對(duì)自性“空”“無”的覺悟確認(rèn)為審美的最高境界。佛禪思想中的這種高妙智慧,為人擺脫各種痛苦煩惱的糾纏,進(jìn)入絕對(duì)自由超脫的逍遙游精神境界,提供了方便法門,對(duì)于唐宋文人,尤其是那些仕途失意、宦海沉浮的文人,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當(dāng)他們把自己對(duì)于佛禪“空”觀的自我體認(rèn),以一種個(gè)性化的抒情方式呈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時(shí),必然使作品中攜帶著唐宋不同的文化氣質(zhì),營造出具有強(qiáng)烈佛禪審美意味的“空”境。“一身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1]252的王維,與“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2]2114的蘇軾,都深受佛禪文化濡染,在其文學(xué)作品中,都存在一個(gè)具有豐富文化內(nèi)蘊(yùn)的“空”境,這是唐宋變革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的自然反映。然而,王維與蘇軾對(duì)佛禪“空”境的自我體認(rèn)與文學(xué)書寫,無論從形成路徑還是從審美風(fēng)格及內(nèi)在精神追求方面看,都表現(xiàn)出佛禪“空”境的文化氣質(zhì)在唐宋審美轉(zhuǎn)型背景下的時(shí)代新變,因而成為考察唐宋審美轉(zhuǎn)型的一個(gè)有效文學(xué)樣本。
一、空靈蘊(yùn)藉與空幻寂滅:王維與蘇軾“空”境的審美特色
1.與道合一:王維“空”境的總體特質(zhì)
王維常常在靜物、靜景中營造出一種極具空間張力的空曠靜寂,從而賦以其詩歌作品中的“空”境以無限靜謐的靈動(dòng)之美。他常常直接從“空”字著眼,如空山、空林、空館、空庭、秋空等,“空”字大概出現(xiàn)在其五分之一的詩歌中。這些“空”字,表面上寫自然山水之空,實(shí)則是由山水而體察世界。詩人以一顆隨運(yùn)自然的心靈,描繪出一個(gè)恬淡安然、空靈和諧的自然世界。這些“空”字又常常與“靜”“閑”“幽”字等聯(lián)系在一起,使其詩中所描述的直觀之物,不僅僅是一個(gè)客觀實(shí)在的自然物象,而是有著般若“空”觀意味的心靈意象,從而使其詩歌獲得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深長審美意味,最終使他詩歌中的“空”境具有禪意盎然的意趣。
王維常常由“靜”返“動(dòng)”,于“靜中有動(dòng)”來呈現(xiàn)“空”境的張力。最典型的莫過于《鳥鳴澗》中的“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shí)鳴春澗中”[1]89,外在環(huán)境中處于靜態(tài)的夜靜、山空、人閑,與處于動(dòng)態(tài)的花落、月出、鳥鳴的鮮明對(duì)比,反襯出“空”境的容納深度。又如《鹿柴》中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fù)照青苔上”[1]86,同樣也是通過聲音層面的“人語響”和光影復(fù)照青苔上的搖曳動(dòng)態(tài)之勢(shì),來襯托出“空山”的靜寂氛圍。此“空”境中的“靜”,便是詩人于充滿動(dòng)態(tài)的外在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靜”,一動(dòng)一靜之間,更顯“靜”的深度。這也就是王維自己所說的“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guān)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fēng)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1]120。在這些動(dòng)靜結(jié)合的直觀形象中,“惟好靜”且“萬事不關(guān)心”的自我主體,在“自顧”與“空知”中,對(duì)“君問窮通理”的回答方式,表明的也是對(duì)世事看空后的解悟。“山中習(xí)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1]187亦然,表達(dá)的即是《莊子》所謂的“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3]的境界。詩人在虛靜的坐忘心齋之中進(jìn)入空明寂靜的心理狀態(tài),在內(nèi)心體察領(lǐng)悟之中絕思絕慮,最終達(dá)到與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因此,對(duì)于王維而言,構(gòu)成其詩詞作品“空”境中的“靜”,不是指外在自然環(huán)境的靜,而主要是指詩人自己在般若空觀浸染下形成的主觀審美心態(tài)的靜謐狀態(tài)。
2.任運(yùn)自然:王維“空”境的情感狀態(tài)
這種恬淡靜謐的安適心靈狀態(tài),折射出的是詩人對(duì)“不生不死,來去自由”的涅槃境界了悟后,以一顆“無住”“無念”與“無慮”之心面對(duì)宇宙天地的任運(yùn)自然。詩人或在“北窗桃李下”[1]153的幽靜環(huán)境中“閑坐但焚香”[1]153,或“終年無客長閉關(guān),終日無心長自閑”[1]170,或“悟寂為樂,此生閑有余。思?xì)w何必深,身世猶空虛”[1]39,或“閑居日清靜,修竹自檀欒”[1]207,從中都可以看出,王維的“閑”更多的是一種與佛禪焚香、入定、悟空等有關(guān)的禪定空寂之意。這種“閑”得之于佛禪的“無心”,王維將這種由對(duì)佛禪之“空”的感悟而來的“閑”,安放于自然山水中,以一種悠閑自在的姿態(tài),傳遞出作者在佛禪濡染下任運(yùn)自然的存在方式,從而使其詩歌具有濃郁的佛禪韻味。這與蘇軾空幻寂滅中的“閑”所透露出的禪理哲思,有著極大的不同。
此外,“幽”也是構(gòu)成王維“空”境的重要元素之一。王維或是直接以“幽”入詩,如“清燈入幽夢(mèng),破影抱空巒”[1]268、“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1]126等,尤其是“獨(dú)坐幽篁里,彈琴復(fù)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1]249的描述,表面寫客觀自然環(huán)境的幽靜,實(shí)際上是描繪詩人自我幽淡空寂的心境。或是在詩句中不直接使用“幽”字,但詩中卻時(shí)時(shí)表現(xiàn)出詩人參禪去念的幽思之情。如“字字入禪”的《過香積寺》:“不知香積寺,數(shù)里入云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1]131在香積寺幽冷安靜的外在自然環(huán)境中,與佛禪密切相關(guān)的“深山何處鐘”之意象及其聲響,及至“安禪制毒龍”的典故使用,傳遞出的是詩人參禪去念的幽思幽意。
3.萬境歸空:蘇軾“空”境的總體狀態(tài)
王維與蘇軾對(duì)佛禪般若“空”觀都有深刻的體悟,但與王維不同,蘇軾側(cè)重表現(xiàn)主體心靈的空幻寂滅,反映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就是他在《送參寥師》中所說的:“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dòng),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咸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dāng)更請(qǐng)。”[2]905詩人與僧人一樣,都需要在虛靜的狀態(tài)中了悟群生百態(tài),才能創(chuàng)作出上乘的藝術(shù)作品。這是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空”境審美意味形成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因此,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的“空”境,并不是空無一物的境界,而是一種在主體心靈中容納宇宙萬境的狀態(tài),是一種形而上的“空”境。
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的“空”境,較多表現(xiàn)為在了悟世界皆空的佛禪義理后所形成的對(duì)整個(gè)宇宙人生的空幻寂滅意識(shí),由此衍生出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貫穿始終的“人生如夢(mèng)”或“人生如寄”的主題。從青年時(shí)期雪泥鴻爪的感慨,到“過眼榮枯電與風(fēng),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2]331,再到“回頭自笑風(fēng)波地,閉眼聊觀夢(mèng)幻身”[2]868等,它一直是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最重要的一個(gè)主題。對(duì)于這一現(xiàn)象,周裕鍇先生曾進(jìn)行過系統(tǒng)論述:“在蘇軾的很多文學(xué)作品(包括詩、文、詞)中,始終貫穿著一個(gè)鮮明的禪學(xué)主題,即人生如夢(mèng)、虛幻不實(shí)。這一主題來自禪宗的般若空觀。……縱觀蘇軾的全部詩歌,視人生如夢(mèng)幻泡影露電空花浮云的詩句,幾乎近百處。這種般若空觀與老莊虛無思想結(jié)合,構(gòu)成了蘇軾處理人生存在意義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在蘇軾詩中,人生如夢(mèng)的主題卻常常伴隨著深沉的慨嘆,并不輕松達(dá)觀。”[4]這種人生如夢(mèng)的主題,在世事滄桑的感觸中,使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的“空”境典型地表現(xiàn)出一種空幻寂滅的特點(diǎn),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孫虹也曾對(duì)蘇門文人群評(píng)價(jià)道:“對(duì)于生存的悲哀,蘇門文人充滿悲劇性的體悟:紅塵之樂事,不能永遠(yuǎn)依恃;樂事中何況還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的遺憾,自其變者觀之,瞬息間則又樂極生悲,人非物換,終究是到頭一夢(mèng),萬境歸空。”[5]蘇軾作為蘇門文人群的首領(lǐng)人物,他對(duì)這種“到頭都是一夢(mèng)、萬境歸空”的理解更加深刻而真切。
4.幽寂感傷:蘇軾“空”境的情感色彩
與此空幻寂滅的審美特點(diǎn)相適應(yīng),在蘇軾詩詞作品中,幽寂是其“空”境中不容忽視的一種重要審美感受。但與王維不同,蘇軾“空”境中的幽寂是一種遠(yuǎn)離塵世的孤高決絕和超凡脫俗。《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中那個(gè)在幽寂夜晚中如同孤鴻般徘徊的“幽人”,正是蘇軾自我孤高絕俗的典型刻畫。也正是這種遠(yuǎn)離塵世的幽獨(dú)決絕,才使黃庭堅(jiān)說此詞“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diǎn)塵俗氣,孰能至此”[6]。蘇軾也曾明確地將自己視為“幽人”,如“嶺南萬戶皆春色,會(huì)有幽人客寓公”[2]2071等。還有一些作品采用比擬手法,如在《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一詩中,詩人以“幽獨(dú)”的海棠名花自擬,與“漫山桃李”的粗俗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海棠,正是蘇軾“純以海棠自寓,風(fēng)姿高秀,興象微深”[7]的寫照。
此外,“閑”也是一種與“空”境相關(guān)的審美感受。但是,與王維不同,“閑”在蘇軾的“空”境中,是那種透著淡淡感傷的無可奈何之“閑”。在蘇軾晚年那些似乎與世無爭(zhēng)的“閑”中,我們其實(shí)更多體會(huì)到的是一種身心疲憊后的無奈落寞與惆悵之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深沉喟嘆。《沁園春》中的詩句“用舍由時(shí),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yōu)游卒歲,且斗尊前”[8]134,在看似悠閑的“袖手何妨閑處看”的表面下,隱藏著一種無處可逃的苦悶。《行香子·清夜無塵》中“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shí)歸去,做個(gè)閑人。對(duì)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8]725的隱逸之思,也只是蘇軾對(duì)人生“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mèng)中身”[8]725虛無體驗(yàn)后,做個(gè)飲酒彈琴閑適之人的自我想象與安慰,透著一股濃郁的感傷情懷。
相比較而言,王維詩歌作品中的“空”境,呈現(xiàn)出一片空靈蘊(yùn)藉的審美意味,透出濃郁的生命氣息,與蘇軾充滿空幻寂滅色彩的“空”境,表現(xiàn)出極大的不同。王維詩歌中由“靜”“閑”“幽”構(gòu)成的“空”境,在對(duì)宇宙自然世界的恬淡和諧描繪中,具有一種空靈蘊(yùn)藉的純凈之美。這與蘇軾那種在人事滄桑的經(jīng)歷中所體會(huì)到的,更多具有形而上意義的宇宙人生空漠幻滅的悲劇意識(shí)所構(gòu)筑的空幻寂滅之“空”境不同。從某種程度上說,蘇軾“空”境的空幻寂滅與王維“空”境的空靈蘊(yùn)藉在審美特色上的不同,是佛禪文化對(duì)唐宋審美轉(zhuǎn)型期文人創(chuàng)作影響的直接結(jié)果。當(dāng)然,這種佛禪“空”境審美意蘊(yùn)在唐宋文學(xué)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文化氣質(zhì),也與蘇軾和王維所采取的不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手法有著直接關(guān)系。
二、以畫入詩與以禪入詩:王維與蘇軾“空”境的形成路徑
王維與蘇軾深諳般若“空”觀,并能將這種佛禪智慧體悟巧妙地轉(zhuǎn)化為文學(xué)作品中的“空”境。但在具體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過程中,二人對(duì)“空”境的建構(gòu)手法完全不同。簡(jiǎn)單說來,王維較多地采用以畫入詩的方式,蘇軾則更多地采用以禪入詩的手法。
1.畫的技法與詩的意境:王維“空”境的營造方法
王維嫻熟地運(yùn)用以畫入詩方式營造“空”境,使其作品具有生命靈動(dòng)氣息的空靈蘊(yùn)藉之美。然而有趣的是,王維詩雖然“字字入禪”,但我們?cè)谒U意盎然的作品中,卻很少能像在蘇軾作品中那樣,看到大量佛禪用語或典故,具有濃郁的學(xué)問化和思辨氣息,更多感受到的是詩畫合一的無限妙趣。正如沈德潛所說:“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shí)得禪理。”[9]《舊唐書》說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尤經(jīng)營),參于造化,而創(chuàng)意經(jīng)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yuǎn),云峰石色,絕跡天機(jī),非繪者之所及也”[10]。這在他的“空”境塑造中也表現(xiàn)得較為明顯。
王維開創(chuàng)了南宗畫派,深諳繪畫技法與詩歌創(chuàng)作技巧。他以畫家之眼觀照自然,以詩人之心體悟自然,自覺將繪畫手法中的構(gòu)圖、線條、色彩、點(diǎn)染、暈染等繪畫技法,巧妙化用到詩歌創(chuàng)作中,形成其詩畫藝術(shù)在經(jīng)營與構(gòu)思、色彩與樂感、氣韻與意境等方面的有機(jī)融合,使其詩歌具有獨(dú)特的“氣韻生動(dòng)”之繪畫美特色。從“空”字著手,大量使用“靜”“閑”“幽”等與空有關(guān)的關(guān)鍵字眼來構(gòu)筑“空”境,是王維詩歌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如他的《山居秋暝》,用文字媒介描繪了一幅清新靈動(dòng)的秋山新雨圖:初秋山雨初霧的清新傍晚,幽靜的山間皓月當(dāng)空,清冽的山泉輕輕拂過石面,晚歸的漁舟劃過蓮池,一切都顯得極為清幽寂靜,不染塵埃。在《積雨輞川莊作》中,他以典型的繪畫構(gòu)圖方式,由遠(yuǎn)及近,由景及人,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輞川山莊圖:“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xí)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zhēng)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1]187這不禁讓人想到朱景玄對(duì)其《輞川圖》的評(píng)價(jià):“山谷郁盤,云水飛動(dòng),意出塵外,怪生筆端。”[11]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蘇軾何以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12]了。又如,在“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13]的《鳥鳴澗》中,王維運(yùn)用繪畫點(diǎn)染手法描繪的夜靜山空、月亮初出、桂花飄落、山鳥春澗的唯美畫面,恰如《史鑒類編》評(píng)價(jià)的那樣:“王維之作,如上林春曉,芳樹微烘,百暗流鶯,宮商迭奏……真所謂有聲畫也。”[1]511
此外,使用繪畫留白手法形成虛實(shí)相生之境,也是王維“空”境具有空靈蘊(yùn)藉之美的重要原因之一。“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1]86、“峽里不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云山”[1]98、“山中元無雨,空翠濕人衣”[1]90等,都是從“空”字著手描繪出一個(gè)極具畫面感的既實(shí)又虛的縹緲空間。在這個(gè)空間中,景與人若隱若現(xiàn),似有似無,具有中國山水畫留白中隱藏的靈動(dòng)之美,表面上是自然山水之空境,實(shí)則向“空”而生,將自我置于其間,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禪意化的“空”境來表達(dá)自我內(nèi)心的空靈境界,虛實(shí)相生之間,傳遞出一種含蓄深邃而又幽遠(yuǎn)深沉的無窮意味。正如趙殿最所言:“右丞通于禪理,故語無背觸,甜澈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寶也,果之于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使人索之于離即之間,驟欲去之而不可得,蓋空諸所有而獨(dú)契其宗。”[14]
由此可見,王維在營造“空”境時(shí),常常借用繪畫手法,通過對(duì)自然山水的生動(dòng)描寫來傳遞心中的禪意禪趣。用這種以畫入詩的創(chuàng)作方式來表現(xiàn)“空諸所有”的理念,既符合禪宗對(duì)外在現(xiàn)象世界的認(rèn)知,也賦予其詩歌一種詩畫合一的蘊(yùn)藉之美。再借助“詞秀調(diào)雅,意新理愜,在泉成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15]的詩歌語言進(jìn)行情景交融的描繪,也就使其詩歌具有了無限的言外之意、韻外之致和味外之旨的美感。因此,錢鐘書說:“在他(王維)身上,禪、詩、畫三者可以算是一脈相貫。”[16]王維采用以畫入詩方式形成的“空”境,由此也就具有了較為明顯的禪意化與詩意性文化氣質(zhì)。
2.禪意化與詩意性:王維“空”境的文化氣質(zhì)
以畫入詩的方式,使王維詩歌中的“空”境,在妙若天機(jī)的繪畫美中,形成一種空靈幽靜與超塵脫俗的悠遠(yuǎn)意境。他以“對(duì)境無心”的清凈無染之心,直指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美無言的天籟“真如”世界,呈現(xiàn)出類似“住心看靜”般的空寂虛靜之佛禪體悟意味。王維對(duì)于外在自然世界的“空”“靜”“閑”“幽”等感悟,也并非虛無一片,而是在處處會(huì)心適意處,一切境隨心轉(zhuǎn)處,無色無相更無塵。山深人寂處、不知流年幾許的辛夷花,自開自落,既無生的欣喜,亦無死的哀傷,得之自然又歸于自然,于靜謐空靈的詩歌意境之中,傳遞出不悲生死的禪意感悟。“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的隨緣乘化與無心之舉,有一種悠然會(huì)心處,所見無非是道的深刻佛禪意味。在天光云影的自然空靈之中,詩人“審象于凈心”,心境空寂而萬境相擁,是一種物我兩忘的禪悅之趣,傳遞出靜極生動(dòng)、動(dòng)極歸靜、動(dòng)靜不二的深刻禪意感悟。《竹里館》中于萬籟俱寂的深林月夜,獨(dú)坐幽篁,彈琴長嘯的詩人,同樣還是在幽深靜寂之極的清寂中,摒絕塵俗,超然物外,傳遞出一種清妙和諧的寂靜之樂。這一切,折射出王維在澄明無蔽的自然中,以一顆不染塵埃的清凈之心,了悟宇宙自然與人生清凈無染的本來面目,從而擺脫物累、乘化超然,并獲得物我一如,了脫煩惱的自在解脫之精神境界。由此而來,王維詩歌中的“空”境,也就常常于空靈靜寂中蘊(yùn)含著深邃的佛禪意趣,如野云孤飛般禪趣盎然、佛味十足。
與此同時(shí),王維詩歌中的“空”境,也在禪觀自然的意趣中有了心生萬境的圓融詩意。在王維看來,無論外在自然世界如何變幻無窮,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如何紛擾繁復(fù),人生經(jīng)歷如何波瀾起伏,內(nèi)心世界如何萬壑爭(zhēng)流,最終都將歸于佛禪的般若空境。因此,他總能以一種萬法平等的禪悟體驗(yàn)方式去感知萬物,并竭力將自我主體淡化、消融于大千世界之中,讓自然萬象以一種最本真自如的方式直現(xiàn)在其詩歌中,以至其詩歌中深得佛禪般若三昧的“空”境,在看似虛無縹緲的塵外空靈之中,于心物融合的妙悟體驗(yàn)瞬間,將佛禪的宗教體驗(yàn)轉(zhuǎn)化為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梵我合一的無礙心境與無功利的審美體驗(yàn)。因此,在王維詩歌的“空”境之中,人與宇宙天地萬物是同一的,主客同體,物我兩忘。而且,與道合一的任運(yùn)自然與灑脫超越,又始終不離真如本性的詩意體驗(yàn),形成其詩歌“空”境以佛禪“空”性為內(nèi)在思想底蘊(yùn),且飽含豐富宇宙本體與人生意義的味外之旨。這樣,通過以畫入詩的手法,最終形成王維詩歌“空”境中無處不在的幽靜淡雅的意境,于清空閑遠(yuǎn)中感悟自在永恒的空靈蘊(yùn)藉之美,充滿禪意與詩意的圓融之美。
3.禪的思維與詩的語言:蘇軾“空”境的營造方法
由于宋代禪宗的發(fā)展影響以及蘇軾自身較高的佛禪造詣,以禪入詩成了蘇軾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gè)典型特點(diǎn)。惠洪在《跋東坡允池錄》中對(duì)蘇軾的文風(fēng)評(píng)價(jià)道:“其文渙然如水之質(zhì),漫衍浩蕩……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17]宋代胡仔說蘇軾“語言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18]。明代俞彥也說:“子瞻詞無一語著人間煙火,此自大羅天上一種。”[19]清代劉熙載說:“東坡詩善于空諸所有,又善于無中生有,機(jī)栝實(shí)自禪悟中來。”[20]這些評(píng)價(jià)充分說明,蘇軾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深刻的佛禪烙印,反映到“空”境的形成,就是一種以禪入詩的方式。
“以禪入詩”本是一個(gè)較為寬泛意義上的概念。從禪與詩的思維方式到語言表達(dá)、價(jià)值取向等方面,都可歸入“以禪入詩”的范疇。在蘇軾這里,“空”境創(chuàng)作中所采取的是一種比較狹義化的以禪入詩方式,主要是從文學(xué)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手法上來說。蘇軾一方面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過程中直接引用佛禪用語和典故入詩,另一方面也借用將抒情化的文學(xué)語言重新改造加工后來表達(dá)相對(duì)較為抽象的佛禪義理。當(dāng)然,蘇軾的以禪入詩并不是以宣傳佛禪義理為指歸,而只是運(yùn)用語言形式來承載佛禪內(nèi)容。
因此,蘇軾通過以禪入詩塑造“空”境的方式,可以粗略分為兩個(gè)層次。一是直接引用佛禪用語或典故入詩。如“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靜聲。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2]1218-1219、“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rèn)家山作本元”[2]2365等。二是用抒情化的文學(xué)語言重新改造加工后來表達(dá)相對(duì)較為抽象的佛禪義理。如在蘇軾大量的人生如夢(mèng)的空幻感喟嘆里,明顯具有《楞嚴(yán)經(jīng)》《維摩經(jīng)》《圓覺經(jīng)》等的影子。《楞嚴(yán)經(jīng)》中“卻來觀世間,猶如夢(mèng)中事”[21]1的覺悟、《維摩經(jīng)》中“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mèng)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yè)緣起,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云須臾變滅……”[21]539的人身無常之喻、《圓覺經(jīng)》中“如夢(mèng)中人,夢(mèng)時(shí)非無,及至于醒,了無所得”[21]913的佛禪義理等,在蘇軾的文學(xué)作品中,轉(zhuǎn)化為“事如春夢(mèng)了無痕”“世事一場(chǎng)大夢(mèng),人生幾度秋涼”[8]798、“休言萬事轉(zhuǎn)頭空,未轉(zhuǎn)頭時(shí)皆夢(mèng)”[8]533、“萬事回頭都是夢(mèng)”[2]1520、“人間何者非夢(mèng)幻,南來萬里真良圖”[2]2121、“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云隨”[2]98等詩意化的表達(dá)。包括他著名的雪泥鴻爪之喻,也是《華嚴(yán)經(jīng)》“譬如鳥飛虛空”[21]1的文學(xué)化表達(dá)。
4.學(xué)問化與思辨性:蘇軾“空”境的文化氣質(zhì)
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蘇軾的“空”境,由于較多指向宇宙人生的空幻寂滅,而具有明顯的形而上意義。相對(duì)于王維而言,蘇軾的“空”境中禪理意味高于禪意妙趣,哲學(xué)思辨色彩相對(duì)濃厚,較多受到佛禪經(jīng)書中有關(guān)文字的啟發(fā)。“因此,盡管蘇軾說什么‘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dòng),空故納萬境’(《送參寥師》),‘我心空無物,斯文何足關(guān)。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主張用平靜空明的內(nèi)心來返照萬象,牢籠萬物,但實(shí)際上,他很少能做到這一點(diǎn)。至少在作詩之時(shí),那些佛典禪理、邏輯思辨、古言俗語又征服了他,心無法空,意不能靜,于是筆若懸河,滔滔不絕,揮灑開去。空境的觀照本是無言的,或是寡言的,意象自然呈露,禪意自蘊(yùn)其中,而蘇軾觀照的結(jié)果,卻常常引發(fā)大段哲理性的思辨,‘橫說豎說,了剩無語’。”[22]因此,蘇軾采用以禪入詩方式形成的“空”境,具有明顯的學(xué)問化與思辨性色彩。
“臺(tái)閣山林本無異,故應(yīng)文字不離禪。”[2]2755蘇軾喜好佛禪,對(duì)《維摩經(jīng)》《楞嚴(yán)經(jīng)》《圓覺經(jīng)》等佛教經(jīng)典和《景德傳燈錄》《五燈會(huì)元》等禪宗語錄非常熟悉,深悟佛禪“性空”觀、“唯心任運(yùn)”觀和“無住無縛”觀等,具有較高的佛禪文化造詣。佛家對(duì)“活法”的追求與禪門宗風(fēng)“反常合道”“游戲三昧”“禪悟機(jī)峰”等的影響,又使蘇軾能夠在以翰墨作佛禪之事時(shí),將相對(duì)抽象的佛禪語匯、義理和充滿玄幻色彩的佛禪事典不落言筌地為我所用,巧妙剪裁而不著痕跡地引入自己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他以高超的才力將佛禪學(xué)問自然糅入詩詞中,使佛禪語義、事典、義理和詩詞情感之間妙和無垠,毫無牽強(qiáng)湊合之跡,也無雕琢用力之感。因此,佛禪智慧與游戲筆墨的渾然天成,使蘇軾以禪入詩的“空”境文學(xué)書寫兼具學(xué)問功夫與詩情妙意。這種才情與學(xué)力的相得益彰是形成蘇軾之文“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答謝民師推官》)圓活流轉(zhuǎn)之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蘇軾詩詞創(chuàng)作乃至整個(gè)宋代詩詞創(chuàng)作學(xué)問化特征的典范,賦予其詩詞作品中的“空”境較明顯的學(xué)問化色彩。
較高的佛禪文化修養(yǎng)與三次遭貶、顛沛流離的曲折人生經(jīng)歷,又使蘇軾對(duì)佛禪思想的理解參悟,總是與自我人生實(shí)踐的思考和安頓心靈的追尋密切相連。融入自己對(duì)宇宙人生獨(dú)特感悟以及對(duì)生命終極意義超脫思考的佛禪文學(xué)書寫,使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的佛禪“空”境,具有更為深刻的哲理思想內(nèi)涵,形成較為明顯的思辨性色彩。特別是深深植根于蘇軾靈魂深處,并在其詩詞作品中被反復(fù)詠嘆的“人生如夢(mèng)”與“人生如寄”,看似消極,實(shí)則是在“萬境皆空”的感傷惆悵抒情中,反跳回真實(shí)無常的人生,直面生的艱辛,在透悟人生有限性的基礎(chǔ)上,不執(zhí)著于絕對(duì)的永恒,并力圖在對(duì)人生的大徹大悟中,不假外求,返回自我內(nèi)心,超脫生老病死的痛苦,于“心安處”做到超然物外、不為塵累,達(dá)于“歸去,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的隨緣自適,并由此直抵曠達(dá)人生境界。這種來自佛禪之“空”的虛幻式生命體驗(yàn)及其超越,實(shí)際上是蘇軾在對(duì)宇宙自然人生的整體性觀照中,從宇宙與人生、社會(huì)與人生的種種關(guān)系上,對(duì)人生價(jià)值意義做出的理性判斷。這就從反面表現(xiàn)出人對(duì)自我人生與宇宙自然和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深刻哲理性反思,因而必然使其詩詞文學(xué)作品中的“空”境,具有較為深刻的思辨性色彩,而這也恰恰是蘇軾以禪入詩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手法得以實(shí)現(xiàn)的表現(xiàn)之一。
因此,王維以畫入詩對(duì)“空”境的塑造,更多表現(xiàn)出其詩歌的禪意色彩;而蘇軾以禪入詩對(duì)“空”境的塑造,使其詩詞作品具有濃郁的禪理意味。這充分表明,在唐宋審美轉(zhuǎn)型期,文人在佛禪文化影響下所采取的兩種不同的自我解脫方式,這也是王維和蘇軾文學(xué)作品中的佛禪“空”境,能夠進(jìn)一步在內(nèi)在精神追求方面,表現(xiàn)出唐宋不同文化氣質(zhì)的一個(gè)重要原因。
三、美的發(fā)現(xiàn)與性命自得:王維與蘇軾“空”境的內(nèi)在精神
王維詩歌中的“空”境具有較為明顯的禪意妙趣,蘇軾詩詞作品中的“空”境則具有濃郁的禪理意味。借用王國維的“境界論”觀之,王維的“空”境較多表現(xiàn)為一種大寫的“無我之境”,蘇軾的“空”境則較多表現(xiàn)為一種大寫的“有我之境”。
1.物我渾融:王維“空”境的藝術(shù)精神
王維的“空”境,較多表現(xiàn)為由內(nèi)到外的美的發(fā)現(xiàn)。在王維這里,由于“無心”而感受到的“空”“靜”“閑”“幽”,將詩人自我與宇宙自然物象有機(jī)融為一體,渾然天成,物我渾融無礙,在對(duì)宇宙自然一切生命之美的發(fā)現(xiàn)與呈現(xiàn)中,有我而無我,是一種大寫的“無我之境”。在“木末芙蓉花,山中發(fā)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空”境中,人消融于自然山水間,于花開花落中靜觀緣生緣滅。“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shí)鳴春澗中”,人境皆俱,卻又恍兮惚兮,皆無差別。在“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guān)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fēng)吹解帶,山月照禪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的淺吟低唱里,詩人自我與宇宙的窮通變化融為一體,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尤其是“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1]35的隨心任運(yùn)與隨遇而安,將物我打通,融為一體,整個(gè)世界呈現(xiàn)為一片空靈澄澈的境界:“行到水窮處去不得處,我亦便止;倘有云起,我即坐而看云之起。坐久當(dāng)還,偶值林叟,便與談?wù)撋介g水邊之事,相與留連,則便不能以定還期矣。于佛法看來,總是個(gè)無我,行所無事。行到,是大死;坐看,是得活;偶然,是任運(yùn)。此真好道人行履。謂之‘好道’,不虛也。”[23]因此,在王維的“空”境中,我們看不到蘇軾“空”境中那個(gè)總是無處不在的“我”,一次次強(qiáng)化著對(duì)宇宙人生空幻寂滅的體驗(yàn)而使其“空”境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在王維這里,一切“以一種最自然最實(shí)在的方式直現(xiàn),而并不是事先預(yù)設(shè)一個(gè)情感的尺度,在直現(xiàn)出物態(tài)的本然之后,再從中去感悟生命的自然本質(zhì),發(fā)現(xiàn)自我和一切外物最佳的生命方式及狀態(tài)”[24]。這樣的世界既是外在的實(shí)相世界,又是內(nèi)在的心靈世界,是對(duì)宇宙自然萬物及生命存在的“美的發(fā)現(xiàn)”。在這個(gè)美的發(fā)現(xiàn)過程中,自我逐步退出,讓位于自然美的世界,從而使王維詩歌的“空”境中,總是含有一種物我渾融的禪悅審美色彩。這也是王維“空”境內(nèi)在精神追求與蘇軾“空”境內(nèi)在精神追求的最大不同點(diǎn)。
在王維的“空”境中,世界原初的本真自然之美,與詩人不染塵埃的禪悅心境,在物我渾融的統(tǒng)一中,禪意盎然而又不著痕跡。詩人總是能在任運(yùn)自然的無心自在中,即刻與周流不止的自然相融,進(jìn)入物我兩忘的狀態(tài),直抵物我一體的本真之性,實(shí)現(xiàn)生命的詩意棲居。在王維空靈蘊(yùn)藉的“空”境之中,沒有對(duì)生命本質(zhì)空幻寂滅體驗(yàn)的感傷與融通諸多哲理的生存智慧,唯見自然本真的純凈之美,只有心靈與自然的同生共滅、行止與萬境的默契融和所帶來的物我渾融。在“與道合一”的“空”境之中,王維洞見自然之性與自我之性,在人與自然的親和關(guān)系中,體悟到自在精神世界里最高的審美愉悅,也就是自我生命與宇宙自然圓滿融合的、既在世間又超然世外的空靈澄澈之美。正是在這種以物我渾融的禪心來統(tǒng)攝世界美的發(fā)現(xiàn)過程中,王維的“空”境也便具有了“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25]的難以言說的禪意之美。這又從另一個(gè)角度證明了佛禪的般若“空”觀,從來都不是一片毫無生命氣息的死寂,王維因參悟萬法皆空而具備了萬法平等無分別的智慧而消解了分別的界限,使物我渾然一體,空與有、動(dòng)與靜的對(duì)立都可以在禪的意境中融化為一個(gè)圓融無礙的整體,因而其空靈蘊(yùn)藉的“空”境中,蘊(yùn)含著無限的生命靈動(dòng)氣息。
2.生命律動(dòng):王維“空”境的宇宙精神
在“空”境的表現(xiàn)中,王維較多關(guān)注的是將自我融入宇宙流變中獲得物我兩忘的禪悅,較好地契合了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王維“空”境中的幽靜虛空,絕非空無一物的枯槁死寂,而是在充滿生命氣息的禪意盎然之中,氤氳著萬物的勃勃生機(jī)。《鳥鳴澗》的空山靜夜里,花落有聲夜更靜,月出鳥鳴澗更深,在恍若原初的天地深處,自然萬物自在自適,在既是寂寞也是愉悅的情感流動(dòng)中,臻于永恒的生命化境。空山寂靜里自開自落的辛夷花,獨(dú)化獨(dú)存,既為世所忘,又遺世而立,將宇宙自然的蓬勃生機(jī)和生命力,展開為一片寂靜中的繁艷之美。“如此幽靜之極卻又生趣盎然,寫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詩作中,恐怕也數(shù)一數(shù)二。”[26]還有《鹿柴》里幽靜空山之中的人語聲,以及透過森林灑落青苔的夕陽余暉,在動(dòng)靜相生的恍惚迷離中,聲響光色雜錯(cuò)交合,仿佛萬物都在彼此映襯的剎那間跳躍起來,具有一種既空曠幽靜又極富生命流動(dòng)氣息的天地大美。在王維詩歌的“空”境之中,詩人對(duì)自然真如純凈之美的發(fā)現(xiàn),以一種“目擊道存”的審美體驗(yàn)方式,打開了一個(gè)生機(jī)盎然的美的世界,充滿了生命的律動(dòng)與心靈的真趣,在物性、人性與詩性相統(tǒng)一的物我渾融中,達(dá)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審美境界。
對(duì)于王維而言,“心舍于有無,眼界于色空,皆幻也。離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過于色空有無之際。故目可塵也,而心未始同”[1]358-359。也就是說,要真正體認(rèn)“空”的本質(zhì),必須離開“空”與“有”的執(zhí)著,轉(zhuǎn)而在一種非空非有、似有似無、若即若離的色空有無之間,將自然心境化看空,才能真正體認(rèn)世界的實(shí)相。因此,在王維對(duì)“美的發(fā)現(xiàn)”的“空”境之中,他總是能以一種物我渾融的相依共存方式,細(xì)細(xì)體味宇宙萬物的本真自如面目,呈現(xiàn)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律動(dòng)之美。在這種充盈著生命律動(dòng)的“空”境之中,詩人進(jìn)入心靈與宇宙融合為一的天地境界,自然萬物的大有之美,喚醒了詩人對(duì)宇宙自然最詩意化的審美觀照,從而使其詩歌中“空”境的文學(xué)書寫,既是對(duì)佛禪理想化最高審美境界的詩意詮釋,也是對(duì)宇宙生命周流不止永恒之美的呈現(xiàn)。
3.超越存在:蘇軾“空”境的哲學(xué)精神
蘇軾對(duì)于“空”境的內(nèi)在精神追求,往往著意于由外到內(nèi)的性命自得之道。在“空”境的表現(xiàn)中,蘇軾較多關(guān)注的是對(duì)個(gè)體內(nèi)在生命世俗榮辱得失的忘懷超越,形成其文學(xué)作品中不滯于物的自由精神,以及以寬廣胸襟領(lǐng)悟宇宙人生的雍容氣度。蘇門弟子秦觀曾經(jīng)總結(jié)說:“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shí)足以致遠(yuǎn)。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于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爾!”[27]應(yīng)該說,這個(gè)評(píng)價(jià)是比較中肯的。蘇軾詩詞中“空”境所傳遞出來的空幻寂滅意識(shí),大都是在人生經(jīng)歷中由外而內(nèi)悟得,而且這種感悟隨著蘇軾自我人生世事的沉浮走向而變得更加深刻,經(jīng)歷了一個(gè)由感性認(rèn)識(shí)到理性認(rèn)識(shí)的過程。在這個(gè)過程中,“空”境不空,始終隱藏著一個(gè)“我”的存在。蘇軾詩詞中的“空”境面向自我,直指人生,無論是對(duì)人生如夢(mèng)幻泡影的感嘆,還是對(duì)孤高幽獨(dú)自我形象的刻畫,抑或?qū)θ松鸁o法排解苦悶的無可奈何之“閑”的幻想,他始終是一個(gè)心系世事、鐘情正在我輩的性情中人。蘇軾對(duì)人生空幻不實(shí)的體悟,并非為了“出生死,超三乘”[2]1671,從而將人生走進(jìn)一種徹底空漠寂滅的絕對(duì)虛無之中。相反,他恰恰是在參悟般若空觀,了悟宇宙人生的空幻不實(shí)之后,“期于靜而達(dá)”[2]1671,采取一種“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2]1671的方式返回自我內(nèi)心,依靠佛禪的哲思睿智來化解現(xiàn)實(shí)人生的種種苦悶與憂傷,從而在自我內(nèi)心世界中獲得人生的徹底解脫。這也就是蘇軾“空”境中的性命自得之境,是一種對(duì)不斷超越自我有限性存在而獲取人生絕對(duì)逍遙自由的“有我之境”。
因?yàn)?蘇軾雖然對(duì)宇宙人生如夢(mèng)幻泡影般的虛無存在有著深刻而持久的體悟,但是,他也能在“對(duì)一切不做功利價(jià)值關(guān)懷的生命感受和審美觀照”[28]下,做到心境與物境合一的隨緣自適與任運(yùn)自在。如《定風(fēng)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中,經(jīng)過“一蓑煙雨任平生”的任運(yùn)自在過程后,終于能夠于風(fēng)云變幻的萬千世界中超越實(shí)相,而以一顆“無心之心”“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的禪心去直面“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的人生,并最終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超然自得。這就猶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shí),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后來,親見知識(shí),有個(gè)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gè)休歇處,依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29]般,經(jīng)過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后,方能真正體悟到生命的真義,也才能真正地復(fù)歸自我。因此,當(dāng)歷經(jīng)人生種種波折后遇赦北歸之時(shí),蘇軾已經(jīng)沒有了早年“紛紛榮瘁何能久……恍如一夢(mèng)墮枕中”[2]3093的慨嘆,只是云淡風(fēng)輕地說一句:“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2]2440在此意義上說,陳廷焯評(píng)價(jià)蘇軾“休言萬事轉(zhuǎn)頭空,未轉(zhuǎn)頭時(shí)皆夢(mèng)”兩句為“追進(jìn)一層,喚醒癡愚不少”[30],乃是對(duì)蘇軾不避世也不逃世的多重執(zhí)著與超越的深刻理解。
由此可見,蘇軾的“空”境,雖然具有濃郁的空幻寂滅色彩,但他并不是徹底否定一切,而是在“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8]665的經(jīng)歷中,從空幻不實(shí)的萬千世界中反跳回來,如同一個(gè)睿智的哲人一般,以旁觀者的身份俯瞰塵世中的人間萬象,并通過自我主體心靈的靜觀內(nèi)省來超越化解社會(huì)生活中的痛苦與憂患,最終在自我心靈中獲得徹底曠達(dá)超然的解脫,這亦是蘇軾“空”境的深層內(nèi)蘊(yùn)所在,也是蘇軾的“性命自得”之道。
4.隨緣自適:蘇軾“空”境的人生態(tài)度
蘇軾“空”境中的“性命自得”之道,實(shí)際上就是通過佛禪參悟生命本質(zhì)之后,不再執(zhí)著于具體萬物存在,轉(zhuǎn)而以一種“內(nèi)在親證”的價(jià)值自證方式,在生命過程的隨緣自適中任性逍遙,灑脫自在,形成一種無往而不樂的曠達(dá)精神境界。
“人生如夢(mèng)”或“人生如寄”的空幻體驗(yàn),在將個(gè)體存在的有限性視為夢(mèng)幻泡影的同時(shí),也以“萬法皆空”的般若智慧,使蘇軾明心見性,洞見存在的本來面目,從而能夠以坦然心態(tài)破執(zhí)生的煩惱,順性而為,委順于世,隨遇而安,不為外物所動(dòng),不為憂患所擾,以此形成一種更為理性澄明的生命深情:一切窮達(dá)貴賤,不過都是過眼煙云,幻化迅疾,人生亦應(yīng)作如是觀,從而消解生的痛苦,獲得精神的自在解脫。特別是蘇軾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遇,又使得他在飽嘗人生磨難、閱盡人間滄桑的現(xiàn)實(shí)生存處境中,以一種更加樂天知命的內(nèi)省功夫,參悟佛禪真諦,并在一次次的心靈創(chuàng)傷中,不斷向佛禪靠近,借助佛禪智慧,將人生的苦難困厄,化解于內(nèi)心的從容豁達(dá),成就其超然生死的曠達(dá)性格和超脫塵世的詩詞高妙意境。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正是因?yàn)榻邮懿⑽颉叭松鐗?mèng)”或“人生如寄”空幻思想的本質(zhì)后,蘇軾才能以一種泯生死與齊榮辱的平常心,不斷調(diào)整自我心態(tài),并以超然灑脫的態(tài)度來對(duì)待榮辱沉浮與世情百態(tài),也使其詩詞文學(xué)作品中的“空”境,在追求人生解脫的哲學(xué)之思中,體現(xiàn)出一種隨緣自適的人生智慧。這種從無處可逃的存在痛苦與人生苦難中超脫出來的睿智,是蘇軾以“道”為參照,在“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中達(dá)到的“性命自得”之人生化境,也是一種與天地萬物相參而達(dá)于生命自在境界的隨緣自適。
蘇軾從識(shí)盡天命、洞曉事理與飽經(jīng)憂患、遍嘗磨難中而來的隨緣自適,就是其“此心安處”。這種隨緣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主要依靠自我內(nèi)省性體驗(yàn)的精神自得來實(shí)現(xiàn)存在主體與宇宙萬物親和共存的圓滿與自由曠達(dá),“此心安處”自然成為蘇軾自我價(jià)值本體的終極歸宿所在。隨緣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使蘇軾在心無掛礙的廓落曠達(dá)中撫平人生困厄旅途中的心靈創(chuàng)傷。“萬法皆空,人生如夢(mèng)”的空幻感傷并沒有使蘇軾走向心靈的枯槁死寂,而是在“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有限性存在中,于坐臥行走處,參悟佛法禪意,走出一條“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的淡定從容之路。當(dāng)他將這些體悟天地萬物變化無窮之道與自見人生通達(dá)的獨(dú)特感悟?qū)懭朐娫~中時(shí),我們便看到一位深悟佛禪“空”境本質(zhì)的睿智哲人,他始終能以一種法眼看世界的佛禪觀照方式空觀自省,隨緣自適,性命自得,既成就自己對(duì)傳統(tǒng)士人文化人格的超越,也成就其佛禪“空”境文學(xué)書寫的新高度。
結(jié) 語
從王維與蘇軾對(duì)佛禪“空”境文學(xué)書寫的新變可以看出,唐宋審美轉(zhuǎn)型在具體文學(xué)作品中的差異性走向,是諸多內(nèi)外因素互為因果、雙向互動(dòng)的復(fù)雜過程。由于構(gòu)成“空”境文學(xué)書寫的“靜”“閑”“幽”三個(gè)主要情感要素的不同表現(xiàn),在整體上使王維與蘇軾形成了空靈蘊(yùn)藉與空幻寂滅兩種不同審美特色。王維通過以畫入詩方式形成“空”境,自我逐步退出,讓位于自然美的世界,在物性、人性與詩性相統(tǒng)一的物我渾融中,詩人以清凈之心面對(duì)宇宙天地的任運(yùn)自然,最終達(dá)到與道合一的最高審美境界,呈現(xiàn)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律動(dòng)之美,具有一種既在世間又超然世外的空靈澄澈之美。蘇軾通過以禪入詩方式形成“空”境,其萬境歸空的總體狀態(tài)與幽寂感傷的情感色彩更多指向人生,著意在宇宙人生空漠幻滅的悲劇意識(shí)與人事滄桑的經(jīng)歷中探尋自我解脫的性命自得之道,內(nèi)含超越有限存在的哲學(xué)精神和隨緣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具有明顯的學(xué)問化與思辨性色彩。
王維與蘇軾對(duì)于佛禪“空”境的不同文學(xué)書寫,使來自佛禪領(lǐng)域相對(duì)抽象的“空”觀義理,在唐宋文人的藝術(shù)作品中,成為具有“唐音”“宋調(diào)”兩種不同審美氣質(zhì)的文學(xué)意境,在主情與尚意、情性感悟與學(xué)識(shí)才力、禪意之趣與理趣之美等方面,折射出唐宋審美轉(zhuǎn)型的歷史性存在。因此,唐宋社會(huì)變革的發(fā)生,不但塑造了以王維和蘇軾為代表的唐宋文人及其文學(xué)藝術(shù)的不同文化精神品格,也是形成“唐音”與“宋調(diào)”兩種不同經(jīng)典審美范式的重要原因,是我們理解整個(gè)唐宋文學(xué)新變時(shí)無法繞開的思想史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