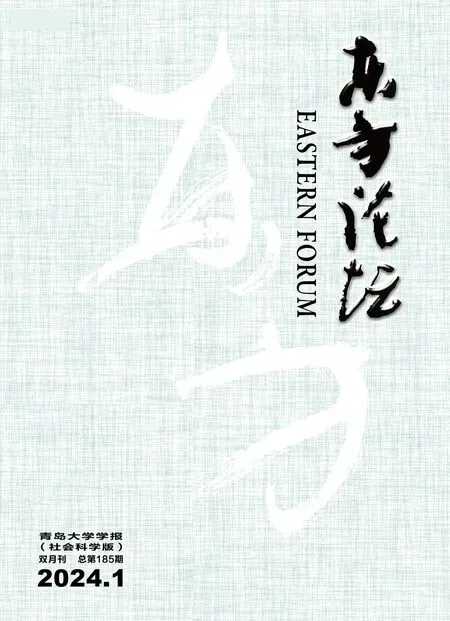“美”的轉(zhuǎn)向與超越:莊子“悲態(tài)”美學(xué)思想闡微
王康寧 薛振宇
1.山東師范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部,山東 濟(jì)南 250014;2.新興際華集團(tuán)有限公司 綜合部,北京 100020
美學(xué)中的“悲態(tài)”是一種審美意境,“悲態(tài)”之美在于人們能夠超越否定性的“悲”本身,升華出令人愉悅和享受的精神體驗。這意味著“悲態(tài)”中不僅有“消極”和“否定”,也有“積極”和“肯定”的成分,而后者是確證“悲態(tài)”哲學(xué)內(nèi)涵與價值的重點。審美范疇中的“悲態(tài)”與作為藝術(shù)形式的“悲劇”以及表征情感的“悲感”差別迥然。前者具有哲學(xué)思辨和形上追問的意旨,后者則主要關(guān)涉世俗人生的悲楚與痛苦。徐鍇《系傳》曰:“心之所非則悲矣。”①黃建中、胡培俊:《漢字學(xué)通論》,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0 年,第355 頁。“悲”以“心非”之否定情態(tài)為特性,統(tǒng)指消極否定的情感與觀念以及由其引發(fā)的一系列有違意愿或意志的形態(tài)或狀態(tài)。“美學(xué)悲的悲態(tài),是一種偏離的悲,是感到人與社會,人與宇宙對立一面時的悲,是帶有詢問的哲學(xué)高度的悲。”②張法:《美學(xué)導(dǎo)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 年,第113 頁。“悲態(tài)”以“悲”為起點,是經(jīng)由對世俗之“悲”的超拔與升華而達(dá)至的精神高境。其中富含的深旨妙義既可被視作生存狀態(tài),也是現(xiàn)代人通達(dá)與實現(xiàn)自我的重要標(biāo)志。
一、《莊子》“悲態(tài)”美學(xué)的理論溯源
“悲態(tài)”是貫穿《莊子》的基調(diào)與主旋律,莊子重“悲”且從中開出一條超越性的思維路向。以“悲”為中心概念或情感筆觸,《莊子》中既有“悲感”的情態(tài),也有“悲劇”的藝術(shù)內(nèi)涵。司空圖概括古體詩歌的“悲慨”道:“大風(fēng)卷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撫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③孫聯(lián)奎、楊廷芝:《司空圖〈詩品〉解說二種》,濟(jì)南:齊魯書社,1980 年,第38 頁。“大風(fēng)卷水,林木為摧”,是對自然之悲的描摹;“適苦欲死,招憩不來”,是對人生之悲的嘆息;“百歲如流,富貴冷灰”,是對生命之悲的揭示;“大道日喪,若為雄才”,是對社會之悲的揭露;“壯士撫劍,浩然彌哀”,是對個體之悲的闡發(fā);“蕭蕭落葉,漏雨蒼苔”,是借景象之悲映射心理與精神之悲。司空圖區(qū)區(qū)48 個字將宇宙—自然—社會—人生—個體—心理之“悲態(tài)”予以淋漓盡致的闡釋。由是觀之,“悲態(tài)”是個體生存的必然環(huán)境和條件,個體所處的時空條件和心理狀態(tài)則是悲態(tài)產(chǎn)生的緣由。
(一)以“有涯”應(yīng)“無涯”:無限宇宙與有限自我的矛盾
莊子“齊物”的前提是“天—人”的同源性,“天與人,不相勝也”(《莊子·大宗師》)。然而,“天—人”在存在形式上的非對等性也必然致使“合一”的有限性。在《莊子·養(yǎng)生主》中,造成這種有限性的根本原因是人之生存局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在“無涯”之宇宙自然的反襯下,個體人生之瞬時短暫尤為凸顯,由此衍生的“悲態(tài)”注定是個體人生不可回避的必然。“正由于對自己‘此在’的珍視,知覺自己存在的‘有限’和追求超越此有限存在,便與‘時間’處在尖銳矛盾以至斗爭中。”①李澤厚:《人類學(xué)歷史本體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8 年,第123 頁。面對有限自我與無限宇宙之間的鴻溝,人不免生出“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也”(《莊子·齊物論》)的迷思與慨嘆,無以復(fù)加的悲態(tài)也似乎成為籠罩人生的主宰。“只有在人的有限性、暫時性和不可重復(fù)性的背景上,失意才與哲學(xué)意義有聯(lián)系。”②張法:《美學(xué)導(dǎo)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 年,第114 頁。宇宙自然之于人的不可違逆和抗衡性,以及人對宇宙自然的難以盡知盡能,時刻伴隨著“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莊子·達(dá)生》)與“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莊子·齊物論》)的哀傷與無奈,而人在“悲態(tài)”中求突圍又進(jìn)一步渲染與強化“悲態(tài)”的主題與氛圍,從而將人生與“悲態(tài)”緊裹。
(二)“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對缺乏普世價值和共同倫理的哀嘆
莊子以“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概括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背景。雖然學(xué)界有關(guān)“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的解讀莫衷一是,但認(rèn)為莊子以其表達(dá)“亂世”主張卻基本無異。莊子對“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作過隱喻:“昔者十日并出”(《莊子·齊物論》)。“十日并出”既可視作莊子對“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的結(jié)論性描述,也是莊子對價值解體、秩序混亂、道德不一的現(xiàn)實社會的形象化摹寫,其真正意旨在于揭露普世價值和共同倫理的淪喪。莊子詳細(xì)闡釋過“天下之亂”與“文化觀念之亂”或“倫理價值之亂”之間相生相依的關(guān)系:“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好,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莊子·天下》)“社會之亂”與“文化之亂”或“倫理價值之亂”之間,從來沒有明顯的先后彼此之分。當(dāng)周遍之道盡毀而“一曲之士”遍存時,各有所持的觀念與行為必然導(dǎo)致人際關(guān)系的疏離,造成人世社會的爭斗與混亂。莊子之時的荒唐世道與險惡人心以“分”“裂”的形式淋漓盡顯,“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論》)。渾然為一的宇宙秩序與自然法則,一旦被“有心”者做目的性的割裂與取舍,其結(jié)果只能如被鑿出“七竅”的“混沌”般,走向“死”的末境是必然結(jié)局。誠如黑格爾所說:“基本的悲劇性就在于這種沖突中對立的雙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辯護(hù)理由。”③[德]黑格爾:《美學(xué) 第3 卷 下》,朱光潛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1 年,第286—287 頁。莊子對因倫理價值解體而導(dǎo)致的社會亂象痛心疾首,在其有關(guān)人事之分的書寫中飽含著深重的憂思與悲患。
(三)“喪己于物”與“失性于俗”:對眾人生存悲境的嗟吁
成玄英先生疏解《莊子·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曰:“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圣跡,黥鼻無刑,遂使桁楊盈衢,殊死者相枕,殘兀滿路。相推相望,明其多也。”①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jīng)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第218 頁。面對天下洶洶顛連無告的不堪境況,莊子之所以予其以深刻揭露與批判,究其根本在悲憫心。承襲老子的理論主張,自然人生觀亦為莊子所秉持。在老莊思想中,自然暢意的人生以對自然本性的順應(yīng)與持守為原則。然而,“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皆有余”“昭昭”“察察”“皆有以”(《老子》第20 章)以及“終身役役”“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莊子·齊物論》)的“眾生”沉淪樣態(tài)與自然人性之間差之千里。“喪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民”或“蒙蔽之民”(《莊子·繕性》),以思想和精神的沉淪下陷為本質(zhì)特點,以“滑欲于俗”為生存方式,服從于機心、巧智的干涉乃至宰制。“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莊子·齊物論》)“‘間間’之知,‘詹詹’之言,無時不在伺察、交接當(dāng)中。諱莫如深的提防,秘藏深因。與封閉提防相伴隨的是各種形態(tài)的恐懼。‘心斗’和恐懼指向自我界限的強化和封閉,這一沒有確定性的自我邊界往往被執(zhí)以為實。”②楊立華:《莊子哲學(xué)研究》,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0 年,第41 頁。疏離與違背自然本性的眾人不得不承受自身非自然言行的戕害,“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gòu),日以心斗”(《莊子·齊物論》)。無底線的縱欲和恣行只能導(dǎo)致更深程度的自我遮蔽和自我迷失,而人們對身陷彷徨與掙扎之悲境的全然不知或迷惑不解,實乃蘊藏在鏡像之悲后的更為深徹的“悲態(tài)”。
(四)“獨有”者的“獨來獨往”:悵然失落的個體心理
尼采對人之悲做過終極追問,認(rèn)為悲之根本因由“在于其造物的狀態(tài)”和“造物者的思辨沖動”③周國平譯:《悲劇的誕生 尼采美學(xué)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6 年,第15 頁。。“思辨—悲態(tài)”既表明“悲態(tài)”之于個體人生的必然性,也表明思辨深度與“悲態(tài)”程度之間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悲態(tài)”之生成不僅取決于客觀環(huán)境的影響和渲染,更取決于主觀心理和思想。“思辨—悲態(tài)”之間“原因—結(jié)果”的直接關(guān)聯(lián),意味著個體越是具有哲人思維,其于“悲態(tài)”的體認(rèn)和感觸愈明徹。顯然,莊子對悲態(tài)的敏感度和洞察力遠(yuǎn)遠(yuǎn)超越一般人。畢竟,將“未來”和“過去”都納入概念思考的范圍,意味著認(rèn)識將廣大范圍內(nèi)的各種痛苦照亮,因而人的痛苦也就急劇增長④劉興章:《論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身體理論——兼評叔本華的悲情人生觀》,《求索》2014 年第4 期。。《莊子》的“悲態(tài)”哲學(xué)與莊子本人博古通今的開闊思維、達(dá)天入地的廣大視野和上下求索的哲人精神密切關(guān)聯(lián)。莊子對“獨”傾注大量筆墨,視其為理想的人格特質(zhì)和生存樣態(tài)。“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逍遙游》),“獨來獨往,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莊子·在宥》)。與其說莊子重“獨”,毋寧說“獨”是道家人格的核心特質(zhì)。《老子》第20 章中區(qū)別于“眾人”的“我”,便是“獨來獨往”的典型代表。老莊所謂的“獨有之人”,統(tǒng)指“獨守道”、抱持不入俗流之“獨特”人格者。這類“獨有”者相比于陷于流俗的“眾生”,思想和精神往往獨立與“孤寂”。概觀莊子之時“仁義之士”遍存的社會環(huán)境,莊子的“重獨”在表達(dá)觀點的“獨特”性之余,也傳遞出自身理論為人們忽視或冷落的“孤獨”境遇。“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圣人被褐懷玉。”(《老子》第70 章)。這種以自我為起點而衍生出的“悲態(tài)”,是莊子“悲態(tài)”哲學(xué)形成的深層原因。
二、《莊子》“悲態(tài)”美學(xué)的形式與內(nèi)容
徐公持先生認(rèn)為承繼于先秦的漢代文學(xué)的“悲情”是彌漫整個漢代的文壇風(fēng)氣。“悲態(tài)”也是道家思想的一貫風(fēng)格,其集中體現(xiàn)為老莊對“悲態(tài)”的哲學(xué)沉思與闡釋。《莊子》的“悲態(tài)”有多樣化的形式和內(nèi)容。經(jīng)由呈現(xiàn)“悲態(tài)”而揭示浩瀚玄遠(yuǎn)的哲思與真諦,以及引發(fā)人們豁然通達(dá)的精神體驗,既可被視為莊子“悲態(tài)”哲學(xué)的邏輯進(jìn)路,也可被視作其特有的表達(dá)手法和書寫技巧。
(一)難以逾越的天然局限:作為生存境域與心理樣態(tài)的“無”
批判世俗之“有”而肯定“無”之“大用”,是老莊的一貫邏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莊子·齊物論》);“去知與故,循天之理”(《莊子·刻意》)。“故”本為“有意而為”,可引申為“詐偽”①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第540 頁。。老莊揭露機心、巧智、物欲蒙蔽自然性的實質(zhì),主張人們經(jīng)由“日損”“損之又損”(《老子》第48 章)的功夫促成自然本質(zhì)的“澄明”,從而達(dá)到“無己”“無功”“無名”“無情”(《莊子·德充符》)的境界。然而,人們之于“無”的體認(rèn)與獲得是充滿艱辛和曲折的過程,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夠通過“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莊子·大宗師》)的方式實現(xiàn)“同于大通”(《莊子·大宗師》),通達(dá)“無”之妙境。由世俗之“有”與終極之“無”間的懸殊而導(dǎo)致的“求道”過程之艱難,極度渲染了“無”之境界的深晦,也為人生理想的實現(xiàn)增添了諸多困惑與艱辛。
“無”不僅被莊子視為理想的精神高地和生存高境,也被用作描述人的心理樣態(tài)和情感體驗。“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莊子·在宥》)郭象認(rèn)為:“窈冥昏默,皆了無也。”②郭象注,成玄英疏:《莊子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208 頁。“愚芚”(《莊子·齊物論》)的圣人,“如嬰兒之未孩”(《老子》第20 章)般純真質(zhì)樸,絲毫不受情感的牽絆和束縛。然而,人本質(zhì)上是“有”,是立于天地之間的“實在”,有其難以避免的“阿喀琉斯之踵”。“人被毫無來由的‘拋’在這個世界上,鬼神不可靠,死亡不可知,人因此陷入絕對的虛空。這造就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悲劇意識。如果說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那也是悲極而樂(選擇樂)的文化。”③冷成金:《“向死而生”:先秦儒家道家哲學(xué)立論方式辨正——兼與海德格爾的“為死而在”比較》,《中國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2012 年第2 期。現(xiàn)實人生極難脫離“有”的范疇,“無”之深奧晦澀也較難與尋求安定執(zhí)守的人類心理間形成真切關(guān)照。如同“罔兩問景”(《莊子·齊物論》)中被動而虛幻的“影子”必須以實體為依據(jù),“無”與“有”也是相反相成的統(tǒng)一體。“有無相生”(《老子》第2 章),離開“有”談“無”,意味著“無”之合理性的自動消解。雖然“罔兩問景”有彰顯本質(zhì)之“無”而弱化個體之“有”的意旨,但也明確表明“無”與“有”的本質(zhì)與現(xiàn)象之間相生相依、相互證成的關(guān)系。此外,莊子對擁有“無”之心境和狀態(tài)的“神人”“至人”“真人”的多維度刻畫與描寫,雖能為人們的超越性發(fā)展提供指引,但也真切地反映出其作為理想狀態(tài)的難以企及,從而似乎在以一種反襯的手法強化現(xiàn)實中人不可逾越的“天病”——天賦局限。
(二)短暫而荒誕的人生:片段性和戲劇化的“生”
莊子重生,以“養(yǎng)生”為主題的“養(yǎng)生主”闡述的是合理之生的原則與方式。在《莊子》中,萬物在“生”處獲得絕對意義上的等同,“齊物”“齊一”的前提是對“生”的尊重與珍視。不同于世俗之人“厚生—養(yǎng)生”的生命觀和生活方式,莊子基于對自然生命的倡導(dǎo)而極力反對“厚生”:“悲夫!世人之以為養(yǎng)形足以存生”(《莊子·達(dá)生》)。誠所謂“五色亂目,使目不明”(《莊子·天地》,由生命有限引發(fā)的“厚生”是盲目恐慌的表現(xiàn),其不僅無益于生命本色的彰顯,反而對人之生具有不可逆轉(zhuǎn)的危害。這種對待生命的不當(dāng)行為,在莊子看來只能導(dǎo)致生之悲。“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莊子·人間世》)不可企及的“來世”與“往世”將人逼促于短暫的“現(xiàn)世”之中。莊子的“重生—養(yǎng)生”以“生”之有限為思想和情感依據(jù)。“天下歡之日短而悲之日長,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長,此定局也。”①謝柏梁:《中國悲劇美學(xué)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108 頁。由生之瞬時和短暫,珍視生命與熱愛生活也便顯得“不可待”,而由此引發(fā)的諸種“厚生—害生”的觀念與行為,復(fù)又使得本就短暫的生命附加不可承受之輕。
倘說莊子以生之短暫證成人生之悲態(tài),進(jìn)而由中生發(fā)出“生”的無限可能的話;以“生”之忽而與荒誕反襯人生之艱難與沉重,則體現(xiàn)出莊子“悲態(tài)”哲學(xué)的宛轉(zhuǎn)進(jìn)路。“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莊子·大宗師》);“俄爾子輿有病,喘喘然將死”(《莊子·大宗師》)。生與死的界限只“莫然有間”與“俄而”,此不免令人悲不自禁。《莊子·至樂》中,莊子喪妻后“箕踞鼓盆而歌”,惠施道:“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以,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對此,莊子回應(yīng)道:“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針對莊子對“鼓盆而歌”的“辯護(hù)”,人們多關(guān)注其中的“齊生死”觀點,并因此認(rèn)為莊子超越世俗生死觀以至于面對至親的離世并無悲感。然而,惠施以“禮”之“表”對應(yīng)莊子的外在行為,不僅忘卻“禮”之實質(zhì),也難以窺見莊子之真實心理。“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雖而哭之,自以為不同乎命”,通曉死之自然與必然而后止悲,定然離不開理性之于感性的強力克制。莊子的“欲悲而不能”反而隱藏著極為深重的悲痛。“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②黃周星、王岱:《黃周星集·王岱集》,長沙:岳麓書社,2013 年,第162 頁。看似荒誕的“鼓盆而歌”,何嘗不是莊子之悲的極端表現(xiàn)形式;莊子之歌,又何嘗不是如泣如訴的大悲歌。
(三)復(fù)雜而有待的自我:受限與無力的“身心”
莊子“悲態(tài)”產(chǎn)生的根源性動因是人對自然天性的悖離,以非自然方式生存的必然結(jié)果是“有待”。在《莊子》中,世間萬物絕大多數(shù)都“有待”,就連“御風(fēng)而行”(《莊子·逍遙游》)的列子也有依憑和借據(jù)。真正的“無待”者只有道、天地以及極少數(shù)得道的“至人”“真人”。莊子致力于刻畫與描述的主體以“有待”者占大多數(shù),如身體殘缺者、智識有限者、道德缺失者等,而其對“有待”者的生存境遇的揭示,也使得艱辛、無奈、困頓等的悲況與悲像盡顯。
“井蛙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莊子·秋水》)楊國榮教授以“井蛙”“夏蟲”“曲士”比喻不同存在形態(tài)的人,認(rèn)為“拘于虛”“篤于時”“束于教”分別對應(yīng)“受制于特定環(huán)境”“為一定的歷史條件所限制”“片面性的思想、觀念對人的影響”③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 年,第111 頁。。在生之局限性上,人與井蛙、夏蟲并沒有本質(zhì)差別,區(qū)別在于人之束縛和局限往往是主客觀因素綜合導(dǎo)致的結(jié)果。“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④王國維:《王國維文學(xué)論著三種》,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0 年,第12 頁。受制于外物和自身的限制,人總要面對不可預(yù)測和無法抗衡的“不得不”之“悲態(tài)”。在《莊子》中,智識、視野和道德的“有待”既是“悲態(tài)”的表現(xiàn)形式,也是導(dǎo)致“悲態(tài)”的根本原因。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夫知亦有之。”(《莊子·逍遙游》)面對接輿對“藐姑射山神人”的“質(zhì)疑”,連叔以目盲、耳聾之人的感官局限對應(yīng)接輿淺顯的見識,表明凡俗之人與得道者認(rèn)識層次的天壤之差,從而勾勒出“藐姑射山神人”令人心生向往的生存樣態(tài)。智識有限,不解與疑惑便難以消解,由此引發(fā)的心理、思想、精神、行為之緊張、局促、困頓等“悲態(tài)”也便是“常態(tài)”。針對蜩與學(xué)鳩對鯤鵬“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莊子·逍遙游》)的不解與嘲笑,莊子用“行路備糧”的隱喻揭示蕓蕓眾生重眼前實際而忘長遠(yuǎn)未來的局限視野。這也是“小大之辯”對個體局限性的形象揭示。視野之差別導(dǎo)致人們觀念與行為之差異,進(jìn)而導(dǎo)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嫌隙、矛盾旁生不斷、此起彼伏,此無疑是現(xiàn)實中人時常面臨與應(yīng)對的“悲態(tài)”。“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莊子·天地》)“機事”者究其根本是“人為”之事,為則偽矣。“機心”重則“道心”淺,道德發(fā)展便難入無為之妙境。在老莊語境中,硬性、人為、外在的“機事”必然損傷與戕害柔軟、自然、內(nèi)在的道德,“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好知”(《莊子·胠篋》)。“機心”導(dǎo)致的道德危機始終以或顯或隱的方式,增加與深化著人類“悲態(tài)”的形式和內(nèi)容。
三、《莊子》“悲態(tài)”美學(xué)價值的生成路徑
在對“悲態(tài)”的描述和表達(dá)方面,莊子是毫不保留與淋漓盡致的;在對“悲態(tài)”的態(tài)度和方式上,莊子無疑極為積極與樂觀。莊子重“悲”卻不迷執(zhí)于“悲”,而是積極尋求多種突圍“悲態(tài)”的方式和途徑。經(jīng)由“下沉-升華”的過程,莊子將“悲態(tài)”與大化流變的宇宙人生相關(guān)聯(lián),從“悲態(tài)”中超拔與升華出關(guān)乎個體自我、宇宙自然的積極精神體驗和價值觀念。勇于突破、消解和超越天賦或后天“悲態(tài)”,此既是《莊子》“悲態(tài)”哲學(xué)的內(nèi)在歸旨,也是其現(xiàn)實關(guān)懷的真切表達(dá)。
(一)怒生:化悲為力
區(qū)別于“無為”“自然”“順應(yīng)”等的道家概念,“怒”是理解《莊子》的獨特維度。倘由“虛無”“順命”中可導(dǎo)出消極“避世”或“出世”思想主張的話;在“怒”處,則可明確得見莊子對主體性的高度持重與認(rèn)可,從而也能夠抽繹出莊子思想積極“入世”的內(nèi)涵和特點。以“怒”的方式打破“生”之種種“悲態(tài)”,促成“生”之“綻放”,是莊子“怒生”觀的核心意旨。
“怒”字最早見于《莊子·逍遙游》,在描述“鯤鵬南徙”時,“怒而飛”用以表明“鵬”之飛的動作與態(tài)勢。“怒,鼓怒翅翼”①楊柳橋:《莊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2 頁。,以“怒”為修飾,“鯤鵬之化”是鯤鵬奮力突破局限并實現(xiàn)超越的主動行為。“‘怒’中有主動的奮發(fā)、振起,在‘怒生’中充盈著的是上達(dá)之沖動與不可遏制的生長趨勢”。②陳赟:《〈莊子〉“小大之辯”兩種解釋取向及其有效界域》,《學(xué)術(shù)月刊》2019 年第8 期。鯤鵬之“怒”飛是一種在原始力量促動下的行為,其中蘊含著機體的勃勃生機與奮力行動。在主動之“怒”中,鯤鵬實現(xiàn)“圖南,且適南冥”的宏愿,達(dá)至“逍遙”之高美意境。
不同于鯤鵬的“怒而飛”,蜩與學(xué)鳩之“飛”是“決起而飛”,斥鴳則是“騰躍而上”。“怒而飛”“決起而飛”“騰躍而上”雖在形式和狀態(tài)上存在差別,但蜩與學(xué)鳩之“決起”、斥鴳之“騰躍”與鯤鵬之“怒”都是對奮力、竭力之主體行動的摹寫與表達(dá)。如同鯤鵬,蜩與學(xué)鳩、斥鴳也是在竭力的“決起”與“騰躍”中突破各自之局限而實現(xiàn)“飛之至”,達(dá)到觀念與行為的極致境地。莊子善以自然事物比擬個體人生,郭象注“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莊子·外物》)曰:“青春時節(jié),時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①郭慶藩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826 頁。鳥獸、草木尚且“怒生”“怒飛”,人之“怒生”更是促成個體擺脫局限、實現(xiàn)自我的根本方式。
(二)顯用:以悲為用
符合中國古典哲學(xué)“藏體顯用”的一貫特點,莊子重視“用悲”。《莊子》中的諸多人物和事物都能憑借“用悲”而盡性全生。比如,“匠者不顧”的“樗”、“無用”之“大瓠”(《莊子·逍遙游》)、“支離疏者”(《莊子·人間世》)等皆因“悲”生“喜”,由世俗之悲處得其天年。
《莊子·逍遙游》中,莊子在指出惠子“瓠”“樗”之困的根本原因在“拙于用大”后,給出疏解郁結(jié)的根本方式——“以無用為用”:“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游于江湖?”“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xiāng),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頓哉!”以“無用”為“大用”,關(guān)鍵在于積極轉(zhuǎn)變對待“無用”的消極與否定態(tài)度,改變看待“無用”的視角,從而發(fā)現(xiàn)“無用”之妙處。“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莊子·人間世》),皆因“無用”而悲戚,莊子卻因“無用”而歡欣,“以無用為用”體現(xiàn)出老莊的“反向”思維進(jìn)路。
莊子不執(zhí)著于“有”之用,而是在否定“有”之暫時與不確定性后,將視野集中在“無”處,認(rèn)為生萬物的“無”乃是真正的“大用”。“反者道之動”(《老子》第40 章),一旦意識到事物發(fā)展的“反向”“返回”的必然規(guī)律,則由消極否定的世俗“無用”之“悲”處必然能夠?qū)С龇e極美善之“喜”與“樂”。面對“大瓠”與“樗”,莊子生發(fā)的不是極端的“掊之”與揮之不去的“困頓”,而是乘“大樽”而“浮游于江湖”以及“彷徨乎無為其側(cè),逍遙乎寢臥其下”的“逍遙”心境,其中之暢然自適不可不謂高美之境。
(三)待時:悲中候運
《莊子》的“待時”具有順應(yīng)時勢和等待時機的雙重含義,其以對外部時勢的順應(yīng)為前提,實質(zhì)則是在順應(yīng)時勢的前提下等待機緣以行動。“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莊子·齊物論》)以及女偊答南伯子葵問話(《莊子·大宗師》)中多次出現(xiàn)的“守”字,皆確證了“順時”“待時”之于“得道”的重要意義。由于“悲態(tài)”總是以必然和偶然的形態(tài)持續(xù)存在,故而以“順時”的方式積極應(yīng)對“悲態(tài)”是莊子極力倡導(dǎo)的理想人生態(tài)度和價值取向。
《莊子·養(yǎng)生主》中的“庖丁”,是“順時”者。庖丁之“順時”可被理解為“順勢”,即順應(yīng)牛之機體的內(nèi)在走勢。在“見全牛”至“不見牛”的漫長歷程中,庖丁定然面臨和經(jīng)歷過諸多疑惑與困頓,所幸之處在于庖丁始終秉持“順勢”的原則不斷精進(jìn)技藝。經(jīng)由不斷摸索和積累經(jīng)驗,庖丁之技藝最終通達(dá)“游刃有余”之道境,傳遞出“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jīng)首之會”的和諧美感。至于庖丁解牛后的“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則可被視作個體經(jīng)由消解或化解“悲態(tài)”而實現(xiàn)理想預(yù)期后的積極心靈享受和精神體驗。
《莊子·逍遙游》里的“鯤鵬”,同樣經(jīng)由順應(yīng)和把握時勢而實現(xiàn)突破與超越。“徙于南冥”確然不能憑借“鯤鵬”一己之力實現(xiàn)。“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fēng),而后可以南徙也。”②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2—3 頁。“海運”并非鯤鵬“徙于南冥”的原因,而是垂天之翼依憑而起的條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易傳·艮·彖》)倘若沒有“海運”這一契機,單憑“不知其幾千里”的“鵬之背”和“若垂天之云”的“翼”,絕不可能“適于南冥”。然而,倘若鯤鵬沒有“絕云氣,負(fù)青天”的意志、能力和行動,徒有“海運”之條件,則亦不會“適于南冥”。“鯤鵬之化”的隱喻表明,在“順時”的前提下通過自覺而合理的行為突破“悲態(tài)”的限制,是實現(xiàn)與超越自我的必然途徑。
(四)順命:安悲若命
人人都有突圍“悲態(tài)”的內(nèi)在需求,也有各不相同的“突圍”方式。有身體力行者,有善于轉(zhuǎn)化和利用客觀條件者,有善待時而動者,也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莊子·人間世》)者。莊子認(rèn)同并主張“順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在莊子看來,接受與順應(yīng)命運是道德達(dá)至高點的標(biāo)志。
以莊子之力倡“自然”而言,“安之若命”無疑最“自然”;以人對宇宙天地本源和終極地位的體認(rèn),個體也定然是“不可奈何”者。“不可奈何”是對人之勢能的否定,其之于人而言是必然性的“悲”。然而,由必然之悲轉(zhuǎn)向“安之若命”的柔和生存樣態(tài),既非逃避或回避“悲態(tài)”,亦非在“悲態(tài)”中沉淪與墮落,而是以一種柔性迂回的方式安置自我身心。莊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是傳達(dá)“被動”的人性和人生觀,而是意在彰顯人對合于“道”之理想生存樣態(tài)的主動選擇權(quán)。人不是被動的“不可奈何”與“安之若命”,而是在理性確認(rèn)的基礎(chǔ)上,主動回歸自然、平靜、淡泊的生存理念與生活方式。誠然,只有在主動與主體的意義上,人才能成為區(qū)別于動物與事物的“德之至”者。
《莊子》中的主體因“順命”“安命”而受到關(guān)注與認(rèn)可。《莊子·大宗師》中靜待造物者施化的“畸人”意而子,將自身缺陷的補救完全訴諸于造物者:“夫無莊之失其美,據(jù)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爐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之以隨先生邪?”面對身體的殘缺之悲,意而子并非毫不在意,否則不會在“無莊之失其美”“據(jù)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的“悲”例中尋求自我安慰,也不會因?qū)χT此之“悲態(tài)”的思索而總結(jié)出“皆在爐錘之間”的原理和規(guī)律。然而,對比世俗之人沉浸于“悲”乃至于為“悲”所摧毀的情形,意而子的“安之若命”充滿著樂觀與豁達(dá)。這在相當(dāng)程度上弱化了因身體缺陷而導(dǎo)致的心理和思想困境,從而使人生充滿希望與期待。“畸人”意而子的“順命”既是大悲之后的覺醒,也是個體思維觀念不得已的“大轉(zhuǎn)向”。由此“轉(zhuǎn)向”,人之生才能真正擺脫外物的牽絆與束縛,從而駛向豁然通達(dá)的自我—自由之境。
四、《莊子》“悲態(tài)”美學(xué)的現(xiàn)實鏡鑒
有學(xué)者指出,“在人性面前,三千年的時光幾乎沒有什么威力”“有時古典文學(xué)作者比現(xiàn)在的文士還要更明智勇敢”①鐘叔河:《周作人文選 1898—1929》,廣州:廣州出版社,1995 年,第480 頁。。《莊子》的學(xué)說魅力和藝術(shù)光華在歷史長河中的持續(xù)蔓延,與其顛撲不破的時代通用性密不可分。莊子的“悲態(tài)”與現(xiàn)代社會的“悲態(tài)”在實質(zhì)、內(nèi)容、形式等方面的互通性,既是促成莊子“悲態(tài)”哲學(xué)現(xiàn)代性表達(dá)的基礎(chǔ),也可為現(xiàn)代人理性體認(rèn)、預(yù)防、消解和利用“悲態(tài)”提供有益鏡鑒。
(一)認(rèn)識自我:“悲態(tài)”的解蔽與澄明
無論是在專門的哲學(xué)理論中還是經(jīng)由對日常生活的體悟,人們都會時常感受和經(jīng)歷作為人生有機組成部分的“悲態(tài)”。以消極和否定為特性的“悲態(tài)”是人們無可逃脫的生存環(huán)境。既然“悲態(tài)”之于人是必然現(xiàn)象,那么個體對于“悲態(tài)”的理性認(rèn)識則是個體獲悉自我的重要內(nèi)容和途徑。“逃避”對于“悲態(tài)”的感知,雖是一種自我心理防御機制和普遍的心理現(xiàn)象,但忽略或否定“悲態(tài)”也是拒絕認(rèn)識自我的表現(xiàn)。其結(jié)果是自我人生的模糊和失控,以及人們在“悲態(tài)”中的麻木與沉淪。由“悲態(tài)”的消極和否定性而言,認(rèn)識“悲態(tài)”即是勇于與不理想的自我“照面”,由此關(guān)于自我的模糊認(rèn)識會得到“澄明”;由“悲態(tài)”作為哲學(xué)思索的結(jié)果而言,認(rèn)識“悲態(tài)”也即經(jīng)由哲學(xué)沉思走向自我“解蔽”,由此自我意義與價值會獲得更加清晰的顯現(xiàn)。
認(rèn)識“悲態(tài)”就是認(rèn)識自我,“風(fēng)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莊子·齊物論》)人各有悲,悲各不同,認(rèn)識“悲態(tài)”需要堅持個體性原則。以自身之悲為認(rèn)識對象能夠最大程度的調(diào)動感官和心理的作用,從而更有助于個體從中獲知生存與發(fā)展的真諦,并賦予自身之悲態(tài)以特殊而切己的意義和價值。《莊子》中具備自然德性的主體都能在對自身“悲態(tài)”的中肯認(rèn)識中掘發(fā)出有關(guān)自我人生及社會人世的一般原理,從而能夠隨性養(yǎng)身、符道合德。“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莊子·大宗師》)以對宇宙自然之強力與自我身心之局限的理性認(rèn)識為前提,人才能夠合理對待和安置自我。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荀子·正名》)人是群居者,對于自我的認(rèn)識既可以通過體認(rèn)自我之“悲”的途徑實現(xiàn),也可以通過間接感受與體認(rèn)他者之“悲”的方式獲得。“有人之形,故群于人”(《莊子·德充符》),與他人共處是人的必然本質(zhì)和天然需求。這種個體的群居宿命使得“悲態(tài)”往往具有“群體”屬性。莊子對個體“悲態(tài)”的描述背后隱藏的是“群像之悲”。抑或說,個體之“悲態(tài)”是他人乃至全體之“悲態(tài)”的典型代表與具體呈現(xiàn),由個體之“悲態(tài)”可推至群體之狀態(tài)與處境。人對他人之悲的體認(rèn)并非全然依靠“有意而為”,心理機制的相通性為人們的感同身受提供原始依據(jù)。“惻隱是一種道德感情,而且可以說是一種最原始的道德感情。”①何懷宏:《良心與正義的探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57 頁。由同情心和同理心引發(fā)的共鳴與共情,為人們以“悲”為內(nèi)容的交流和溝通提供可能。有鑒于此,人們既對自身“悲態(tài)”進(jìn)行積極主動的覺察和認(rèn)識,又借助對他者之悲態(tài)的體認(rèn)而生發(fā)切己的感觸,可謂全面有效“認(rèn)識悲態(tài)—認(rèn)識自我”的途徑與方法。誠然,“悲態(tài)”究其根本是符號動作的結(jié)果,這意味著人們對同一悲態(tài)的覺察和體認(rèn)不可避免的存在個體差異。這種經(jīng)由認(rèn)識他者之悲而明晰自我處境的方式、過程和效用也往往因人而異,需要人們加以靈活調(diào)控和把握。
(二)關(guān)懷自我:“悲態(tài)”的消解與珍視
“關(guān)懷自我”是貫穿中西方哲學(xué)的核心命題。先秦道家闡發(fā)自然人性的目的在于促成人們對原初本性的體認(rèn)與回歸。道家“復(fù)歸”的根本意義不是“返回”,而是對原初自我的回望、珍視與堅守。西方哲學(xué)家福柯通過賦予“自我技術(shù)”以“個體通過自身努力或憑借他人幫助,對他們自己的身體和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進(jìn)行某些操作,從而改變自身,以達(dá)到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狀態(tài)”②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Patrick H. Hutto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8:17-18.的定義,以及追溯古典犬儒主義者的生存樣態(tài),構(gòu)建出其哲學(xué)思想“自我關(guān)懷”的主旨。“左右一切行為的規(guī)則是,生命體總是會本能地保護(hù)或增強其生命力。一言以弊之,支配一切行為的生理原則乃是自我保護(hù)。”①[美]喬治·薩拜因著,[美]托馬斯·索爾森修訂:《政治學(xué)說史:民族國家(上)》第4 版,鄧正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29 頁。突破與消解“悲態(tài)”是人的原始需求,經(jīng)由消解“悲態(tài)”而關(guān)懷自我則是人們實現(xiàn)理想生存的重要途徑。
消解“悲態(tài)”既源自“關(guān)懷自我”的需求和動力,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與方法。基于“自我關(guān)懷”的動機與目的,人們可以通過各種可能的手段,實現(xiàn)對悲感的重新敘述、忘卻、轉(zhuǎn)移、轉(zhuǎn)嫁,從而成功地把悲感化解②譚光輝:《論悲感的敘述學(xué)原理、作用和化解方式》,《蘭州學(xué)刊》2018 年第11 期。。比如,積極運用個人或群體的力量主動改變不良處境、轉(zhuǎn)化和利用周圍環(huán)境間接改善不良態(tài)勢、順應(yīng)和把握時機一舉打破束縛和限制、經(jīng)由體認(rèn)他人處境提前預(yù)防不良事件的發(fā)生、借鑒他人觀點解決自身困境、用開闊的心境和視野在逆境中尋求自我發(fā)展等,皆是現(xiàn)實中人消解“悲態(tài)”的重要方式。由“悲態(tài)”的不可逃遁性而言,消解“悲態(tài)”是人生的永恒課程,具備應(yīng)對和消解“悲態(tài)”的能力既是人之主體性確認(rèn)與彰顯的重要標(biāo)志,也是人達(dá)至精神高境的必然要求。
“悲態(tài)”之于個體人生的消極影響是消解“悲態(tài)”的本原依據(jù)。然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2 章),缺乏或沒有“悲態(tài)”的人生定然充滿缺憾和危機。“對人的力量持樂觀信念,常常容易滋生對外部世界(包括社會領(lǐng)域)過強的支配、主宰等意向,并導(dǎo)致各種形式的理性僭越。”③楊國榮:《莊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 年,第40 頁。人生浩瀚縱橫的欲望需要借助“悲態(tài)”予其以收煞和消止。個體人生需要“悲態(tài)”這盆“冷水”作為鎮(zhèn)靜劑,從容的人生從來不會只有積極樂觀一種旋律。面對不可避免的悲態(tài),人們既要及時消解“悲態(tài)”的負(fù)面影響,又要合理看待并珍視蘊藏在“悲態(tài)”中的積極意義,從而通過恰當(dāng)?shù)剞D(zhuǎn)化與利用“悲態(tài)”而達(dá)成積極樂觀之結(jié)果。這種“消解—珍視”“既消解又珍視”的“悲態(tài)”觀,既是莊子“悲態(tài)”哲學(xué)欲意傳達(dá)的核心觀念,也是現(xiàn)實中人關(guān)懷自我必須依憑的手段與方式。
(三)實現(xiàn)自我:“悲態(tài)”的轉(zhuǎn)化與利用
以“蘇格拉底主義者”著稱的安提斯泰尼,經(jīng)常借用醫(yī)學(xué)隱喻指出社會價值與理想的病態(tài)特點。在安提斯泰尼看來,那些對財富、飲食、性過于貪婪,生性妒忌且又無知的人其實是患了嚴(yán)重的疾病,需要用理性來拯治。道家莊子也善用“疾病”的隱喻,其常借用身體畸形卻道境高尚之人,表明“悲態(tài)—道德”之間的轉(zhuǎn)化關(guān)系。朱光潛先生談及藝術(shù)形式之“悲”道:“這種悲色彩對讀者情緒的凈化作用正在于將世俗意義上的憐憫和恐懼轉(zhuǎn)變成為合于美德的思想情感。”④朱光潛:《悲劇與心理學(xué)》,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 年,第154 頁。“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老子》第51 章)。“道德”是中國古典哲學(xué)尤其道家哲學(xué)的核心概念,“悲態(tài)”哲學(xué)轉(zhuǎn)化與利用的最終指向是“道德”。
作為表達(dá)和呈現(xiàn)“悲態(tài)”的藝術(shù)形式,“悲劇是最上的藝術(shù),就因為它能教人‘退讓’,能把人生最黑暗的方面投射到焦點上,使人看到一切都是空虛而廢然思返”⑤朱光潛:《文藝心理學(xué)》,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9 年,第238 頁。。悲劇藝術(shù)所傳達(dá)的“退讓”精神實質(zhì)和道德觀念,與老莊“柔性”“不爭”的道德主張互為貫通,是理解“悲態(tài)”向“道德”轉(zhuǎn)化的重要介質(zhì)。“老莊思想是一種具有社會批判意識的弱者的哲學(xué),是試圖用最消極的方式積極把握人生的生命哲學(xué)。”①郭忠義:《道家文化內(nèi)核——復(fù)興的原因淺談》,《求是學(xué)刊》1992 年第2 期。道家之“德”的內(nèi)在特性是“柔”而非“剛”,以“柔”的方式面對困境并非退讓與躲避,而是以“無聲”的方式達(dá)至轉(zhuǎn)化和利用“悲態(tài)”的“勝有聲”的理想效果。“每一個在道德上有價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擔(dān),沒有承擔(dān),不負(fù)任何責(zé)任的東西,不是人而是物件。”②[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175 頁。道德之境從來不會自發(fā)形成,而只能是道德淬煉的結(jié)果,尤其是主體在“悲態(tài)”中以道德安置與回應(yīng)自我、他人和宇宙萬物的結(jié)果。由對“悲態(tài)”的沉思中獲得倫理啟示和道德指引,而非沉溺于“悲態(tài)”中不能自拔,是人之為人的本質(zhì)規(guī)定。
阿德勒(Adler)認(rèn)為,悲感的被動性中隱含著主動性,“這種情感充分展現(xiàn)了以退為進(jìn)、反弱為強的奮斗過程,展現(xiàn)了個體想要維護(hù)自己的地位、想要規(guī)避無力感和自卑感的意圖”③[奧]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理解人性》,汪洪瀾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 年,第229 頁。。面對消極否定的悲態(tài),來源于生命的“強力意志”往往“逼迫”人們由對“悲態(tài)”的感受與體驗中生發(fā)出無限的生命期待并將其訴諸于真實行動。這種主動弱化、克服、超越“悲態(tài)”而走向理想生存境遇的觀念和行為時刻離不開理性的指引與規(guī)約。轉(zhuǎn)化與利用“悲態(tài)”必須建基于對“悲態(tài)”的理性關(guān)照。理性的價值不僅在于發(fā)現(xiàn)和確證悲態(tài),也在于轉(zhuǎn)變和改善悲態(tài)。以理性調(diào)控和運載悲態(tài),而非停留在對“悲態(tài)”的感性認(rèn)識中,能夠促成“悲態(tài)”積極效用的最大化。“知道者必達(dá)于理,達(dá)于理者,必明于權(quán),明于權(quán)者,不以物害己。”(《莊子·秋水》)只有經(jīng)由“理性的沉淀或融化”的“悲態(tài)”才能夠具有普遍適用的意義與價值。經(jīng)由訴諸理性而體認(rèn)、轉(zhuǎn)化和利用“悲態(tài)”,方能真正成就與樂享理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