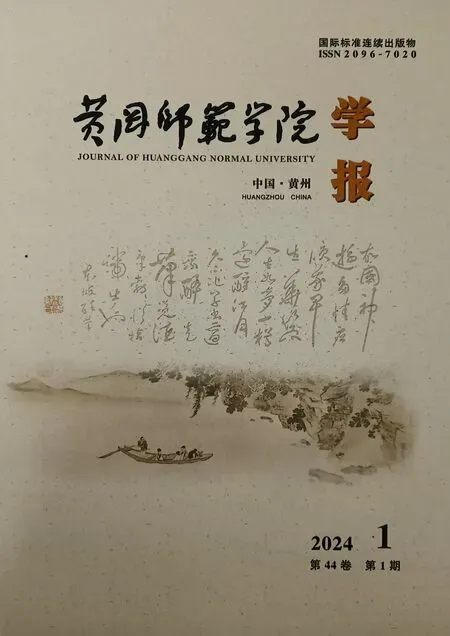國際視域下以“自然”為中心的跨學科文本細讀
——評楊治宜教授《“自然”之辯:蘇軾的有限與不朽》
陳 娟
(黃岡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岡 438000)
近日拜讀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楊治宜教授大作《“自然”之辯:蘇軾的有限與不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10,337頁,ISBN 978-7-108-06301-4,45元),宛如跟隨楊教授開啟一場縱橫四海的學術之旅,從瑞士巴塞爾到中國羅浮山,從中文英文到希臘文拉丁文,從藝術美學到社會倫理學,徜徉其中,跳躍騰挪,興致盎然,欲罷不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教授為本書所作序言和封底北京大學張鳴教授精辟的書評,高屋建瓴,言簡意賅,惜有未詳之憾。筆者不揣愚陋,擬從開闊的國際視野、跨學科比較思維、原創性文本細讀、立足當下的研究視角等四個方面推介此書。
一、開闊的國際視野
此書開闊的國際視野由楊治宜教授的學術背景決定,楊教授接受北大中文系實驗班本科和比較文學碩士的訓練后,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攻讀中國古典文學博士學位,期間為求在宋代思想史和歐洲哲學方向上精進,前往德國深造。2012年博士畢業后執教于德國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2015年起任副教授(終身教職),現為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主任。楊教授治學之路穿行亞歐美三大州,涉獵三大陸思想文化,英文達到準母語程度,此外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日文,書末參考文獻充分說明這一點。此書參考文獻分為古籍書目142條、中文學術文獻95條(其中港臺文獻21條)、日文學術文獻18條、英文參考文獻192條,總計447條,其中,大陸文獻和216條,港臺和海外文獻231條,前者占比近一半,后者占比過一半。可見此書視域放眼國際學術,具有和國內其他學術著作明顯不同的特質。
中文學術文獻不限于大陸,眾多港臺學者最新研究成果陳列其中,如臺灣葉嘉瑩《蘇軾》、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禪與詩》、李一冰《蘇東坡新傳》、劉維崇《蘇軾評傳》、劉石《蘇軾詞研究》、吳汝均《游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謝敏玲《蘇軾史論散文研究》、徐月芳《蘇軾奏議書牘研究》、朱傳譽編《蘇軾傳記資料》、香港林天蔚和黃約瑟編《唐宋史研究》,還有臺灣出版刊行的大陸學者或海外漢學家出版的學術成果,如王利器《葛洪論》、王水照《蘇軾論稿》,柯馬丁、李紀祥編《史記學與世界漢學續編》等。
日文學術文獻18條涵蓋日本蘇軾研究專家論著和論文,如竺沙雅章《蘇東坡》、久松真一《禪與藝術》,也包括日本學者編纂的文集,如吉川幸次郎編《中國文學論集》、古田紹欽等編《禪與藝術》、日本佛教學會編《佛教與自然》,還有專論一事或一題的論文,如竺沙雅章研究蘇軾與佛教、西野貞治研究蘇東坡詩歌源流、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的交友、蘇軾與元祐黨爭中的人物、內山精也對東坡烏臺詩案的考查等。
英文參考文獻192條,為數最多。其中一些經典的文藝理論研究著作,有的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如美國文藝理論家、批評家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鏡與燈》(北京大學出版社)、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美學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學附注》(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什么是藝術》有部分節譯),美國哲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奎邁·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的《榮譽法則:道德革命是如何發生的》,還有更多紅遍英語世界暫無中文譯本的論著和作品,如德國著名猶太學者、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散文集Illuminations和Reflections等。就參閱期刊雜志品種和數量而言,也略窺作者涉獵之寬,搜羅之廣,一共有來自西方最權威漢學雜志《通報》(T’oungPao)、《美國東方社會雜志》(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亞洲研究雜志》(JournalofAsianStudies)、《宋元遼金》(JournalofSong-YuanStudies)《道家文獻》(TaoistResources)、《中國文學:論文、文章、評論》(ChineseLiterature:Easy,Articles,Reviews)、綜合期刊《宗教史》(HistoryofReligion)、《亞洲學院院刊》(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Studies)、《亞洲專刊》(AsiaMajor)、《美國比較文學協會會刊》(ComparativeLiterature)、《比較文學研究》(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批評探索》(CriticalInquiry)、哲學學科期刊《東西方哲學》(PhilosophyEastandWest)、藝術學科期刊《東方學》(ArsOrientalis)、《亞洲藝術檔案》(ArchivesofAsianArt)等十六種刊物的數十篇論文。關于這些文獻所涉及的領域,將在正文第二部分進行梳理。英文參考文獻搜羅細致詳盡,幾乎囊括西方漢學界成書之前所有關于蘇軾生平、創作、理論的研究成果。192條英文參考文獻中包含26種譯著、22種編著、6篇博士論文,其中包含香港、臺北出版的英文論著各一種,還包括7條德文文獻、一條法文文獻、一條日文文獻,正如柯馬丁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本書是博學的典范,廣泛運用了古典中國傳統的各種資料,并利用了當代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學術著作。”[1]3
成書過程是另一個國際視野的證明。此書最早的形態是2012年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答辯的博士論文,后有2015年荷蘭萊頓大學博睿(Brill)出版社付梓的英文版,書名為DialecticsofSpontaneity:TheAestheticsandEthicsofSuShi(1037-1101)inPoetry,在此基礎上才有三聯書店出版的中文版。中文版由楊教授本人翻譯和改寫,和英文版之間的內容有些許差異。“除了具體行文顧及中文的學術常例和表達習慣有所增刪潤色之外,還添加了我這兩年來對此問題的一些最新思索。但最主要的變化還是增加了第三章‘名花的挑戰’。這章原本是我博士論文的一部分,但是沒有放進英文版專著,主要是因為比較側重考據,不太適合英文閱讀的緣 故。……出于敝帚自珍的意思,也為了這部分文章能繼續與中文讀者見 面,把它加以修訂、重新收入本書。在結構上,與第四章之間花、石相映,或許也更加成趣。”[1]2英文版出版后西方學界先后有兩篇書評,先是有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美國宋詩研究專家傅君勵(Michael A. Fuller)于2015年發表在《宋元研究期刊》第45卷長達13頁的書評,后有2018年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楚辭》研究專家魏寧(Nicholas Morrow Williams)于2018年發表在《中國文學研究前沿》第12卷篇幅5頁的書評。近日有一篇針對中文版的書評,主要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視角“探討作者如何圍繞此(自然)主題建構全書的邏輯論點與闡釋框架”[2],筆者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發此書文本細讀的原創性和研究視角的當下性以及對蘇軾研究乃至學術研究的貢獻。
二、跨學科比較思維
柯馬丁教授在序言中說:“楊治宜對美學創造、對自然世界的化用以及對藝術之意義的探討為中國學做出了深入而感人的貢獻,也為對藝術、文學和哲學的討論增加了跨學科、比較式的維度。”[1]3關于跨學科維度,可以從文末參考文獻涉及的領域和書中展開論證的行文來看。
此書除了涉獵國內外蘇軾研究權威專家有影響的學術成果,同時廣納與論題相關聯的思想、制度、文化、藝術等領域重要研究成果,筆鋒所及,關涉美學、美術學、倫理學、佛學、禪學、道教、哲學、語言學、文學(唐宋詩歌、江西詩派、詞)、文學理論、宋代制度、政治等各方面。下面以導論部分為例進行說明此書的跨學科特點。
導論分四個部分:《2016年2月20日,瑞士巴塞爾》《否定的自然》《藝術與自然》和《蘇軾:一個天才的神話》,通過探討藝術與自然的關系,揭示作為美學風格的“自然”一詞的否定性定義和辯證性特點,并進一步論及作為蘇軾作品風格的“自然”,從蘇軾接受史角度選取北宋、南宋、明代、清代四個不同時期代表性人物對蘇軾的評價所形成的矛盾性,從而進入正文討論的對象——以蘇軾作品以及關于蘇軾的批評話語為代表的美學和倫理觀。導論部分征引了20多位海外學者和中國古代6位士人(未包括論題人物蘇軾)的言論,本書跨學科特點從這些學者研究領域可略窺一斑。列舉的古代中國文人有黃庭堅、蔡絳、朱熹、袁宏道、趙翼、何薳,分布文學、書法、理學、文學理論、史學等各學科。海外學者有:法國藝術家杜步斐(Jean Dubuffet)、杜尚(Marcel Duchamp),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Slavoj Zizek),德國藝術史家貝爾廷(Hans Belting),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藝術批評家和藝術哲學家丹頓(Arthur Danto),新西蘭哲學家斯蒂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國詩人、文評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ee Sigmund Frued),德國哲學家、音樂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德國古典理性主義哲學創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德國著名詩人、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劇作家,德國啟蒙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席勒(Johann C. F. von Schiller),日本京都學派哲學家久松真,英國著名漢學家葛瑞漢(A. C. Graham),美國漢學家雷麥倫(Maureen Robertson),美國羅格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田菱(Wendy Swarts),加拿大漢學家林理璋(Richard John Lyn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佛教和東亞宗教中心主任、佛教研究專家傅瑞(Bernard Faure),美國沙拉勞倫斯學院教授、禪宗研究專家福克(T. Griffith Foulk)等,關涉文學、哲學、心理學、音樂、宗教等領域。
為了研討“藝術”和“自然”兩個概念和二者之間的關系,作者博采名家,論述中常見中西方比較思維的運用。首先是時代的類比。“如果用古希臘比擬漢魏藝術的簡淡、文藝復興比擬盛唐的絢爛的話,那么現代藝術就好比中國的宋元,是一個對藝術和技巧本身開始反思的時代。”[1]4其次是觀念的類比。在探討技法與自由的張力和“自然之藝”這一美學理念時,借用臺灣學者吳汝均提出的觀點,“西方席勒‘自由游戲’的審美境界與佛家的‘游戲三昧’不無契合。”[1]15類比中作者善于異中求同,并與本書主旨人物蘇軾的觀點進行比對,如“這些美學理論都各有其背景與預設,自不可一概而論。然而它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藝術至自然創造力的中間性(in-between-ness)。唯心主義哲學家以理念為真,而佛家以空為真,然而藝術(或三昧之境)暫時肯定了現象界的真理價值。蘇軾的佛學觀傾向于藝術的肯定面。”[1]17
書中論述蘇軾的藝術美學(第一、二章)和自然美學(三、四章)時,亦見精彩之中西比較。第一章《詩心如鏡》檢討蘇軾以人論藝的傾向和他詩心如鏡的譬喻。通過對《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的文本細讀,指出“水”的意象“象征著得道、入定的禪心,能夠如實、即時地涵容映攝萬象而不改其靜。”[1]55蘇軾建議求道之途不僅要研習佛經,也要鉆研各種藝術,就要把自己轉化為一面水鏡。“就東西哲學比較的角度,這樣的一面鏡子有別于柏拉圖模仿論所用的鏡喻。當柏拉圖把藝術比喻成反映了自然界形象的一面鏡子時,他并沒有賦予這面鏡子以任何認識論價值。與此不同的是,水鏡并不僅僅機械反映可見的形象,而且也揭示出‘群動’和‘萬境’,這是我們的感官通常不能直接知覺到的。這表明冥想中的詩人具備了更加敏銳、包容萬象的認知能力。”[1]56
第二章《制造“自然”》談論藝術的自然創造力和創作運思的過程與狀態。“蘇軾把自己的文章比喻成‘萬斛泉源’。泉源(或江河)是潛意識的、沉浸在遺忘之境的藝術的普遍象征。”無獨有偶,西方文化中也有此類觀點。“古典學者哈羅德·萬禮希[Harald Weinrich]提出,一條具有魔力的河流是藝術的重要象征。在希臘神話里,‘忘川’[Lethe]是冥界之河。……希臘文的‘真理’[aletheia],是以否定的前綴a-加上-leth-構成。因此,從希臘傳統,尤其是柏拉圖哲學開出的歐洲哲學從來都是從遺忘的反面,即記憶和回憶里尋找真理。”[1]94-95“飲酒可以幫助詩人墨客放松意識的自我控制,陷入忘境,讓他借意識的黃昏揮灑行文。這意味著飲酒也被用為藝術的自然創造力境界的‘方便法門’……在西方傳統里,遺忘的藝術[ars oblivionis]是甜蜜的黑暗,治愈真理灼人的光芒留下的創傷。……我們的例子也不無相通之處:通過遺忘,藝術家短暫地懸擱了自己對悟道的不懈追求”。[1]94-95
第三章《名花的挑戰》檢討蘇軾的自然美學,分為四部分:自然美學、花解語、佛寺牡丹考、“色”與道德、結語。其中“自然美學”部分專門介紹在西方美學傳統里,就自然物能否成為美學研究的對象是有爭論的。列舉黑格爾、康德、顧彬、本雅明、海德格爾、詩人策蘭、列奧塔、貢布里奇等西方學人的不同觀點,最后總結,“這樣說來,不僅‘藝術的自然創造力’是矛盾修辭,‘自然美學也是矛盾修辭,因為美學本質上就是闡釋。……這將幫助我們認識中國11世紀對自然物的鑒賞話語”。[1]123“花解語”部分重點解讀蘇軾詩句“我觀解語花,粉色如黃土。一眼破千偈,況爾初不語。”指出蘇軾把當時已成常語的“解語花”之喻更翻轉了一層,首句把花納入人類中心主義的意義系統,末句則打破幻相,重新肯定花的純粹物質存在,這種存在成為無言、永恒的真諦的象征。“蘇軾的譬喻讓我們想到了上文所引的自本杰明以來現代美學思想家對非人語言的思索。盡管二者之間有哲學傳統和理論體系化程度之別,但核心的出發點,都是渴望著擺脫人類中心主義語言觀,乃至思維模式的可能性。”[1]127作者的學養根基使得中西比較思維在書中隨處可見,且異中見同,中西互證,也凸顯了自然、美學和藝術的世界同一性,經由作者的闡釋,蘇軾的自然美學走向了世界。
三、原創性文本細讀
楊治宜教授此書立論多建立在對蘇軾作品的文本細讀之上,每章都有精細的作品解析,整篇的、節選的、有時也有只言片語的。第一章《詩心如鏡》中除了上文提到的作于1091年的《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還有作于1061年的《中庸論》、作于1095年流放惠州時期的《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1101年逝世前不久所作的《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行文中亦提及為好友駙馬王詵新修藏畫樓所撰的《寶繪堂記》《墨寶堂記》。第二章《制造自然》里選取書信《與二郎侄一首》、詩歌《石倉舒醉墨堂》(常引,重讀出新)、《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小篆般若心經贊》《雪堂記》《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第三章《名花的挑戰》中,詩歌《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贈東林總長老》《牡丹記敘》《中和勝相院記》《梅花二首》。第四章《雄辯的怪石》里《詠怪石》《書青州石末硯》《孔毅甫鳳咮石硯銘》《鳳咮硯銘并序》《龍尾硯歌并引》《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軾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及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天石硯銘》《和陶讀山海經其十三》。第五章《回歸內在的烏托邦》中《和陶歸園田居其一》《和陶歸園田居其二》《和陶下潠田舍獲》《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其二》《和陶擬古九首其九》《和陶止酒》《鳳翔八觀秦穆公墓》《和陶詠三良》《和陶桃花源并引》《和陶還舊居》《和陶東方有一士》《和陶歸去來兮辭》。第六章《逍遙的肉身》中《過大庾嶺》《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指出艾朗諾解讀之誤)《和陶讀山海經其二》《跋嵇叔夜養生論后》《龍虎鉛汞說》《白鶴新居上梁文》《天慶觀乳泉賦》《和陶雜詩十一首其二》《和陶形贈影》《答徑山琳長老》,行文中提及《后赤壁賦》《謫居三適》和《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其一》。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魏寧(Nicholas Morrow Williams)教授在書評中開門見山指出:“盡管基于之前的學術成果,楊的研究也是高度原創的,因為她介紹了許多被忽視的作品,同時以極大熱情和博學闡釋了它們的哲學悖論和文體微妙之處。”[3]這種原創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被忽視的作品進行文本細讀,以《雪堂記》《龍虎鉛汞說》為代表;另一個是對常引的作品進行全新的文本細讀,得出與以往不一致的結論,以《石蒼舒醉墨堂》和晚期放逐詩為代表。
“相較于人們對于雪堂之名的熱衷,《雪堂記》文本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后世少有評說。以至于曾棗莊《蘇文匯評》中未收此文,《蘇詩全集校注》該文后亦沒有集評。對文本語句的化用也較為少見。”[4]楊治宜教授在第二章《制造“自然”》中以長達12頁的篇幅逐段細讀了《雪堂記》,并以“雪堂與‘似境’為小標題”,闡釋蘇軾的“中道”觀。“‘中道’也就是‘空’的絕對真理與‘假’的色相世界之間的第三種存在境界。蘇軾貶謫黃州期間(1080-1084年)所撰的《雪堂記》,描述的恰是這一境界,這也是藝術創造的‘似境’,在空與假之間,外物的色相都通過藝術得以表現。”[1]97作者細讀的結論是“《雪堂記》同時向以否定方式表達的絕對之‘道’致敬(因為道不可知也不可道,所以任何對絕對之道的陳述都必然只能用否定的方式來表達),也為肯定性的審美之道辯護”,[1]110獨具慧眼挖掘出《雪堂記》對于剖析蘇軾哲學觀和美學觀的重要意義——“由文本建立起來的詩歌人格,不能完全與作者本人畫等號。作品與作者的自我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其功能不僅在于簡單的表達和抒發,而每每蘊含了作者的自我投射、自我幻想、自我塑造、自我說服。”[1]98
《龍虎鉛汞說》是給蘇轍的一封私人信件,對于蘇軾的道教信仰和丹學修行研究如此重要,和《雪堂記》一樣,成為第六章《逍遙的肉身》中一個部分的小標題。作者把文章分成四部分,逐一闡釋評點,對艱澀的道教丹學術語如龍、汞、虎、鉛、胎息、泥丸、懸癕等進行解釋,對蘇軾具體修行法門如飲食控制(吃干蒸餅,不飲湯水,略飲酒),采日月精華,呼吸控制和行龍虎訣等做出總結。楊教授迎難而上,旨在矯正之前中文學術界大多對蘇軾的道教信仰和追求長生的修習諱莫如深的傲慢與偏見,這種學術勇氣、決心和眼力也是作者導師柯馬丁教授在為本書所作序言中所嘉許的。
蘇軾作為文學和藝術大家,很多作品被關注,解讀不同,持論亦異。如關于藝與學的關系,蘇軾是頓悟派還是漸悟派,兩派看法迥異,因為蘇軾有些詩歌文章似乎確實倡導“不學”和“無法”,《石蒼舒醉墨堂》詩就是持“無法”論學者常引的論據。結合蘇軾與石倉舒的身份(草書家)與關系(朋友),經過對“姓名粗記”典故的揭示,和“我書意造本無法”的文本細讀(“意造”是按照主觀揣度妄為的意思),得出不同的結論:蘇軾并不主張摒棄學習和法度。又如蘇軾晚期放逐詩,當代學術多數贊頌它們展示了對大自然、對“人民”的熱愛。經過對蘇軾和陶詩的文本細讀,對比同一時期不同文類的作品,發現“私人書信里袒露的這種絕望感,卻幾乎從來不流露在蘇軾的詩歌里”,指出“蘇軾在散文書信里抱怨了身處的異境,而他的詩歌卻浪漫化了他的重新植根。它們之間的差別顯示蘇軾要融入當地居民的誓言多少有自我說服的成分”[1]207-210,從而質疑蘇軾向嶺海山川的回歸的徹底或者“自然”。
張鳴教授評也說此書“看點很多,以下三點最突出:第一,利用蘇軾思想觀念、審美意識和文學藝術中含義豐富復雜而又十分核心的‘自然’命題,將各個領域貫穿成一整體,構成宏大的闡釋體系,核心概念的抽繹和闡釋框架的設立都富于理論建構意義。第二,通過歷史文本的細讀,嘗試還原蘇軾思想、文學、藝術以及審美觀念得以生成的語境,實現同情之理解與理解之同情,在與蘇軾對話的場域中,表達作者對蘇軾的獨到思考和認知。第三,在細讀歷史文本過程中體現出綿密的思維追求和方法論自覺。做到獨出心裁、深入詮釋、充分揭示文本承載的信息而又盡量避免背離文本的意義走向,避免將復雜問題簡單化。”[1]文本細讀是此書中西方學者被共同吸引之亮點。
四、立足當下的研究視角
傅君勵(Michael A. Fuller)教授的書評中著重強調了此書立足當下的研究視角:“楊治宜將《自然之辯》描述為‘對蘇軾的現代重新體驗做出的持續不斷的評釋努力’。楊教授探討的中英文學術中討論過的關于蘇軾的論題,旨在使解讀深入復雜,并重新構建蘇軾作品在當代的意義。……從一開始,楊就塑造了她的批評術語,使其關注的不是蘇軾的關注,而是后來文化和當今的關注。”[5]
雖然本書研究對象是蘇軾的美學和倫理觀,但導言部分交代研究的緣起,卻是一個現代學者由參觀瑞士巴塞爾貝葉樂(Beyeler)美術館陳列的法國藝術家杜步斐(Jean Dubuffet,1901-1985)雕塑展品引發的對于“藝術”定義和自然與技巧的辯證關系的思考。書中兩個核心概念“藝術”和“自然”,也是結合當代的理論研究成果而界定的。德國貝爾廷(Hans Belting)認為歐洲的“藝術”時代起自1400年左右,美國丹頓(Arthur Danto)進一步提出“藝術”的時代終結于20世紀80年代,“蘇軾生活在中國參照歐洲模式進入‘藝術的時代’之前,但他的時代依然存在‘藝術實踐’……本書用‘藝術’一詞指具有審美形式、由創造性活動產生、并在我們當代被一致認定為‘藝術’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了代表語言藝術之最高典范的詩歌。作為詩人、書法家、畫家的蘇軾,當然也不妨被稱為‘藝術家 ’。”[1]9另一個核心概念“自然”是英文普通用法的詞匯,但是經過作者用中國哲學里的一種核心理念加以闡釋,從而上升為一種理論范疇。中文版主要采用老莊哲學中內涵豐富的“自然”一詞來指稱這個概念。
蘇軾的時代和作品雖然離我們遙遠,但藝術是永恒的論題,作者在研究展開過程中,也緊密結合當今理論成果。如“技法與自由的張力至今都是重要的美學課題……當代藝術嘗嘗試驗各種表達的自由……從歷史的角度看,‘自然之藝’這一美學理念代表了藝術反對慣例、當權者或體制化傾向的革命精神。”[1]14在談及藝術家和藝術品互為因果時,作者列舉了2016年5月24日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發生的游客誤把素人眼鏡當做藝術品的趣事,從而進一步強調明確“自然”定義應為受過高度模式化訓練之后、打破常規“回歸”的自然,而不是未經任何訓練的原始的自然。[1]21-22論及蘇軾對藝術手段的物質性保持警惕時,引入“現代資本主義理論認為人所占有的物質是自我的延伸……而蘇軾所繼承的哲學傳統則認為心神平靜、集中的主觀自我才是個人力量的唯一來源。”[1]69在論及藝與學的關系時,作者用現代神經科學來解釋[1]85。蘇軾經常寫詩記錄作為禮物的石頭,作者援引當代著述《禮物》里的言論,禮品贈送的基本原則是互惠,其目的在于達到社會團結,用以闡釋蘇軾與友人的饋贈唱酬[1]172-174。正如楊治宜教授在書《跋》中所說:“作為學者的我在闡釋學上有意拉開距離,……蘇軾的這面鏡子里,映出的是我作為現代、跨文化讀者的面孔。”[1]303
本書的創作宗旨,是為了揭示蘇軾其人其文在當下的意義。第五章《回歸內在的烏托邦》探討蘇軾109首和陶詩,作者一方面注意到西方學界關注蘇軾在陶潛經典化過程中的作用,一方面從另一個角度論證蘇軾和陶之于蘇軾的意義。先經過文本細讀得出“通過風格上的‘回歸’陶潛,蘇軾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狀態的回歸”的結論,緊接著從現代文學批評的角度分析蘇軾自稱陶潛“后身”的問題,指出“把文學人格等同于詩人的真實人格,這在現代文學批評看來是相當靠不住的理論范式”,“哪怕蘇軾作為陶潛的‘后身’可以合法‘繼承’陶潛的風格,精確復制本身就將消解兩位詩人各自的獨特性。”指出“所有矛盾都指向了蘇軾效陶深層的自我說服因素。……他有意維持的樂觀主義凈化去了陶詩中偶然流露的焦慮或懷疑。”最后揭示蘇軾和陶對于蘇軾的意義:“蘇軾把陶潛的形象提升成了崇拜和神話,而通過戴上他所建構的這個陶潛的面具,他對自己的命運行使了一種想象的權力,并在迫害、困窘與絕望等苦難之上尋找自由。”[1]248-250亦即“通過陶潛,抵達自身”(第五章結語標題),作者也通過這些對話,抵達自身,“我在此書中要提出的,恰是如何以他為榜樣,在人的有限性之內實現這樣蓬勃勇猛的自由感。”[1]3
此書除了開闊的國際視野、跨學科多元思維、原創性文本細讀、立足當下的研究視角這幾個突出的特色之外,吸引人的還有精辟的見解、跳脫的行文和縝密的結構。全書六章,前兩章談“自然”美學風格的創作主體,即創作者或藝術家之必要條件和創作過程,中間兩章談蘇軾“自然”美學的外部世界表現,后兩章談“自然”美學的內在心理機制,緊密圍繞“‘自然’之辯”論題,上一章結尾必有牽出下一章的文字,結構縝密,文心細膩。行文游走于古今中外,輕盈跳脫,引人入勝。
最后以楊教授導師柯馬丁教授的話語作為本文結束:“它代表了我們未來最好的希望,即不再拘于某一特定學術圈或意識形態之需要的學術。……它的成就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它把許多深刻的人文問題帶入對蘇軾的研究之中,也把蘇軾的生平和作品帶入全球學者共享的哲學、文學和美學話語語境,而不僅限于漢學學術圈的語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