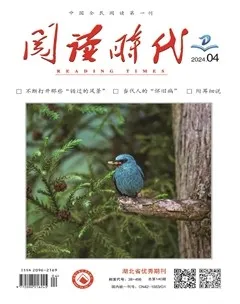羅伯特·瓦爾澤:渺小,保持渺小
王雨寬
世人對羅伯特·瓦爾澤的好奇源自一張拍攝于1956年的照片。照片中,一名老者張開四肢,躺在瑞士東部的一片皚皚白雪之中,散落的帽子、周圍深深淺淺的腳印引發了人們無限的浪漫聯想。這原本是記錄死訊的一張相片,卻令這位生前默默無聞的作家在隨后的歲月中吸引了眾多關注。曾經將他忽視、對他不屑一顧的讀者們熱切地研究、閱讀著關于他的一切,探尋這位謎語般的瑞士作家:他是誰?他從何處出發,又如何走進了森林與雪地?
“來自內心的詩”
1878年春天,瓦爾澤出生在瑞士小城比爾的一戶多子家庭。幼年時的瓦爾澤生活優渥,衣食無憂,和兄弟姐妹們在“巖石、洞穴、河岸、草場、低地、峽谷和森林瀑布”中“到處玩耍、發明游戲”(《坦納兄妹》)。
然而,在瓦爾澤逐漸長大的那些年歲里,父親的生意卻走上了下坡路,家族財富不斷縮減,社會地位持續下滑,這令生性敏感好強的母親患上了憂郁癥。雪上加霜的是,最年長的哥哥在瓦爾澤四歲那年病逝,給這個本就不幸的家族帶來了更深重的打擊。
瓦爾澤14歲那年,被家人送去銀行當學徒。在漫長而枯燥的學徒生涯期間,瓦爾澤遇到了可以為之燃燒一切的熱愛——他觀看了席勒創作的戲劇《強盜》,并一發不可收地愛上了戲劇,夢想成為一名演員。為此,他逃往德國南部大城市斯圖加特,并報名參加了一個表演訓練班,但這個愿望很快便落空了——生性靦腆的瓦爾澤并不具備演員這一職業所必需的“神圣的火花”(《散步:羅伯特·瓦爾澤中短篇小說集》)。之后他回到瑞士蘇黎世,再次成為了一名助理會計師。
1897至1902年是極為動蕩的幾年,青年瓦爾澤輾轉于慕尼黑、柏林、圖恩與維爾茨堡,寄住在不同的親戚與朋友家中。就是在這種動蕩不安中,瓦爾澤開始以詩人的身份嶄露頭角。出版人弗蘭茨·布萊對他的詩作評價很高:“這些都是真實且真正來自內心的詩歌。韻律從不主導意義。沒有一首詩為了迎合耳朵而調整其旋律。詩歌不為音樂犧牲,語言不為節奏犧牲,詞句不為旋律犧牲。”寥寥數語點出了瓦爾澤在文學創作中不拘泥傳統形式、突出真誠、注重意義的特質。
成為一名“仆人”
1905年,27歲的瓦爾澤來到柏林,此時,他的第一本書——中短篇小說集《弗里茨·科赫的作文簿》已經出版,并獲得了評論界的一些褒獎。這鼓舞了他。他來到柏林投靠自己年長一歲的哥哥卡爾·瓦爾澤——一名事業有成、通曉人情世故的書籍插圖師及舞臺美術師。卡爾將他引薦給柏林的各色出版商、藝術家和文學家。但是,瓦爾澤并不適應這種光鮮亮麗的生活,這位生性靦腆的年輕作家始終無法真正走進那個由文學明星、戲劇明星和文化商人所組成的文藝圈,他在那個圈子外圍打轉,最終什么也沒有得到。
盡管瓦爾澤承認城市對藝術的促進作用,但在這個文明的中心,出生于瑞士小城的瓦爾澤痛苦地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在后期的短篇小說《猴子》中,瓦爾澤塑造了一只忽然闖進人類咖啡館蹲坐時光的猴子,這只猴子在衣著方面費盡心思,戴著一頂可笑的高帽,操著一口方言,猶豫著是否要在咖啡館的中心落座——這是一只未被文明徹底馴化的“牲畜”,精準地再現了內向者在人群中感到的壓迫與不適。

之后,瓦爾澤轉身背離了那個五光十色的世界,做了一個不被周圍人理解的決定——進入一所仆人學校,并試圖像他的母親一樣去做一名合格的仆人,做一名無產者:“我不愿身為占有者卻只占有一半,我寧愿自己屬于徹底的無產者,那么,我的靈魂至少還屬于我。”(《坦納兄妹》)在十年后寫作的《托波德》中,瓦爾澤將自己這種“成為一名仆人”的決心描述為一種生活實驗,一種“冒險”,并將其與堂吉訶德的瘋癲之舉作對比,并大膽宣稱:“那種既沒有獨特之處,也沒有所謂瘋癲之舉的生命,算得上是生命嗎?”(《散步:羅伯特·瓦爾澤中短篇小說集》)
“自然”是靈感來源
瓦爾澤在柏林沉浮7年,后期愈發深居簡出。1913年,他回到故鄉比爾,在一間名為“藍十字”的旅館住下,在孤獨和貧困中繼續他的創作。
為了維系自己與外界脆弱的聯系,瓦爾澤一次又一次走出房門,進行漫長的散步,瓦爾澤的代表作《散步》便誕生在這一時期。或許用“散步”來形容他的出走也并非如此恰當,準確來說,那是一種漫長的、苦行僧式的徒步,時常長達半日乃至于幾日,瓦爾澤會翻山越嶺,甚至步行至另一個城市。《散步》所描寫的就是這樣一種試圖用行走與世界接觸的體驗,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一名窮困潦倒、孤苦伶仃的作家對這個龐大世界的種種看法與回應。
在這段日子里,瓦爾澤的創作主題開始由城市生活、藝術生活轉向大自然與田園風光(這本是他擅長的領域)。家鄉秀美的山水滋養了他的文字,他以最細膩的筆觸描畫雙眼所見之物,寫出了一篇又一篇意蘊悠長的散文與短篇故事。他對自然的研究充溢著各種飄浮的想象,同時也包含著謀求自由的政治訴求。在他的筆下,萬事萬物都有靈魂與生機,因為當他“沉默地、長久地、仔細地注視著大地之時……一切美麗的外界事物都會反過來回望我”(《散步:羅伯特·瓦爾澤中短篇小說集》)。
徹底的“逃逸”
在比爾度過了困頓的7年后,瓦爾澤為了尋找新的靈感,遷居伯爾尼,并謀到了一份在伯爾尼國家檔案館中的工作,但這份雇傭工作卻因與上級的矛盾草草收場。自此,瓦爾澤徹底告別了從青少年時期就與他牽扯不斷的辦公室。
在伯爾尼,瓦爾澤出版了他在世期間的最后一本文集《玫瑰》。這本文集被瓦爾澤稱為“我最優雅的作品之一,只有年長的高貴女性才能將它捧在手心,因為它需要得到許多的理解與諒解”。而它在商業上并不成功,這也宣告了瓦爾澤作為職業作家生涯的落幕。自此之后,瓦爾澤的寫作徹底脫離了出版與發表,他開始了一種純粹為了寫作樂趣而進行的秘密寫作:從1924年起,瓦爾澤開始用鉛筆寫作,字跡也大大縮小,僅有2毫米高。就是以這種方式,他在24張八開藝術印刷紙上寫下了現存于世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強盜》。這部小說如今僅以草稿的形式存在,瓦爾澤從未對其進行謄抄,或許他從未想過要出版它。
《強盜》再次動用了少年時期瓦爾澤的熱愛——那部由席勒創作、點燃了他文藝夢的同名戲劇《強盜》。與席勒塑造的那名追求真理與自由、曾成功發動了革命的強盜不同,瓦爾澤的強盜仍舊是一個未能成功“適應市民秩序”的“無用之人”。這名強盜從未有過任何犯罪行為,卻以自己的存在挑釁著大部分已然順從了社會秩序的主流大眾。
1929年,瓦爾澤入住伯爾尼瓦爾道療養院,開啟了他長達27年的療養院生活。在隨后與世隔絕的療養院歲月中,瓦爾澤扮演著一位恭敬順從的病患角色。與此同時,他似乎也徹底放棄了寫作,不再發表任何文章,并在唯一陪自己散步的好友卡爾·澤利希面前反復申明了這一點。
然而,在他去世后,澤利希卻收到了五百二十六張密密麻麻的手稿,那是瓦爾澤在車票、日歷、煙卷盒上不斷寫下的文字,字體甚至比前文提到的《強盜》更小,運用了各種難以破解的縮寫,這成為日后所有瓦爾澤研究者的難題。澤利希這才意識到,原來瓦爾澤從未放棄寫作。這種秘密的寫作生活一直持續至1956年的圣誕節。那一天,78歲的瓦爾澤像往常一樣走出療養院去森林中散步,卻倒在了皚皚的白雪地之中,再也沒有起來。
縱觀瓦爾澤的一生,我們注意到,瓦爾澤的“失敗”勾勒出的是一條清晰的逃亡路線:在瓦爾澤的前半生,他試圖逃脫辦公室的管控,為此,他曾求助于戲劇與文學;而在他的后半生,他又試圖從充斥著浮華與偉大的文藝圈逃脫,遁入唯一的、父母般的大自然。
逃亡的背后是瓦爾澤對一切權威與控制的拒絕。在大多數忙于生計的庸碌大眾眼中,這種代價顯然太高昂了。但瓦爾澤卻做到了,他用渺小與貧苦守住了內心的自由,將其獻給寫作與思索。這是他的寶貴之處。天性的善良與柔弱令他無法像他崇拜的戲劇作品《強盜》中的主人公卡爾一般,以行動向社會公開宣戰。然而,每一位心有所感的讀者都能在那些狀似謙卑與臣服的低語中讀到一陣又一陣關乎自由的風暴,它們是如此強大,如此令人熱淚盈眶。
(源自“新京報”,有刪節)
責編: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