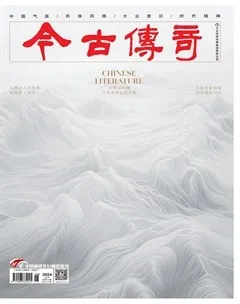梓園光影
吳昕孺

一
中巴從谷底加速沖上八景鄉蘭家洞水庫大壩即戛然而止。連綿群山間,一片長天浩水映入眼簾,我仿佛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剛才的溽熱與疲累一掃而空。藍天、碧山、綠水,它們不是排著隊,而是一幅和諧、完整的畫面,它們不是呈現,而是將我納入其中——我不是闖入,似是歸來。
我視野里的水域盡頭有一個半島,半島頂端高木林立,密集而壯碩的枝丫故意留出一個漏洞,從那里長出一瓣樸素的檐角,與湖光山色相映成趣。那是梓園。韓少功老師在郵件中,對我有過詳細的描摹與交代。八景,號稱岳陽的西藏,當時是湘北唯一不通柏油公路的鄉鎮。老師告訴我,水庫邊上的那條簡易公路也在修,無法通車,我只能坐船過去。
大壩下面的確有艘木船,船頭的柴油發動機像只蹲著的猴子。我到了壩下,高喊一聲,有人嗎?一個寡瘦的黑臉農民就從我的聲音里飄過來。他看了看我,笑著問,去韓爹那吧?我一時沒聽懂,就說,我要去梓園!他低聲咕噥道,不就是韓爹家。
“韓爹!”我被這個稱呼逗樂了。晚上,我問老師對這個稱呼的看法,他也哈哈一笑:“我不是來鄉里住住的,我就是一個鄉里人。我在這里不僅鋤地、種菜,還參加村民大會,在這里參政議政、調解鄰里糾紛、捐款修路等等。鄉親們把我當作他們中的一員,如果他們都喊韓老師,就說明我還披了一層文人的皮,改造得不徹底。”我說:那您不成農民作家啦?韓老師突然嚴肅地說,“作家”前面是不應有前綴的,“作家”是唯一的,也是一切身份的總和。
船開了。仿佛是一排波浪推著船走,而不是船在水面劃開波浪。漣漪像音符一般,響得很遠很遠。整個水庫,包括群山,都微微地蕩漾著。我在那瓣檐角下上岸,但還得穿過大片菜地,爬上一個陡坡,走進八景學校的校門。從學校再往水邊上走,便看見一叢樹林的前面,矗立著一張大門。韓老師瞇著眼睛,笑吟吟地站在門口。
晚飯,師母炒了黃瓜、萵筍、臘肉、雞蛋等,蔬菜是自己地里種的,蛋是自家雞生的,臘肉是鄉親們送的。我小口小口地吃著噴香的飯菜,不是出于拘謹,而是感受到我所吃的食物里所蘊含的一種獨特的勞動,那似乎是文學化了的人間煙火氣息。
晚上在前坪乘涼,八景學校的蘭老師來了,還有住在對面的一個老農。韓老師向他們介紹我,笑稱是“省里來的”。我有好多年沒坐過鄉下的木制火椅了,而梓園只有這種椅子,所以一坐就坐到了濃烈的鄉情里。我們用土話聊天,聊教育,聊農事,聊收成,聊張家長李家短……月亮真好,“像別在鄉村的一枚徽章”。“我伸出雙手,看見每一道靜脈里月光的流動”。那是八景的月夜,是韓老師的《月夜》,我作為觀者和讀者得到雙重的浸潤。
二
第一次去八景后不久,我競聘上了《大學時代》雜志社執行主編一職。我的初衷是辦一本《大學》雜志,以思想性、文化性、精英性為旨歸,不求發行量,追求影響力。但雜志報批時,新聞出版部門改名為《大學時代》,要求辦一本反映大學校園生活的刊物。我拿到這個刊名有些氣餒,卻不甘心,我寫信給韓老師,請求支持。韓老師二話不說,幫我聯系了張承志、史鐵生、南帆等知名作家……雜志出來后,贏得一片叫好,卻不叫座。大學生寧愿花錢上網聊天、下館子請客,也不愿意買刊。2003年春末,我發郵件給老師,申請前往八景當面請教。
梓園,就像大自然的一塊特區,悠然矗立于半島之上。外面的陽光有違春天的本分,急于揮戈舞劍去攻占夏天的地盤,但只要走進梓園,濃密的綠蔭讓你頓時收汗、消喘,氣息平穩,心情舒爽。還有蟲鳥的合唱、邁著標準臺步的母雞、一天到晚在做著神秘偵探工作的貓……太陽透過樹群枝葉的空隙,在小徑和前坪灑下無數光斑,風一吹,光斑的位置和形狀隨時發生變化,酷似夜晚打在舞臺上的射燈。我跟韓老師說,您這里娛樂元素和大城市一樣啊!韓老師用手畫了一個圈,說,它們才是梓園的主人,我們回來做客,所以盡量不要驚擾它們。
韓老師把我拉回到20世紀風云際會的80年代,他在海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辦《海南紀實》雜志。他說,辦刊和寫作大不一樣。寫作是私人行為,表達自己;辦刊是公共事業,得讓別人喜歡。當時,我們去考察市場,看到地攤上大多是拳頭加枕頭的東西,花花綠綠,粗制濫造,那我們怎么辦?我想出了四個字:守正出奇。《海南紀實》也注重思想和品位,但雜志首先是要傳播,沒有市場份額,辦起來就沒什么意思,所以我們決定辦一本紀實性的新聞刊,邀請大作家、名作家來寫紀實文學,剖析要聞熱點,配上著名攝影家拍的照片,立馬打開了局面。這本雜志發行一百多萬份,三個印刷廠同時開印,把我們自己都嚇了一跳……
韓老師一席話說得我云開霧散。臨走,他送給我一套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8卷本文集,小開本,淺紅色,很別致,其中就有敘述《海南紀實》辦刊經歷與經驗的長文。我馬上對《大學時代》進行調整,將辦刊宗旨修改為“弘揚校園文化,追蹤熱點時尚,點擊大學生活,反映時代氣息”,一邊力邀一批名家為我們寫稿或做專訪,一邊吸收在校大學生進編輯部,和我們共同辦刊。《大學時代》發行量躥升,被譽為“中國經營大學生活第一刊”。然而,糾纏于人事,困頓于商海,惶惑于應酬,我疲累至極,苦惱不堪。
2004年是《大學時代》扭虧為盈、情況最好的一年,我在10月15日給韓老師的信中這樣寫道:“雜志基本上挺過來了,但我付出的代價也很大,要做許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說大量自己不喜歡說的話,經常有斯文掃地、無地自容之感。最大的收獲就是對社會生活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我也跟韓老師交流過一些對他作品的看法。《暗示》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但我對出版社將它列為“長篇小說”頗為不解,如果要作為小說的話,那附錄三“主要外國人譯名對照表”便顯得多余。韓老師的意思是,倘若你覺得這是一部好書,干嗎要糾纏于它究竟是一部長篇小說還是一部學術專著呢?這個回答很智慧,卻沒能解開我心中的疑問。我覺得文體可以打通,但應有一定的界限。在這點上,我認為《馬橋詞典》幾乎做到了完美。
2013年,韓老師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其第三部長篇小說《日夜書》。9月17日,我參加了在長沙九所賓館召開的研討會。韓老師的三部長篇《馬橋詞典》《暗示》《日夜書》都是知青題材,但《馬橋詞典》含蓄著田園牧歌式的風味,《暗示》帶有飄忽詭秘的詞語氣息,《日夜書》則呈現出更多的時間況味和史詩特征,看似隨意點染、零散回憶、片段敘述,韓老師以極為嫻熟的穿花插葉之功,將質地截然不同的半個世紀打成一片。我一直在想,這部長篇小說為什么要叫《日夜書》?我在一篇評論中寫道:“人畢竟是人,無論遭受捆縛、禁閉還是迫害、侮辱,總會有人絕處逢生,在漫漫長夜中窺見黎明的光影。目前為止的人類社會,既沒有永遠的黑夜,也沒有永遠的白晝。或許,日夜交錯,光與黑的纏斗,星與云的糾結,是大自然的宿命;而悲欣交集,治與亂的博弈,清與濁的對抗,則是人類繞不過的永恒命題。”
三
2014年3月,“湖湘教師讀書論壇”策劃者黃耀紅找到我,詢問邀請韓少功老師擔任4月中旬在湘潭舉辦的讀書論壇主講嘉賓的可行性。我給韓老師發郵件,第二天收到老師的回復:“昕孺你好。剛剛高興地看了《湖南文學》上你的專輯,就接讀來信。四月中的時間有點緊,我擬十五號自駕到湘西,看望一下黃永玉,十八號到汨羅,安頓幾天后就是下旬了,可能與你們的時間不大合。要不下一屆活動我再參加?祝創作再迎春天!”
耀紅看了這封信,決定就韓老師的時間,將論壇推遲到4月25、26日兩天。我再征求老師的意見,老師說:暫時這么定吧。我趁熱打鐵,趕緊將論壇的策劃方案《微時代:讀書是心靈的還鄉》傳過去,以便老師早做準備。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4月24日,即論壇開幕的前一天,我正在單位食堂吃飯,接到韓老師的電話,說他嚴重感冒,發高燒,咳嗽不止,可不可以……然而,當聽我說到有數百名中小學語文教師整裝待發,主辦與承辦單位已經做了大量工作時,韓老師在那邊笑呵呵地說:“我把藥的劑量加大點,認真對付感冒,力爭成行。”
放下手機,我滿身是汗。那一整天我都在祈禱,坐立不安。翌日中午1點,我和妻子敏華坐上單位周哥開的車,冒著那個春天最大的雨,緩緩行駛,前往梓園接韓老師和師母。
25日上午9點,短暫的開幕式之后,韓老師講課開始。我作為主持人,沒有著意渲染老師的創作成就以及獲了多少獎之類,那些在網上都搜得到,而是著重向臺下聽眾介紹了韓老師的諸多特異之處:他是最早一批沖破“文革”遺風、寫出現代小說的中國當代作家,又率先倡導致力于回歸傳統的“尋根文學”;他是最早將西方現代經典翻譯到中國來的作家之一,又是中國新時期下海的第一批作家;他成功創辦《海南紀實》與改造《天涯》雜志,又是中國唯一一位半年住在城市、半年住在鄉村的作家……
韓老師的講課讓數百名聽眾茅塞頓開,大呼過癮。他說:“當前我們的危險不是無知,而是知道得太多,信息過剩。我們看似知識分子,其實是知道分子而已。”“吃飯要適量,營養結構要合理,閱讀也一樣,并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有魯迅、胡適之才,但可惜的是在互聯網中缺乏高水平和高質量的參照,很多人被他人的點贊搞糊涂了,從而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以中外經典和真正的高手為參照,我們才能有真正的提高。”……
吃過中飯,我和敏華又將老師和師母送回梓園。雨停了,蘭家洞水庫煙水迷蒙,有如夢幻。梓園內則花木扶疏,江南春天的濕氣里總是包蘊著別樣的生氣。與老師告別時,一道光芒穿過繁茂的枝葉,射到我們頭頂,小徑上的水跡霎時閃亮如銀。它們仿佛在同一部詞典里,表現著不同的暗示。而這梓園里的風光霽月,恐怕是一部永遠也寫不完的日夜書吧。
(責任編輯 蔣茜 7405021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