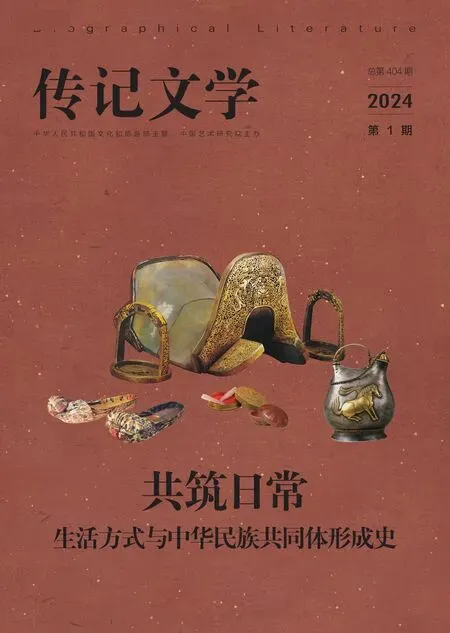“一杯滿瀉蒲桃綠”:葡萄與葡萄酒中的文化融合
蒲 帥

張騫出使西域圖,敦煌莫高窟第323 窟
漢家西域是誰開,博望功成事可哀。
斷送壯夫知幾許,換將胡物過東來。
——鄭文康《讀張騫傳》
這是明人鄭文康在讀罷《張騫傳》之后寫下的詩篇。詩人認為張騫出使西域耗費了無數人力物力,因此對漢家遣使鑿空西域的行為持否定態度。詩篇后兩句采用對比手法,本意在于批判張騫通西域之舉費巨功小,但尾句所言的“換將胡物過東來”卻也并非虛謬,客觀上的確有無數“胡物”借助這條絲綢之路被引入東方,例如核桃、石榴、苜蓿等物產皆屬此列。當然,其中也少不了本文所要討論的主角——葡萄。
葡萄,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又被稱為“蒲陶”“蒲桃”或“蒲萄”等,可謂名目繁多。關于其命名由來,李時珍在《本草綱目·果部》中稱“葡萄漢書作蒲桃,可以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1]劉衡如、劉山永、錢超塵、鄭金生編著:《本草綱目研究》下冊,華夏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65 頁。,以“酺醄”二字解釋葡萄之得名,其中“酺”為聚飲之意,“醄”則指沉醉之貌,將人在飲用葡萄酒后的醺然醉態作為這種西域傳入水果的命名依據。
以此種方式闡釋“葡萄”的命名,顯然重視釀造而成的葡萄酒遠甚于葡萄本身,故而此種解釋并未得到廣泛認可,目前更加被接受的觀點則相信“葡萄”應當是音譯名。有學者考證,“葡萄來自大宛,此詞應是大宛語budaw 的對音,與伊蘭語bud?wa 相對應”[2]楊泓、孫機:《我國古代的葡萄和葡萄酒》,《尋常的精致》,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191 頁。關于葡萄名稱的音譯問題,常有人會提及其得名來源于希臘語中表示“一串葡萄”含義的單詞或地名單詞,對此,書中亦有相關討論:“早年西方漢學家在言必稱希臘的觀念支配下,認為葡萄是希臘語bǒtrus(一嘟嚕[葡萄])的對音。但大宛并不流行希臘語,此說連伯希和也不相信。”。外來語的對音在翻譯之初往往缺乏定字,音譯說合理解釋了古籍中“葡萄”一詞多名的現象。然而,從這種命名依據中,亦能夠看出葡萄這種水果與釀酒存在重要關系。
“等閑不博涼州牧”:西來的葡萄與難得的瓊漿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
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
——蘇軾《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
蘇軾詩歌中提及的“伯郎一斗得涼州”,指的是漢代時孟佗以一斛葡萄酒賄賂宦官取得涼州刺史官職之事。裴松之在注解《三國志》時,曾引用《三輔決錄》中的記載言稱(孟佗[3]《三輔決錄》中記載“孟佗”名為“孟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1](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版,第355 頁。東漢靈帝在位之時,以“十常侍”為首的宦官集團把持朝政,天下奇珍異寶無不匯聚于宦官之手。在此種社會背景下,孟佗僅以一斛葡萄酒之量賄賂宦官首領張讓,便換得了一州刺史之高位,足見此時雖有絲綢之路與西域相通,但產自大宛、安息一帶的優質葡萄酒并未大量輸入中原地帶,至漢末時葡萄酒對于華夏民族而言仍是罕貴之物。
事實上,史書所載的高品質葡萄與葡萄酒雖多由西域傳入,但中原地區卻并非缺乏葡萄屬的植物,如今在《詩經》文本中,我們仍舊能夠看到先民食用葡萄屬植物的相關記載[2]除下引的《豳風·七月》一篇之外,《詩經·王風·葛藟》與《詩經·周南·樛木》等篇目中出現的“葛藟”同樣是一種葡萄屬植物,但兩詩內容均未圍繞葛藟展開,葛藟在詩中僅起到即物起興的作用,故不在正文作詳細展開說明。: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詩經·豳風·七月》)
《豳風·七月》描述了周人一年四季的農事活動,詩中提及多種可食用植物,此處的“薁”,指的便是葡萄屬植物蘡薁[3]《豳風·七月》詩篇中的“薁”所指究竟為何物,歷來有多種說法,如《說文解字》中即解釋“薁”為“櫻也”。此處根據程俊英《詩經譯注》中的說法定其為“野葡萄”。參見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第230 頁。,李時珍《本草綱目》中記載:“蘡薁蔓生,苗、葉與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碗者。冬月惟葉凋而藤不死……蘡薁子生江東,實似葡萄,細而味酸,亦堪為酒。”[4]劉衡如、劉山永、錢超塵、鄭金生編著:《本草綱目研究》下冊,華夏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66 頁。雖然稱其“堪為酒”,但史書中罕有以蘡薁為原料大量釀造葡萄酒的記載。以賈思勰所撰的《齊民要術》為例,在這部詳細記載民間農業智慧與生產經驗的總結性書籍中,作者對葡萄有著明確描述,也詳細記錄了各種釀酒方法,卻并未出現任何利用蘡薁釀造葡萄酒的記錄[1]參見《齊民要術》中第四卷“種桃柰第三十四”與第七卷“造神曲并酒等第六十四”至“法酒第六十七”等部分的相關內容,(北魏)賈思勰撰,石聲漢譯注,石定枎、譚光萬補注:《齊民要術》,中華書局2015 年版。,由此可知古人對于以蘡薁為代表的本土野葡萄資源并未進行成規模的開發利用[2]部分考古發現中曾出現過先民使用野葡萄釀酒的相關例證,如1980 年在河南商代后期古墓中曾發現過一個密閉的銅卣,經專家分析后認定其中盛裝的便是葡萄酒(參見牛立新編摘:《保藏三千年的葡萄酒》,《釀酒》1987 年第5 期);再如1995 年在山東日照兩城鎮文化遺址考察過程中,考古人員同樣發掘出葡萄籽遺存,并在部分陶器內壁上檢測出含酒的殘留物,據此認定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兩城鎮地區的古人就已經開始使用野葡萄釀酒。此類個例難以形成完整論證鏈條,只能據此推斷認定古人知曉食用野葡萄及利用其進行釀酒,但并未形成大規模釀造,其具體生產工藝也沒有以書面文本形式流傳后世。。

[日]細井徇撰繪《詩經名物圖解》中的薁(1848)
而與籍籍無名的野葡萄不同,自西域傳來的葡萄與葡萄酒很快成為深受中原人喜愛的明星物產。《史記·大宛列傳》對其發現與引入過程有如下記載: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3](漢)司馬遷撰, (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引,(唐)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十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60 頁、第3173—3174 頁。
由此段記載可知至西漢時,中原地區已經依靠“漢使取其實”[4]《史記》只提及“漢使取其實來”,關于葡萄何時經何人之手自何地傳入中原的問題,古來便有多種觀點:《酉陽雜俎·卷十八》中提及(葡萄)“實出于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 《白孔六帖》則記載“或以為李廣利破大宛,得種歸漢”,《本草綱目》則指出“張騫使西域還,始得此種”等,以上諸說可備作參考。于大宛而開始種植葡萄,但結合前述孟佗“一斗得涼州”的事跡判斷,西域相對成熟的釀酒技術似乎并未隨之傳入,那些種植在離宮別觀旁的葡萄成熟后也不曾被釀造成醇香甘洌的葡萄酒,這種由西域進貢而來的瓊漿在兩漢時期仍為奇物。
前輩學人論及此事時常會提到一本名為《漢武帝內傳》的書,書中在描繪漢武帝招待西王母的場面時,有“設玉門之棗、酌蒲桃之酒”這樣的措辭。然而是書雖托名為班固所撰,實則是后人假借其名編纂的傳奇小說,《四庫全書總目》稱其當為魏晉時人所作[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評點此書時指出:“《漢武帝內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隋志》著錄二卷,不注撰人,《宋志》亦注曰不知作者,此本題曰班固,不知何據。殆后人因《漢武故事》偽題班固,遂并此書歸之歟?《漢書·東方朔傳贊》稱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此書乃載朔乘龍上升,與傳贊自相矛盾,其不出于固,灼然無疑。其文排偶華麗,與王嘉《拾遺記》、陶弘景《真誥體格》相同。考徐陵《玉臺新詠序》有靈飛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實用此傳六甲靈飛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語,則其偽在齊、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詩》,有漢武非仙才句,與傳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語相合。葛洪《神仙傳》所載孔元方告馮遇語,與傳中稱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云云相合。張華《博物志》載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云車來云云,與此傳亦合。今本《博物志》雖真偽相參,不足為證。而李善注《文選·洛神賦》已引《博物志》此語,足信為張華之舊文,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為乎?”參見(清)永瑢等: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五冊,中國臺灣藝文印書館1964 年版,第2788—2789 頁。判斷此書出于魏晉時人手筆。,書中內容也盡數屬于充滿奇幻色彩的臆想內容,故而并不足以作為漢朝飲用葡萄酒的真實情況的參考。真正能直接反映時人對葡萄酒態度的記載,首推三國時魏文帝曹丕的品評,大概是因為瓊漿難得,曹丕特意寫下《涼州蒲萄詔》盛贊葡萄與葡萄酒:
旦設蒲萄解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悁。又釀以為酒,甘于麹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2](清)張澍輯錄,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周鵬飛、段憲文點校:《涼州府志備考·藝文卷一·魏文帝涼州蒲萄詔》,三秦出版社1988 年版,第573 頁。關于此段引文內容,《藝文類聚·卷八十七·果部下·蒲萄》與《太平御覽·果部卷九·蒲萄》中均有記載,且文前皆有“魏文帝詔群臣曰”句。《全三國文·卷六》列其于《詔群臣》題下,《魏文帝集》中將此段標題為《與吳監書》,其內容則與《太平御覽》相類(參見(三國魏)曹丕著,易健賢譯注:《魏文帝集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204 頁)。《本草綱目·卷三十三》援引此段記載為“蒲桃當夏末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長多汁,除煩解渴。又釀為酒,甘于麹蘗,善醉而易醒,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乎?”(參見劉衡如、劉山永、錢超塵、鄭金生編著 :《本草綱目研究》下冊,華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65 頁。)幾處引文措辭雖略有出入,但仍可認定當源于同一文本。
曹丕給予了葡萄極高的評價,認為這是天下無匹的果中之王,單是描述其甘美滋味便足以令人口舌生津。而從曹丕的描述中也不難看出,不論是作為水果的葡萄還是由其釀造而成的葡萄酒在當時皆屬不易獲得的珍品,哪怕貴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也對其心向往之。
類似的情況至南北朝時期依然存在,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洛陽白馬寺周圍已有葡萄種植,其“枝葉繁衍,子實甚大,荼林實重七斤,蒲陶實偉于棗,味并殊美,冠于中京”[3](北魏)楊衒之撰,俞婉君譯注:《洛陽伽藍記》,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5 頁。。對于當時人而言,葡萄仍舊是罕貴難得之物,以至于普通宮人得到皇家賞賜的葡萄后,都要先當作至寶遍傳親屬各家再食用:“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1](北魏)楊衒之撰,俞婉君譯注:《洛陽伽藍記》,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5 頁。
《北齊書》中亦有類似對葡萄珍貴程度的描繪,李元忠“曾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2](唐)李百藥:《北齊書》上冊,中華書局1972 年版,第315 頁。。《新唐書》記載陳叔達得到高祖李淵賞賜后,“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愿歸奉之’”[3](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十三冊,中華書局1975 年版,第3925 頁。。此故事中陳叔達的言行頗類于春秋時期勸諫鄭莊公的潁考叔,而作為其中關鍵的葡萄,顯然同樣因其珍貴,成為了臣下彰顯孝道的最佳憑據。
葡萄罕貴難得,直接影響了葡萄酒的身價隨之水漲船高。對于古人而言,在葡萄酒釀造技術尚不完備的時期,想要喝到這種能令魏文帝聞之垂涎的瓊漿,基本只能依靠西域諸國進貢。上千里的距離對于絕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已不啻天淵,因此對當時人而言,能沉醉于葡萄酒中已是近乎人間極樂的想象。譬如庾信的《燕歌行》尾聲部分,便將痛飲葡萄酒與服丹求仙等量齊觀: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新壓葡萄酒如乳”:中西融合的葡萄酒釀造工藝演進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曲紅。
相逢不令盡,別后為誰空。
——王績《過酒家》其三
這是嗜酒好醉的唐代詩人王績描繪的飲酒場景,其中“蒲萄帶曲紅”一句,為我們理解唐人釀造葡萄酒的真實狀態提供了生動形象的文本樣例。與我們今天尋常易見的葡萄酒有所不同,唐代釀造葡萄酒時還特別向其中添加了酒曲,因而才會出現所釀之酒“帶曲紅”的特殊景象。釀造葡萄酒時添加酒曲堪稱華夏先民獨樹一幟的特色,而想要參透這一行為背后的思維邏輯,首先需要簡單了解釀酒的一般過程與基本原理[1]本文所介紹的釀酒方面相關內容參見單銘磊主編:《酒水與酒文化》,中國物資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14 頁。。
古往今來,釀酒用的原料大致包含淀粉類原料與糖質類原料兩種。不論是以大米、高粱、小米、玉米等各種淀粉類原料為主釀造的糧食酒,還是以葡萄、蘋果等各種糖質類原料為主釀造的果酒,在釀造原理上實則異曲同工,均是將原料中的糖借由發酵轉化成酒精,發酵因此是整個釀酒過程中最為關鍵的環節[2]關于發酵,雖然人類有著悠久的釀酒歷史,但直到19 世紀中葉,微生物學家巴斯德才研究出酵母酒精發酵的生理意義,提出發酵是酵母在無氧狀態下的呼吸過程(即無氧呼吸)。。在酶的催化作用下,釀酒原料的單糖被分解成酒精、二氧化碳與其他物質,這一過程便被稱為“酒化”,以葡萄糖的酒化為例:
根據測定,每100 克葡萄糖理論上可以產出51.14 克酒精,以此法制成的發酵酒,其乙醇含量一般上限為15%[3]原因在于當發酵過程中酒液里的酒精含量達到13%—15%時,酵母即會停止活動,發酵也就隨之結束了。。但中國古代常用各類淀粉類原料釀酒,其中并不天然具備豐富的糖分,而是需要先將淀粉溶于水,在淀粉酶的作用下將淀粉水解為麥芽糖和糊精(多糖),再利用麥芽糖酶,進一步將麥芽糖水解為葡萄糖,為后續的酒化過程做好準備,這一將淀粉轉化成葡萄糖的過程,便是釀酒工藝中的“糖化”。
理論上講,100 千克淀粉可摻水11.12 升,產生111.12 千克糖,再轉化為56.82 升酒精。糖化淀粉往往需要相對漫長的過程,而為了加速糖化過程使用的糖化劑,便是我們一般意義上常說的“酒曲”[4]囿于篇幅與主題所限,本文對于酒曲的描述僅限于基本原理,并未作詳細展開。例如并未細致區分“曲”(發霉谷物)與“蘗”(發芽谷物)在酒曲中的不同等,特此說明。,即長出了曲霉的發霉谷物,可以用作糖化過程的催化劑。相應地,在谷物上培養曲霉的過程便被稱為“制曲”。使用酒曲的意義在于加速糖化過程、提高糖化水平,進而全方位提升釀酒速度與品質。
理解上述原理后,我們便不難發現使用酒曲的前提是利用各種淀粉類原料釀制糧食酒。而像葡萄這樣本身就富含果糖的糖質類原料,實際在釀造過程中可以直接酒化產生酒精,并不需要額外添入酒曲增加糖化過程。
事實情況亦如此,結合現有文獻資料來看,不難發現在歷史上西域地區釀造葡萄酒基本都是直接自然發酵。王光堯在《古代葡萄酒釀造技術的東來及變化——海外考古調查札記(八)》一文中介紹了阿聯酋朱爾法遺址酋長故居博物館中保存的當地椰棗蜜作坊,與《順天府志》記載的高昌地區葡萄酒生產作坊構造、生產方式均相同,皆是將原料置于室內地面搗碎,汁液順著地上的溝渠匯入一口嵌入地下的缸內,待自然發酵后取出即成[1]參見王光堯:《古代葡萄酒釀造技術的東來及變化——海外考古調查札記(八)》,《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 年第6 期。。
除考古資料外,在現存的唐以前的文獻中,罕有對中原地區引進西方葡萄酒釀造技術情況的明確記載。根據前引曹丕詔書中盛贊葡萄酒“甘于麹米”的說法可以簡單進行推斷,兩者之間存在可比性,很可能意味著采用了兩種釀造方法。唐代之后關于西域使用自然發酵法釀制葡萄酒的記錄逐漸增多,例如南宋周密在其《癸辛雜識》中即記載:“回回國葡萄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2]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5779 頁。
從技術傳入與接受的角度考慮,古人最先接觸到的應該是自然發酵釀造法[3]根據考古資料的證據,甘肅天水曾出土有粟特人墓葬棺床石雕,上有池內踩踏葡萄并通過導管引出液體注入罐內的造酒圖樣,說明來自西方的以自然發酵方式釀造葡萄酒的方法確曾傳入中國。。《南部新書》記載:“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種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4](宋)錢易撰,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32 頁。其中使用的“損益”二字,證明這是在借鑒西釀酒法基礎上形成的改進技術,而文段提及“造酒綠色”[5]“造酒綠色”一句另有本作“造酒成綠色”,《冊府元龜》卷九七〇轉引此條時作“造酒成八色”,系為訛誤。后部分學者據此稱太宗時掌握了多種釀造技法,能夠釀出各種不同顏色不同種類甚至不同風味的葡萄酒,則誤之又甚。,則說明此法依舊采用自然發酵釀造,并未加入酒曲導致發生變色[6]此處結論僅為大致判斷,因為對于葡萄酒而言,即便是在自然釀造法內部,仍有兩重更為細致的分類,視選料時是否剔除果渣、果肉、果皮等其他成分劃分為了紅葡萄酒(保留所有成分)與白葡萄酒(只使用葡萄果汁)兩種類型,因此并不能根據顏色簡單判斷加入酒曲釀酒結果即呈現為紅色。但是在唐朝時期,利用自然發酵獲得的綠色葡萄酒對唐人而言并不稀見,李白所作《襄陽歌》詩中即有“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酦醅”之句,可互證參看。。
葡萄種植與葡萄酒釀造在唐代均獲得了長足發展,劉禹錫寫有《葡萄歌》,專門描繪了唐時山西一帶已形成專門種植葡萄釀造葡萄酒的產業結構:“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詩篇所描繪場景縱有藝術夸張成分,亦可由詩句內容想知唐時在西北地區,葡萄酒釀造產業已然蔚為大觀。

明代《食物本草》宮廷手繪彩本中描繪的葡萄酒釀造圖
盡管從原理上看,葡萄酒的釀造過程并不需要酒曲協助,但隨著時間推移,華夏民族將自身擅長的借助酒曲釀酒的方法添加進了葡萄酒的釀造過程之中,自西方傳入的釀造技術逐步與華夏地區原有釀酒理念相融合,進而出現了借助酒曲釀造葡萄酒的新思路、新方式。
例如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箋》中記錄的完整葡萄酒釀造方法,就能看到酒曲的身影:“法用葡萄子取汁一斗,用曲四兩,攪勻,入甕中封口,自然成酒,更有異香。”[1](明)高濂撰,王大淳、李繼明、戴文娟、趙加強整理:《遵生八箋》,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 年版,第386 頁。顯然這是一種文化融合的結果,添加酒曲拓展了葡萄酒的釀造方式,展現出與西方釀造法迥乎不同的思路方式[2]關于中國古代使用酒曲釀造葡萄酒的問題,還有另一種說法可供參考:清人劉岳云在《格物中法·卷六下》中曾解釋過用曲問題:“葡萄釀者,今通行之法是蒸者……前言不用曲,今又言用曲者,緩釀不用曲,速釀用曲也。”由此觀之,則知古人在釀造葡萄酒時選擇添加酒曲,主要考慮的并非酒的風味,而是著眼于釀造速度快慢與否,利用酒曲的催化效果來加快釀造過程,進而提高葡萄酒產量。此論可備為一說,故錄于此。。
但釀造技術的融合發展同樣并非一帆風順,囿于時局戰亂等因素的影響,葡萄酒釀造技術一度瀕于失傳。元好問在其《蒲桃酒賦》中記載“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時人甚至“摘其實并米炊之”,所釀之酒在風味上完全失去獨特口感,直至避亂時偶然發現器皿中貯存的葡萄“熏然有酒氣”,方才重新發現了以自然發酵法釀造葡萄酒。元好問特地為此時作賦紀念,足可見古人對釀酒技術革新改造的重視程度。
隨著時代演進,不同的釀造方法得以齊頭并進、并行不悖。至元代時,文人周權還特地寫作《蒲萄酒》詳細記載了釀造葡萄酒的各個流程步驟,其中既有搗碎原料自然發酵的部分,亦有加入酒曲調和風味的步驟,堪稱東西方釀酒技術巧妙融合的典范象征,其詩云:
翠虬夭矯飛不去,
頷下明珠脫寒露。
累累千斛晝夜舂,
列甕滿浸秋泉紅。
數宵醞月清光轉,
濃腴芳髓蒸霞暖。
酒成快瀉宮壺香,
春風吹凍玻璃光。
甘逾瑞露濃欺乳,
曲生風味難通譜。
縱教典卻鹔鹴裘,
不將一斗博涼州。
飛入尋常百姓家:作為文化符號的葡萄與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王翰《涼州詞》其一
除了實際的食用功能外,葡萄與葡萄酒還往往出現在歷朝歷代的文學作品與生活裝飾中,逐漸演化為體現文化交融的重要文化符號。而要論起描寫葡萄酒的名篇,王翰的《涼州詞》堪稱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作品。在這首我們耳熟能詳的詩篇中,詩人描繪戰士在踏入戰場前痛飲葡萄美酒,甚至豪言要醉臥沙場,一股凌駕于殺伐之上的萬丈豪情由此呼之欲出,使得整首作品展現出強烈的慷慨灑脫之感。
不畏戰,不怯戰,戰士面對戰場表現出了一往無前、睥睨生死的昂揚姿態,這在古代邊塞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別具風味的情緒表達。一個新的詩歌意象由此產生,并逐漸走向豐富與完善,在之后的詩歌長河中留下了屬于它自己的色彩。它表現為“幾回兀坐穹廬下,賴有葡萄酒熟初”(汪元量《通州道中》),表現為“昭陵百戰大山河,涼州幾甕葡萄酒”(艾性夫《題明皇醉歸圖》),也表現為“等閑不博涼州牧,留薦瑤池第一觴”(蘇葵《葡萄酒》)。描述征戰、宣泄憤懣、懷想生活、期盼美好,詩人慣常使用的典型意象得到拓展,兼具有文化融合特征的葡萄成為了邊塞之地戍守之人溝通情感的理想選擇。
在此類詩篇作品中,還有一層隱含的立場需要特別點明,那就是“葡萄酒”意象本身所具有的身份代表性。不同于高適的《燕歌行》中“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種著力展現普通士卒疾苦心酸的表述角度,“葡萄”與“葡萄酒”所能象征的群體往往更多是貴族與官僚。哪怕是在“霜營吹角客愁孤”(汪元量《通州道中》)的無限離思中,能借新釀葡萄酒消愁者也只能是統御兵馬的將軍,而非更具代表性的絕大多數普通戰士。
所以《涼州詞》中表現出的慷慨灑脫其實是有身份、有立場的。更有甚者,我們還能夠在李頎創作的《古從軍行》中讀到這樣的詩句:“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不同于其他引用的作品,李頎在詩中雖然同樣使用了“葡萄”意象,但在態度上作者卻旗幟鮮明地站到了“葡萄”的對立面。詩句中的“戰骨”與“蒲桃”形成了鮮明對比,無數人的犧牲換來的不過是一點微不足道的貢品罷了。相較此前詩篇中尚且只是將葡萄酒視作消愁之物,李頎的創作無疑再次拓展了意象涵義的邊界,同時也著重強調了“葡萄”往往象征權貴的特殊屬性。
華夏文明對待“酒”的情感是復雜的。早在三千年前武王伐紂結束后,周公便在衛國推行禁酒理念,發布了以《尚書·酒誥》為代表的禁酒誥令,提出要以德行標準要求自身,強調“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周人將殷商王朝的失敗部分歸咎于酗酒誤事,歷朝歷代皆不乏縱酒致禍的好飲貪杯之徒;儒家的禮法制度強調人要對自己有所規誡以達到“克己復禮”的程度,即便是以縱情自娛著稱的道家,也同樣堅決反對酗酒[1]早期道教重要經典《太平經·丁部》中有對酗酒者懲罰的明確規定:“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謂吏民言:從今已往,敢有市無故飲一斗者,笞三十,謫三日;飲二斗者,笞六十,謫六日;飲三斗者,笞九十,謫九日。”。
葡萄酒天然量少難得的屬性,加上古人對于飲酒的復雜情態,兩者作用下人人痛飲葡萄酒的豪邁場面固然無法在當時成為社會主流,但葡萄酒作為文化符號的再發現與再利用仍為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生態增添了一抹來自異域的亮色。
而在華夏民族中,新型文化元素的發展還將繼續引領潮流,唐人對于葡萄酒的喜愛,逐漸演變發展,影響了唐代盛行的“酒暈妝”的出現。據古籍記載,所謂“酒暈妝”指的是在傅粉后于兩頰處涂抹調勻的胭脂,使雙頰呈現出宛若醉態般的紅暈。“酒暈妝”是一種相對較為濃艷的妝容,其更為輕淺的版本則被稱作“桃花妝”[2]唐人宇文士及在《妝臺記》中記載:“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故而所謂的“酒暈妝”實指的是人在醉酒后面色酡紅的感覺,葡萄酒“善醉而易醒”的特點想來也必然對酒暈妝的形成助力頗多。

唐代 《弈棋仕女圖》 中化“酒暈妝”的女子

敦煌莫高窟第209 窟中的石榴葡萄紋樣

敦煌莫高窟第322 窟中的纏枝葡萄紋邊飾
除詩文外,葡萄圖案作為裝飾紋樣還廣泛應用于各種藝術作品與日常器物中。敦煌莫高窟中即多見以葡萄紋作為巖窟壁畫中的裝飾元素,如第322 窟纏枝葡萄紋邊飾,用葡萄本來意象展現出中秋時節瓜熟果落的團圓景象;再如第209 窟藻井中的石榴葡萄紋樣,將兩種均以“多子”著稱的水果搭配使用,寄托著古人“多子多福”的樸素思想與美好祝愿,葡萄枝藤纏繞的狀態還象征著親密與繁榮,同樣表達的是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與企盼。此外還有在唐代盛行一時的經典銅鏡紋樣海獸葡萄鏡[1]據宋代《博古圖錄》、清代《西清古鑒》等文獻記載,海獸葡萄鏡又被稱作“海馬葡萄鏡”“禽獸葡萄鏡”“天馬葡萄鏡”等,別名眾多但紋飾大同小異。,該鏡面的一般形制特征是裝飾圖案以海獸形象為主,周圍配飾以葡萄藤蔓紋。“海獸”原型為何物古來眾說紛紜,古人多認為其所指的是龍生九子中的“狻猊”,而今人則更認同其原型當為獅子。不論葡萄還是獅子都是典型的域外生物,自傳統東土后顯現出了溝通文化差異、締造文化紐帶的獨特價值,因“多子”“富貴”等寓意制作的海獸葡萄鏡,也因此被稱作“凝結歐亞大陸文明之鏡”。
不論帶有宗教儀式色彩的石窟裝飾,還是更強調世俗價值喜好的銅鏡花紋,上述例子中都存在一種引人矚目的共性:在東方的文化語境與文化視域之下,作為外來物種的“葡萄”身上異域價值觀念中的文化成分被逐漸剝離,并被重新賦予了一種更符合東方審美趣味與文化樣態的嶄新內涵。
美國漢學家謝弗在其《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所作的總結可謂切中肯綮。他注意到:“由于唐朝勢力迅速擴張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內變得家喻戶曉了。甚至到了唐代,葡萄在人們的心目中還仍然保持著與西方的密切關系:在幾百年中,一串串的葡萄一直被當作外來裝飾的基本圖樣而在彩色錦緞上使用;而在唐鏡背面的‘古希臘藝術風格’的葡萄紋樣式,則更是為世人所熟知。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羅馬人、大食人以及西域的回鶻人等,全都以精于栽種葡萄和善于飲酒而知名,但是當唐朝征服了西域之后,葡萄以及葡萄汁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某些‘外國’的風味,這與‘半外來的’巴旦杏和檳榔的情形是很相似的。”[1][美]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版,第309—310 頁。
這便是橫跨東西的所謂“溝通”與“融合”的真意所在。與其他西來之物相類似,葡萄自東傳進入到華夏大地的文化視野后,同樣表現出了極為明顯的融合特征。不論是兼用酒曲的釀造方式融合新變,還是活躍在唐代的無數異域“酒家胡”;不論是唐詩風潮中那一抹雄奇靚麗的異域色彩,還是反映在日常生活紋飾中的審美樣態。以葡萄為代表的東西方物質文明結晶就在這一用一釀、一詩一文中悄然實現著新的融合與發展,成為文化交流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論東方還是西方,當我們舉起夜光杯、共飲葡萄美酒之時,或許所有的差異與隔閡都已不再重要,杯中美酒代表的是我們對于幸福生活的一致追求,是我們對于美好未來的共同企盼,只要我們共同懷揣著這樣的理想信念,那么所有的溝通與交流就都是水到渠成的自然過程。正如同千余年前的唐太宗李世民寫下《置酒坐飛閣》時,眺望著遠方無盡的山川之色,當時節心中所產生的無限感慨喟嘆,也全都盡數付與眼前的這一杯之中:
高軒臨碧渚,飛檐迥架空。
馀花攢鏤檻,殘柳散雕櫳。
岸菊初含蕊,園梨始帶紅。
莫慮昆山暗,還共盡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