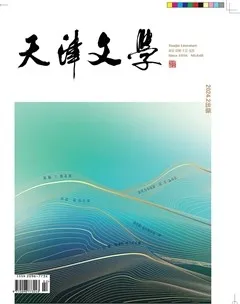北京秋事
1
我至今相信,緣分不是一件患得患失的事兒,無論腳步是快是慢,它的軌跡從未偏移那個即將相遇的地方。就像北京的秋天,一直在等待相遇衍生的驚喜和驚異。
81歲的父親,因胃不舒服,經歷了縣市多個醫院半個多月的醫治和專家會診,沒有發現胃的問題,卻發現心臟三根血管正在抗議。左前降支紅燈閃爍,提示此路已嚴重堵塞。另兩條的紅燈也停在80%處警示。考慮到父親的年齡,支架手術存在風險,醫生建議,馬上進行心臟搭橋手術。家里一場地震般的慌亂后,決定立即去北京為父親做搭橋手術。
北京西三環日壇南路,我的車沒能跟隨最后一格綠燈沖過路口,停在了紅燈的最前沿。導航顯示的紫紅色擁堵,讓我想到父親被堵的血管。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33人的首都,每一個針孔里都可能住著一個人。著急是沒用的,這時,一位交警隨一片落葉一起飄到車前,禮貌地敬禮,標準的普通話。車開到警亭旁,詢問進京原因,出示證件,開具罰單,并告知:外地車輛不允許進入三環以內。進京證要七天一審核。他看了看坐在后座的父親說:走輔路,一直下去就到了。我不知道多少年后是否還記得這個輕描淡寫卻心急如焚的秋天,但此刻,北京對父親來說就是再生地。此時我用眼睛去搜尋它與眾不同的地方——與我的城市不同的色調;車與行人的密度;樓的高度或云朵的行蹤。
父親住的阜外醫院,據說具備國內比較權威的心臟搭橋手術技術。雖然這種手術在很多省市級醫院早已成熟,但妹妹還是通過朋友找到了一個在這兒工作的同學,經過電話短信的反復咨詢,終于把一家人的希望放在了首都的這家醫院。
醫院不允許陪床和探視,只需買好術前、術中、術后各階段所需用品,守候在醫院附近,隨叫隨到即可。入院前的一系列檢查一個都不能少,驗血、驗尿,檢查心電圖……各種檢查后,醫生對父親說:“您是我們這兒有史以來年齡最大但血壓最正常的病人,一定要再創造一個奇跡。”父親笑了:“奇跡是奇人創造的,普通人創造奇跡壓力太大。”
父親表情淡定,腳步沉穩,住院部那扇大門即將關閉。他突然站定,回過頭向我揮手,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這一眼,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眼前總是出現父親站在碼頭孤單遙望的畫面,心里會莫名地疼一下。
父親的手術從下午1點進行到5點45分。將近5個小時,這是和時間拼耐心的時候。對面墻上的電子屏幕,幾臺同時手術的病人的名字一個一個在減少,最后只剩下三個。我和家人在等候區來回重復著“踱步”“坐下”“起來”“看屏幕”這幾個動作。時間只管嘀嗒嘀嗒敲鐘般從我心上踩過,每一聲都讓我心驚膽戰。等待成了我在此時的唯一任務。等待手術的大門打開,等待父親醒來,等待東方的魚肚白趕走沒有情趣的黑夜。就像兒時,等待父親從那場震驚世界的大地震中歸來。
2
那年的大地震來臨時,父親正在參加省先進代表大會,一群各行各業的先進代表,晚上還聚在一起談生產談家庭談明天,幾個小時后,三層的招待所大樓和這些人的夢一起碎了一地。碎磚亂瓦伴著呼喊聲四處飛濺。住在一樓的父親在大樓倒下前的幾分鐘醒來,大聲喊著“快跑”,同時一手一個拽起同屋的室友,借助震波的慣性,被從窗口甩出。最后的一堆磚頭,擦著父親的右腳后跟一起落地。招待所瞬間夷為平地,磚瓦的嗚咽和大地哭作一團。一夜的小雨掩蓋了塵土的慌張,卻讓凄厲的呼救聲、哭喊聲此消彼長。上天的眼淚在天亮時流干了,人的眼淚卻串成了剪不斷的線。父親的右腳后跟血肉模糊,他顧不上,他和兩個室友循著地下的聲音扒著磚頭瓦塊。可三個人怎么會是三層樓的對手?在鋼筋水泥面前,三個血性的漢子蹲在地上放聲大哭。
回家的路,漫長又辛酸,一路走,一路救人,撿到一只涼鞋,穿在左腳。撿到一只球鞋,穿到右腳。撿到一塊布,裹住身子。沒人相信父親還活著,沒人相信會有奇跡發生,包括我的家人和他的同事。35公里回家的路,父親走了三天。
第三天,太陽怯生生地露出頭來,它看到了大地失魂落魄的樣子,小心翼翼挪動著身影,從一個樹枝到另一個樹枝,這是它安慰人間的唯一方式。十一家人的臨時帳篷搭建起來,十一家人中已有七人死亡,還有下落不明的父親。人們的臉上像結了冰。整整三天,我坐在帳篷外的馬路上撿石子,這是父親每天下班回家的路,我相信,石子撿到一百顆時父親就會回來。
父親出現時,西去的太陽停下了腳步,光線聚焦在父親身上,為他鍍了一個金身。我遲疑著站起身來,沒錯,是父親。迅速跳起來扔掉手里的石子,向著父親的方向邊跑邊喊:“爸爸回來了,爸爸沒死。”帳篷里的人涌出來,呼喊,流淚,母親突然雙膝跪地,向著父親的方向……
3
我住在南禮士路的一家快捷酒店。從南禮士路到阜外醫院,步行,單向8分鐘,著急可以騎小藍車,符合醫院十分鐘到達的要求。早晨7點到8點,醫院要求家屬到醫院等消息。7點整,我抓起手機,準時向醫院出發。這一個小時,格外忐忑。盼著有01打頭的電話響起,又害怕電話響起。電話不響,期待父親的消息。電話響起,又擔心消息的好壞。天亮了又盼著天黑。如坐針氈地熬到下午5點,再來醫院等電話,聽醫生介紹病人病情。等電話的隊伍很長,每個家屬有兩分鐘時間傾聽和詢問。家屬按醫生點名的順序站成兩排,除了幾個熟悉的女家屬互相低聲詢問對方病人情況,沉默者居多,眼睛直盯著引導臺上僅有的一部電話,似乎那里裝著我們親人的生死。我站在這個隊伍里,這兩分鐘讓我緊張,我忘了自己是一名央企客服部的管理者,可以輕松應對二十多萬用戶的各種問題。我一遍遍想著該怎樣說話更簡練更明了,既要省時間又要問得全面。
電話放下的那一刻,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乎,父親會因為我的問詢加快康復的腳步。
4
“紙上聲音書店”的出現對我來說就像一劑安神藥。
我是在第三天邊走邊數路邊的電線桿時發現它的,它藏在凹進去的綠化帶后面。沒人能看到我口罩下面僵硬的笑容,我好像已經忘了“笑”這個動作。我必須去那里客串一個角色,我在北京等父親,它肯定是在這兒等我的。生活真是有心,它不愿看到我的落寞,便制造了一個驚喜。它知道我喜歡書,喜歡書里意想不到的變化和大千世界的神奇。我對自己說:“要讓它站在我的身后,支撐我,看我演練悲喜的表情。”
我是不假思索就走進去的。大門玻璃上粘貼的黃色玩具狗機械而溫柔地重復著人的聲音:“歡迎光臨。”書店有兩層,每層六七十平方米的樣子,看書的人并不多。上下結構一樣,一條不寬的圓形過道,靠墻的書架和中間書桌分門別類擺滿了書。夫妻二人各負責一個樓層,女主人負責一層和結賬。二層的咖啡屋可以要上一杯拿鐵或卡布基諾,坐下來閱讀。環顧左右,發現氛圍極其匹配“紙上聲音”這個名字。尋找、購買、翻閱,全程都在無聲中進行。
愛特加·凱雷特的《突然,響起一陣敲門聲》就是在那兒吸引了我,我怕它的敲門聲破壞了書店的安靜,翻看了十幾頁后便收留了它,以免再響起第四個拿槍人的敲門聲。郭文斌《永遠的鄉愁》在家早已成為我的座上賓,在這兒一眼看到它,覺得它更適合與大都市形成對比來閱讀。他說:“人生就像一場刺繡。”他相信緣分,等待緣分。我還沒悟透父親與北京的緣分,我在郭文斌“刺繡”的生活里想象父親在病床上的煎熬——開胸、縫合,十多個小時醒來后無意識地抓狂,疼痛是父親在北京的敘述方式,雖然一句他的傾訴我還沒聽到,但在一個耄耋老人身上完成的“刺繡”恐怕很難掩蓋疼痛的痕跡。想象心臟的驟停和電擊的畫面讓我眼神呆滯,停在書的某頁忘了移動。我明白,書的很多主人都敗給了時間,但文字的力量和教益能讓時間慘敗,我想我的父親也會讓時間慘敗的。
5
我突然發現了街上的熱鬧。
那些被我忽略的景色隨著父親醒來并漸好的消息聚到了我的眼前。大街上隨處可見“美團跑腿”“餓了么”的快遞身影風一樣閃過。公交車不急不慌地從南北東西駛來,擁堵讓它們聚在紅燈前調整情緒,然后繼續前行。記得有人說過:“如果看見一輛法拉利駛過,你可以騎上一輛‘青桔或‘哈啰追趕一番。不用氣餒,在北京,電動車是有機會超過法拉利的。”的確,在北京,快與慢、車輪與腳步,會友好地彼此謙讓。
路燈亮時,我坐進酒店外我的車里,關好門窗,陪我的車坐一會兒。我經常用這種沉默安撫我的焦躁,很管用。酒店門口戴著口罩的人進進出出。住進這種酒店的大多是阜外醫院病人的家屬。操著各種方言,神態焦灼。酒店外狹小的停車場經常停放著一些“魯B”“豫A”“陜C”等外地牌照的車。車開進來的大多是和我父親一樣病情緊急就顧不上禁行和被處罰的家屬。
我也曾站在阜外醫院東南的天橋上,像站在碼頭一樣斟酌“阜外”這兩個字,我更愿意把它們拆開看。“阜”——可以想象多少年前的碼頭、渡口,想象舟帆遠影,順著大運河南下,它會在河邊遇到我的城市,對一條河來說,北京與我所在的城市是一奶同胞的親人。這兩座城市的人也應該是兄弟姐妹吧。“外”——北京之外,我是把北京圈在里面,以一個外地人的眼光看圈內的。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仍能看到本地人的自豪。
6
見到那個東北母親時,我相信了羅曼·羅蘭所說:“生活中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
醫院下午五點半會準時關閉大門,家屬不能留宿。一些家屬租住在附近的酒店或民宿,因為惦記醫院的病人,睡不著時就圍著醫院散步,我有時也會加入這個隊伍。不過,晚上10點以后的北京似乎比白天要熱鬧些。東北母親就躺在醫院的房檐下,幾塊紅紅綠綠的塑料拼圖拼成了她的床。汽車的喇叭聲、行人的談論聲、附近小飯店飄來的飯菜香,都提不起她的興趣。她縮緊身體,來回翻身,被歲月抽打過的臉上內容豐富,憔悴、滄桑,心事重重。
她17歲的女兒因為心臟瓣膜手術在監護室已住了一個多月,為了省下給女兒治病的錢,這些天,她一直睡在醫院外面的大理石臺階上。17歲的花季卻開放在醫院,是在母親心里插了一根針。她隨身的布包里放著幾袋榨菜、幾根黃瓜和幾角大餅或燒餅,一個杯子時刻裝滿從醫院水房灌滿的水。早晨醫院開門,她第一個沖進去,在衛生間胡亂洗把臉漱漱口,便在等候區開始充滿希望的一天。
我想著這個東北母親回到酒店,開始坐在酒店的柜臺前跟服務員討價還價。把有窗戶的標間房換成無窗的大床房,把每天398元的費用降到298元。不再去酒店旁的飯店點自己喜歡的飯菜,買個小鍋,可以煮面、菜、餃子,煮任何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
我仍舊胡思亂想,想父親手術時的場景。想各種管子插滿父親的身體。猜測出現各種狀況時父親的樣子。想周一出院的那個老人,一見到兒子就抱住他嚎啕大哭,定是以為的生離死別被再次相見的驚喜替代。想那個東北母親,如果氣溫再低一些,她會在哪里的夜晚繼續等候她的女兒?她的女兒,會不會有一天突然出現在正吃著燒餅榨菜的母親面前,輕輕地說一聲“媽媽,咱們回家吧”。其實,我們一直在拒絕說拒絕聽拒絕想那個詞——死。這是個生活中必有又讓人恐怖的去處。我特意去書店找到《我與地壇》,并大膽地多看了幾眼“死”。沒錯,就是在這兒,北京,曾有一個與“死”打過很多年交道的史鐵生,他經常把“死”掛在嘴邊,他對死的親近勝過嫌惡,卻在有一天對他的長跑家朋友說:“先別去死,再試著活一活看。”史鐵生盡了最大的努力,活給自己看,活給母親看。我喜歡他把悲傷堆砌成山包,在山包的頂端讓希望拱出頭來,然后,一切都被笑容籠罩……
我知道我的父親也正在努力與命運抗爭。他有一群孝順的兒女,一群乖巧的孫子孫女,一個少有分歧的和睦幾十年的大家庭。愛,是這個大家庭親如一家的營養液,他舍不得丟下。死,是被這個家庭拋在荒郊野外的。
我去了史鐵生去過15年的地壇公園,因為我也有了他“做人質”的想法。此刻,我的生活里只有父親,我把信心抵押給“阜外”這座醫院,而這個秋天也作為人質抵押給了我和父親。
7
父親出院了。那天是我生日。
父親讓我用一天的時間去轉轉長安街和北京的胡同,給他拍些照片回來,他要和他去過的迪拜、香港、深圳、海南、杭州比較一下。他說幾十年前,他經常來北京出差,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車,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天安門和北京的胡同。我步行走過長安街,那天的雨單調、冗長,長安街一片金黃。我告訴父親我可以找到北京不同的秋天。北京的秋天老舍寫過,郁達夫也寫過。老舍的秋天用心在高攤與地攤的美食——在小白梨的“皮嫩水甜無蟲眼”,在“大酒缸”門外“蔥炒羊肉和木槌敲裂蟹腳”。對他來說,北平的秋天就是天堂,甚至“比天堂更繁華一點”。他的秋天里充滿年代感,是剛剛可以怯生生地把“繁華”貼到北平的臉上,是享受。這些對于現在的我們,早已是普通的家常便飯了。郁達夫不一樣,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不遠千里就是想“嘗一嘗”故都的秋。他帶著時間賦予的饑餓感,想嘗透北方秋的蕭索和悲涼,他心中有對比,與他南方家鄉的對比,與背井離鄉人眼中的欣喜對比。“正像是黃酒之與白干,稀飯之與饃饃,鱸魚之與大蟹,黃犬之與駱駝。”他說若能留得住故都的秋天“愿把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他對生命的大度無論如何我都做不到,我的父親已年過八旬,他和病痛斗智斗勇的日子,顯然也是絕不想舍掉他最多不過二十年的生命余額。我和家人提心吊膽地徘徊在大廳,等候在酒店,無非是想看到我的父親健康地走來,一家人圍坐一起,享受他該有的天倫之樂。我會在心里為這座醫院、為北京戴上一枚名副其實的勛章。
收拾東西時,我在車里發現了進京時交警開具的那張罰單,揉成一團準備和其他雜物一起扔掉,父親說留著吧,它也有救命之恩。打開,撫平那些褶皺,卻發現兩個字,那么醒目:警告!沒有扣分,也沒有罰款。眼淚瞬間滴落。這些天只顧忙著父親住院,手術一次次簽字,買東西,沒時間去看一眼這份違章通知單上的字。這些天,我為父親不知流過多少次眼淚,偷偷地,躲在酒店或某個角落,這一次,是為北京流下的,在父親面前。
史麗娜,河北省滄州市作協散文委員會主任。做過央企管理、編輯,作品發于《美文》《當代人》《散文百家》《大地文學》《深圳打工文學》等報刊。曾獲第四屆劉勰散文獎、河北散文名作獎等獎項,有作品入選“中考記敘文閱讀指導”,入選“2022年河北文學排行榜散文榜”。出版散文集《散步的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