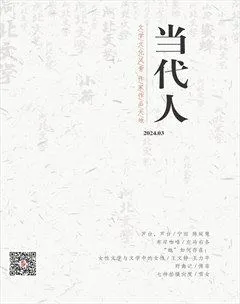書生的遠景
因為一座樓,我要談到兩個宋時的蜀人。
一座樓叫遠景樓,在四川眉山東坡湖畔。今天看到的遠景樓,高十三層,只為紀念兩個命名者:蘇軾和黎錞。命名者,在宋神宗熙寧年間,都離開故鄉蜀地,做了太守。
熙寧年間,蘇軾遠在數千里之外的密州和徐州任職。
黎錞老家在廣安軍(治所今四川省廣安市),離眉州兩百公里。兩百公里,狹隘一點,還是叫異鄉。
兩人都是一等一的讀書人,也是百姓心目中的賢明。蘇軾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與他的兄弟蘇轍同科高中,名震天下。黎錞,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進士,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知眉州,官至朝議大夫,是個經學家。
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
又說,天下好學之風在蜀更在眉州,好學之人在蜀亦更在眉州。
特別要提到眉州。眉州的水土和人文,相關互動——好學之人培好學之風,好學之風又風化山川名物:“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眉州遠景樓記》)
記文中所述遠景樓,巍然聳立在眉山三蘇祠東北五里地外,一到黃昏,金碧輝煌,老遠都能看到。相比“三蘇”故鄉首席物化遺產——三蘇祠,遠景樓是個相對獨立的個案。它的存在,只因如沐春風一般的自述在:
宋人最初收集東坡先生此文時,也收集了作文的時間——元豐元年(1078年)七月十五日,很明確。
多年后,我在關于先生書畫藝術的專題展覽中,看到了文章的墨稿,《眉山遠景樓記》書寫時間卻是“元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書寫地點也有的——喬居之雪寮。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的春天,蘇軾貶謫黃州已遇三春,先生的人生尚在涅槃,情緒似乎剛剛獲得緩解。那個春天,先生書寫了大名鼎鼎的《寒食帖》,也造了“雪堂”,開始了與友人的交往,也有時間思考更大的命題。這篇《眉山遠景樓記》,應是先生在書寫《寒食帖》后,第一篇純粹的書法作品。先生抄寫了此前在另一個異鄉——徐州任太守時的舊文。徐州的功課,應家鄉朋友的托付。現在重新抄寫,也許應某個朋友之邀,以換取資助的應酬,也許只為純粹打發閑暇。寒食之后,先生在他的新居,一座簡易的茅屋,見到了晚輩米芾、友人董鉞,以觀音紙作墨竹贈米芾,隱括五柳先生《歸去來辭》,并即興附和董鉞的《滿江紅》。《眉山遠景樓記》,跟那幾個作品都不一樣。至于它為哪位好友而作,不得而知。也許,它留給了自己。從筆意和章法來看,《眉山遠景樓記》比之《寒食帖》,徐緩而穩重,在“二王”和“顏體”之間,尋找了一個可以倚重的態度。而題款,更是滴水不漏,但沒有提到“雪堂”,只說了“雪寮”。“寮”收“堂”放,個中的些微區別,正好印證了書者情緒的些微變化——
自信已然拐彎,正在重新向上確立。
可以推斷,那個春天快要結束的時候,先生已經不再稱自己的茅廬為“寮”,而叫“堂”了。于是有了《雪堂記》和“東坡雪堂”的佳話。
黃州重書的《眉山遠景樓記》,與徐州初稿《眉州遠景樓記》,少了作文背景的交代:“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筑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記。”
這個黎侯,就是黎錞。
黎錞是“老蘇”蘇洵的好友,跟“大蘇”“小蘇”也有交集,是個做學問的老實人,有個外號“黎檬子”。檬子,就是蜀人說的懵子,憨人的意思,當然是個褒義詞。海南也有黎檬子,幾年前我在海南儋州的鄉場上,見過老百姓賣這玩意,有點像發育受限的小青橘,奇酸難忍,只能切片泡水喝。東坡貶謫海南后,也是見這貨,又想起了故人“黎檬子”:“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為‘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累累。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于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茍隨者也。”
這是東坡先生多年后的記述,個人情感的意味很重。而在遠景樓一記中,蘇軾對黎太守為文、為人、為事,專門有個客觀的簡評:“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茍,眾以為易事。”
看得出來,異鄉為官的黎太守是個做得多,說得少,干實事的執行型地方官員。明眼人會發現黎太守行事風格上似與東坡互補的。這樣想,就很有意思了,因為蘇東坡寫此詩的時候,也是太守,不過在遙遠的徐州。
蘇軾與黎錞最初的交集亮點,在我看來,或源于一首《寄黎眉州》。這是幾年前的事,東坡先生在密州任上。期間,黎錞來到眉州,做了先生家鄉的父母官。
好朋友赴任故鄉的時候,東坡驀然就想家了。他的鄉情,寄托在能托者身上:黎錞。先生試圖通過友人,寄托他于家山瓦屋和峨眉的特別情感:“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云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掃雨余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這是首鮮為人知的迎送詩,因為提到詩人的老師歐陽修,靈魂偶像陶淵明,提到他的故鄉,也是我的老家,如此又不是一首世俗意義的迎送詩。
感嘆六一居士,追隨五柳先生,要表達的深意,都是淺顯明白的。家山瓦屋、峨眉,為蜀中二絕。很多人不知道,也沒有去過。蘇軾不經意的一句“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掃雨余天”,一下讓天下人都知曉了兩山的美。這便是名人的光芒。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享受著先生帶給家鄉的紅利。
兩個蜀人,各赴一方。一個托付求命名文字,一個贈詩以表胸臆。如此互為寄托,是不是很有意思?
還有更具意思的。兩人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踏踏實實做民生,興文化,而且幾乎在同一年,都在當地造了一座地標,黎太守在眉州造了遠景樓,蘇太守在徐州造了黃樓。
很多朋友認為,可能造樓就是當時為官者的政績時髦,時間區間的重疊,僅僅湊巧而已。
有一個被大家忽視的時間節點,七月十五。這一天,蘇東坡寫就此文,他的黃樓要等到九月九日方才落成。也就是說,眉州的遠景樓,或于此前業已竣工。先生趕在他自己的黃樓落成前,急就此篇友情文字,這僅僅是時間的巧合,還是東坡特意的構思?
眉州本土的蘇學研究者認為,遠景樓奠基于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落成于元豐七年(1084年)。這個說法并不一定經得起推敲。元豐元年七月,遠在徐州的蘇軾已經在考慮為樓賦文了,剛剛經歷一個夏天到另一個夏天的抗洪和重建,有暇兌現鄉人的友情托請。從東坡的行文中,我們知道了其自熙寧十年(1077年)正月初一赴任徐州知州以來,與鄉人的書信互動頗為頻繁。這一年,是黎希聲在眉州第一個任期的最后一年。老百姓也是在這一年對黎太守的為官之道有了比較完整的感受。觀宋代士大夫的地方為官生態,要留下什么正面物證,比如造民生名勝之類,大抵會安排在任期的中后期。考慮到眉州老百姓向朝廷請命留任黎太守,此事落地之前,造樓工程或已完成:
“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
蘇東坡很可能是在這一年,徐州抗洪最緊張的時候,得到了鄉人關于父母官黎希聲的信息和請求,只是礙于民生公務纏身,沒有馬上啟筆。也大抵在年末歲初之交,得到了黎太守留任的確切信息,才得以放下公務,考慮還鄉人的請托,不然,以東坡的真誠為人,不會拖到朋友離任。再者,一座三層左右高度的磚木結構樓臺,工程若前后拖達七年,這個效率,老百姓滿意不滿意且不說,黎太守和蘇太守兩個首先就不會滿意。
黃樓于元豐元年(1078年)二月開工,八月十二竣工,三層高十丈。“黃”,取“土實勝水”(蘇轍《黃樓賦》)之意,從名字可看出,蘇東坡在他鄉徐州造樓的目的,也是寄寓民生意愿,抒發抗洪勝利喜悅。蘇轍在賦中,還有專門陳述。更有意思的是,九月九日落成典禮這天,蘇東坡在黃樓專門設“鹿鳴宴”,大賀剛剛通過秋試的舉子,并賦七律《鹿鳴宴》,作《徐州鹿鳴宴賦詩序》,大倡一鄉文風。而在此之前的七月十五,他剛剛為遠在故鄉眉州的高樓作記,又有著怎樣的深意?
我試著順著東坡的行文思緒,做流水的還原。
元豐元年(1078年)七月十五日,蘇軾表情嚴肅,寫下了《眉州遠景樓記》最開始的幾行文字。接下來的敘述,更接近于自言自語:
當初朝廷以聲律取士,各地的讀書人就此養成華而不實的陋習。唯有眉州的士子,仍以西漢文章為典范,被外地的讀書人視為泥古不化。官府的小辦事員,也讀經書,也習筆墨,他們所作公牘文字,竟然有古文遺風!大戶顯貴人家,以文章推重門第,甚至還不吝切磋,相互品評砥礪。老百姓與官府里人的關系,好比古時的君臣。官吏離任,還有人為他們畫肖像,甚至虔誠地供奉起來。出了成就的,也有人自發口碑相傳,一傳就是四五十年呵。有心的老百姓還把家里的好東西收起來,以滿足官府的需求。讀律令條文是經常的事情,誰說讀律令條文有什么不對呢?引以為戒。人一輩子哪能不犯一點小過,吃一塹,長一智,有些錯誤卻是怎么也不敢犯的。二月二,龍抬頭。莊稼人又開始新的忙碌了。四月初頭,野草和禾苗爭著躥長,幾乎家家的青壯勞力都上地薅草了。一個村莊都出動了,幾十上百人,也沒見有誰睡懶覺,打莊稼的迷糊眼。大家伙在田野中央放了個沙漏。有人看沙漏,掌握時辰。有人敲鼓,號令歇晌吃飯,出工收工。有誰要是想“哄”,鼓點沒響就收工,或是花著心思磨洋工,會遭致集體的鄙視和唾棄。俗話說,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按勞分配,秋后算賬。誰家田地多,勞力少,別人給你做了工,你就拿出銀子補償。到了七月,草也敗了,谷也熟了,鼓和漏也收回來了。買來豬羊酒醴,祭祀田祖,而后酒足飯飽,朝著秋冬睡去……
原諒我,費上這么多的筆墨去復述大師的敘述。它只是一種庸常瑣碎的痕跡,但痕跡與痕跡的疊加,一天天往下承傳,最后成為某種不可磨滅的記憶鏈條。它可能與蘇東坡的此篇樓記中,所描述的“俗”或“風”有關。
老實說,這不是一篇足夠“好”的客套的應酬文字。他的好友,眉州知州黎希聲,在眉山的民生城墻上豎了座樓,取名“遠景”。據說站在樓頂,能看到十里外的村莊和遠山。這是朋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得意之作,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的,眉州城固態的文化標識。
朋友是百姓心目中的好官——“能文守道不茍隨者”;朋友也是知根知底的好書生——“為人質木遲緩”。
為這樣的同僚說上些好話,也在情理之中。可蘇東坡沒有提及朋友的政績和政績工程,仍舊是一個人在那里自說自話,講述他對百姓生活魅力的理解——蘇東坡眼里的農耕文明時代,城市和鄉村的“遠景”。
蘇東坡眼里的“遠景”,與樓的實際高度和遠處物化的風景,并無多大關聯。他的遠,甚至是一種“近”,或者“向后轉”。普通的官吏和百姓——作為個體的“人”,他們也許只能看到“近”,眼巴下的“日子”更為要緊。世界很大,也很遙遠,遙不可及。而未來呢?未來是多久?是十年,還是五十年?人一輩子能有幾個十年,五十年?還是過好眼前的每一天吧。他不僅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即便是“昨天”“今天”和“明天”,也是“日子”的三個全新版本了。
做官的有做官的修為,管好任上,不昧良心。做吏的有做吏的做派,聽從差遣,甘為人下。做百姓的有做百姓的樣子,遵受律令,伺候田地。蘇軾所謂的“俗”或者“風”,會不會就是這樣一種最民間的生存狀態——日常的幸福?
只有回到眼下,我們才會感到想象中的“未來”,不再遙不可及。于是,蘇東坡在東坡開出荒來種豆,把銅錢一袋袋掛起來計劃著花。蘇老頭在掰著指頭過日子的同時,也享用著最世俗最民間最簡單最有人氣的幸福。在平靜中堅守平靜,在日常中翻新日常,在瑣碎中容忍瑣碎,在重復中習慣重復。我們在平靜、日常、瑣碎和重復中,為我們的“明天”或者“遠景”,日復一日地用力,再用力。
這么看來,我們是不是對蘇東坡造黃樓作遠景樓記,有了另外一層的認知?
它不是一篇世俗意義的應酬之作,而寄寓了超越個體人生風光,關乎百姓幸福愿景的政治理想。其個人的行高,更契合了公共的致遠。
于是,故鄉眉州遠景樓之名,仿佛不可或缺,且有了洞穿時空,點亮今天的意義。
(沈榮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作協全委會委員、散文專委會副主任,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
特約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