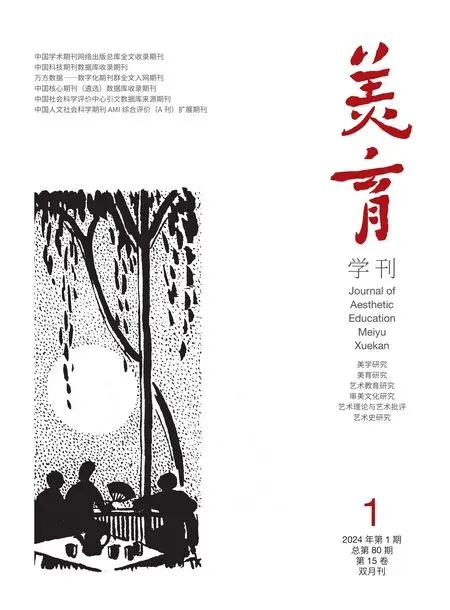區(qū)隔與重構(gòu):《貴州山民圖》中的民族邊緣意識
高尚學(xué),魏海心
(廣西藝術(shù)學(xué)院 人文學(xué)院,廣西 南寧 530022)
民族邊緣的形成,一方面基于不同族群之間語言、文化、地域分布等方面的差異,一方面來源于群體間主觀的認(rèn)同與排異。[1]4清末民初之際,面對帝國主義列強(qiáng)的侵略,全國上下都旨在將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之邦與處于邊緣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聯(lián)合,建立完整的國家邊界。[1]243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我國部分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和學(xué)校相繼向西南腹地轉(zhuǎn)移,促使西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受到了更多關(guān)注,相關(guān)研究機(jī)構(gòu)在此展開了眾多民族學(xué)調(diào)查。龐薰琹(1906—1985),著名畫家和工藝美術(shù)家,抗戰(zhàn)時(shí)期隨北平藝專遷至湖南沅陵,后又去往昆明。在昆明期間,他結(jié)識了聞一多、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他們的影響下轉(zhuǎn)向了對中國傳統(tǒng)圖案的研究。1939年,龐薰琹至國立中央博物院工作,負(fù)責(zé)整理研究中國傳統(tǒng)器物紋樣,后與民族語言學(xué)家芮逸夫赴貴州考察當(dāng)?shù)厣贁?shù)民族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了民族題材作品——《貴州山民圖》組畫。《貴州山民圖》再現(xiàn)了貴州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將民族裝飾紋樣融入繪畫之中,具有歷史性和藝術(shù)性的雙重價(jià)值。此系列作品反映了漢族與苗族之間的文化碰撞,勾勒出了由客觀文化差異所形成的傳統(tǒng)定義下的民族界限,又因繪畫所具有的主觀性特征,《貴州山民圖》隱含著漢族與苗族不同生態(tài)位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潛藏著現(xiàn)代民族邊緣意識,從中可以管窺民國時(shí)期民族邊緣的重構(gòu)蹤跡。
一、民族邊緣觀念與《貴州山民圖》
傳統(tǒng)民族學(xué)觀念將不同的族群看作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區(qū)塊,各個(gè)族群間以語言、服飾、習(xí)俗等顯性文化特征作為基本的區(qū)分依據(jù),呈現(xiàn)出一元性的區(qū)域劃分標(biāo)準(zhǔn)。每個(gè)族群皆獨(dú)有某種代表性文化,由此所形成的族群邊界亦是相對明晰穩(wěn)定的。自西方開啟工業(yè)文明時(shí)代以來,民族學(xué)研究出現(xiàn)了所謂的“邊緣中心理論”,即將民族調(diào)查的中心從各個(gè)族群的文化特征轉(zhuǎn)移至族群間的社會邊緣。挪威民族學(xué)者弗雷德里克·巴斯認(rèn)為族群的區(qū)分必須經(jīng)過排斥與包容的社會化過程,社會組織意義下的族群邊界來自“一人以互動(dòng)為目的,使用族群身份區(qū)別于他人”的這一情境中。[2]因此,近代民族學(xué)背景下的民族邊緣觀念形成于各族群間的主觀互動(dòng),包括強(qiáng)化集體記憶、選擇性遺忘、折損他人等,且互動(dòng)峰值存在于族群邊界的接觸地帶,并且此處尤為可能出現(xiàn)民族邊緣的變動(dòng)。因此,此種觀念下的民族邊緣不再是地理意義的存在,其形態(tài)較為多變、含混,歷史上曾多次出現(xiàn)較大規(guī)模的邊緣變遷,深刻影響著各族群間的地位關(guān)系。
基于上述觀點(diǎn),《貴州山民圖》與民族邊緣觀念之間的關(guān)系成為需要思考的問題,二者作為不同領(lǐng)域的客體有著怎樣的聯(lián)系?是否可以用民族邊緣觀念重新解讀《貴州山民圖》?從總體時(shí)代背景來看,《貴州山民圖》的創(chuàng)作時(shí)代處于民國時(shí)期,此時(shí)期的進(jìn)步民族學(xué)者深受西方近代民族學(xué)說的影響,皆以科學(xué)、多元的方法展開本土民族的研究。李濟(jì)曾提出:“我們出發(fā)點(diǎn),應(yīng)該是以人類全部文化為目標(biāo)。連我們自己的包括在內(nèi),我們尤其不應(yīng)該把我們自己的文化放在任何固定的位置。……我們具體的計(jì)劃,就是先從自己的文化以民族學(xué)的方法研究起。”[3]也是在此種背景下,相關(guān)研究機(jī)構(gòu)展開了眾多邊疆少數(shù)民族調(diào)查,旨在聯(lián)合“四裔蠻夷”,消解漢民族與少數(shù)民族間的邊緣分隔,構(gòu)成完整的國族體系。[1]245而《貴州山民圖》是以龐薰琹、芮逸夫的貴州苗族考察為背景創(chuàng)作的,畫面中的人物、情景、衣飾等都以紀(jì)實(shí)照片和考察成果為范本,是民族學(xué)考察成果的藝術(shù)呈現(xiàn)。繪畫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藝術(shù)形式,更具情感價(jià)值和表意功能。《貴州山民圖》既反映了苗族的生活狀態(tài),又拉近了漢苗之間的情感距離,向居于主體地位的漢族群體展示了西南苗族的真實(shí)面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對苗族的既有印象,促進(jìn)了漢苗間的社會性互動(dòng)。從微觀角度而言,《貴州山民圖》的作者龐薰琹與畫面中的苗族表現(xiàn)對象構(gòu)成了漢苗兩族邊緣變遷的微焦空間。根據(jù)王明軻的觀點(diǎn),民族邊界的形成一是源于我者對他者的異己感,一是基于族群成員的根基性情感。[1]4龐薰琹在民族考察過程中參與了當(dāng)?shù)厝说幕槎Y、喪葬、樂舞歡慶,從異己者轉(zhuǎn)為了同胞親友。就此而言,龐薰琴作為一個(gè)漢族個(gè)體融入了苗族之中,在此后繪制《貴州山民圖》時(shí),亦是將苗族特有的衣飾、風(fēng)情融入了中國傳統(tǒng)繪畫風(fēng)格之中,構(gòu)成了漢苗間互動(dòng)過程的一個(gè)縮影,彌合了二者的邊緣區(qū)隔,與民國時(shí)期整體國族觀念的建立具有一致性。基于以上所述,《貴州山民圖》所傳達(dá)出的深層意義契合于近代民族邊緣觀念,解讀《貴州山民圖》所蘊(yùn)含的民族邊緣意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貴州山民圖》中的“自我”與“他者”
中國古代的統(tǒng)治者歷來將滿、蒙、藏等視為歷史綿長的少數(shù)民族,對其有明確的地域界定,但并未明確西南少數(shù)民族群體,僅以“苗”“蠻”“夷”等稱謂模糊地描述與區(qū)分該地域人群。[1]250-251直至近代,民國政府所建立的“族群”概念依舊未能明確劃分西南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邊緣。因此,為了深入探究西南地區(qū)的地理文化特征,中國近代民族學(xué)研究大多集中于此地。[1]251其中包括1933年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等人于鳳凰、永綏等地的湘西苗族考察,1934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在云南的民族學(xué)研究,1939年至1940年芮逸夫、龐薰琹在貴州的苗族考察,1942年至1943年芮逸夫、胡慶鈞的川西民族調(diào)查等。
此外,在中國傳統(tǒng)的地域觀念中,西南地區(qū)常被稱為“蠻夷之地”。盡管自明清起,統(tǒng)治者開始重新審視西南地區(qū)的歷史文化,但依舊無法擺脫“自我”對“他者”的偏見。直至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中國西南部的地域優(yōu)勢才得以凸顯,民國政府及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也逐步重視起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派遣眾多民族學(xué)者對其考察研究,獲取資料。[4]雖然中國近代民族學(xué)者大多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抱有尊重平等的態(tài)度,但在潛意識中依舊存在著“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文化區(qū)隔。黃文山在《民族學(xué)與中國民族研究》中寫道:
中國民族之“我群”即為漢族,此為最初組織中國國家之民族,其文化地理,自成一個(gè)單位,一派相承,至今不替。“他群”則為邊疆及內(nèi)地之淺化民族,其語言,習(xí)尚,乃至一切文化,尚須經(jīng)若干年之涵化作用,始能與“我群”成為一體者。[5]12-13
據(jù)此可知,漢族與邊疆民族長久以來的征伐割據(jù)逐漸深化了二者間的地位差距,漢民族本位觀念深諳人心,影響著民族邊緣的構(gòu)建。近代民族學(xué)者雖深受西方科學(xué)理論的影響,但仍無法擺脫以漢人視角審視少數(shù)民族的觀念。他們在民族考察時(shí)最為關(guān)注的是少數(shù)民族與自身相異的文化特征,無意間強(qiáng)化了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間先進(jìn)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對立差別。
龐薰琹的貴州苗族考察工作以及所繪的《貴州山民圖》亦顯示出了“他者”的優(yōu)越性。龐薰琹在貴州苗族村落尋訪調(diào)查時(shí),以收集當(dāng)?shù)孛褡逡嘛椈ㄟ厼榉绞?匯集整理了大量苗族工藝美術(shù)成果。[6]雖然這些資料現(xiàn)已佚失,但此后所繪制的《貴州山民圖》組畫較為真實(shí)地還原了苗族的衣飾花紋,并將這些花紋視為獨(dú)立于其他畫面要素的裝飾版塊。有關(guān)文獻(xiàn)曾提到,《貴州山民圖》中的部分苗民形象是以芮逸夫的攝影作品為藍(lán)本的,龐薰琹幾乎完全依照攝影圖片等考察記錄,精細(xì)再現(xiàn)了苗族女子的動(dòng)作形象以及衣飾花紋。[7]龐氏曾說他筆下的貴州苗民因是藝術(shù)形象,并不能以民族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但是在描繪他們的服飾時(shí),卻盡力還原其本來的面目,像女子繡花一般,按照原樣“復(fù)制”到了畫面上[8]。因此,《貴州山民圖》并不是民族志式的少數(shù)民族圖記,它具備繪畫的想象性和主觀性。但與一般繪畫不同的是,《貴州山民圖》中的苗民服飾花紋不是憑畫家主觀印象草草繪制而成,僅僅用以豐富畫面,而是升華為了貴州苗族的“身份卡”,引導(dǎo)觀者識別其獨(dú)有的屬性與特點(diǎn)。從這一角度出發(fā),《貴州山民圖》通過直觀還原苗族在服飾等方面異于漢民族的某些特征,突出強(qiáng)調(diào)了苗族相對于漢族的“異質(zhì)性”。這種傾向根植于長久以來漢人對苗族等邊疆民族所具有的獵奇心理與征服欲望,最終的目的都指向強(qiáng)化漢族內(nèi)部共識。相關(guān)研究表明,歷史上各朝各代對漢民族邊緣的鞏固,除了最為直接的武力征戰(zhàn)、通婚、貿(mào)易往來等方式,還會通過紀(jì)念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銘記歷史中的抗夷戰(zhàn)爭,以及認(rèn)識了解邊緣民族的奇風(fēng)異俗等方式,來加深華夏民族的歷史記憶,從而凝聚起漢族內(nèi)部的民族共識。[1]243因此,《貴州山民圖》所表現(xiàn)的苗族裝飾元素除了具備藝術(shù)功能之外,還反映了龐薰琹的傳統(tǒng)民族觀念,其貴州民族學(xué)考察以及《貴州山民圖》的創(chuàng)作可視為漢苗間的個(gè)體互動(dòng)案例。
綜上可知,《貴州山民圖》中的裝飾元素因真實(shí)再現(xiàn)了苗族衣飾花紋,成為苗族的表征符號,從而具備了民族學(xué)意義,并側(cè)面揭示了作為漢人的龐薰琹或仍在潛意識中存有對邊緣少數(shù)民族的主體凝視,將貴州苗族視為異于自身的“他者”,獨(dú)立區(qū)分了苗族的顯性特征。龐薰琹認(rèn)為社會與生產(chǎn)的發(fā)展推動(dòng)著圖案形式的變革,而這些圖案形式不僅是民族狀貌的象征,還是民族特性的反映。[9]據(jù)此,他將苗族的民族特性移植到畫面中,展現(xiàn)了苗民獨(dú)有的民族烙印。此種強(qiáng)調(diào)苗族服飾裝束、生活習(xí)俗等方面的特異性之行為,于無意間深化了漢族與西南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民族邊緣,進(jìn)一步固化了二者生態(tài)地位的強(qiáng)弱差別。
三、《貴州山民圖》對漢苗民族邊緣的融合作用
清末民初,西方列強(qiáng)在中國及周邊地區(qū)施以擴(kuò)張戰(zhàn)略,使我國民族危機(jī)不斷深化,中國近代的有識之士力圖建立以漢族為中心,以滿、蒙、藏、苗等為邊緣的整體國族觀念,抵御外侵。日本侵華后,中國多地相繼淪陷,位于中國內(nèi)陸的西南地區(qū)成為抗戰(zhàn)的大后方,在抗擊侵略、保衛(wèi)人民等方面貢獻(xiàn)了巨大的力量。基于此,民國政府在民族學(xué)調(diào)查之余,也采取了相關(guān)措施用以籠絡(luò)邊疆民族,從而凝聚中國各民族同胞,共同抵御外敵入侵。其中最主要的途徑之一便是推動(dòng)少數(shù)民族漢化,有資料記載相關(guān)政策:
查西南苗夷雜處,種族分類,號稱一百種左右,語言、生活、服裝、習(xí)尚皆堪自為風(fēng)氣,既無國家民族之觀念,適足啟鄰邦覬覦之野心。滇黔邊之苗胞,滇省南之夷族,廣西之瑤人,川邊之藏番,廣土眾民,監(jiān)教莫及,興學(xué)傳教,人為我謀。東北之淪亡,蒙古之獨(dú)立,寧夏之回亂,西藏之反側(cè),如履霜堅(jiān)冰,誰為厲階?亡羊補(bǔ)牢,道在同化……凡此設(shè)施,皆本救國保民之大職,設(shè)政府懷柔之補(bǔ)苴,款款之余,伏乞鑒察,并飭轉(zhuǎn)令滇黔川桂各部,對于同化苗夷工作,咸皆注意。倘能共體斯旨,則三數(shù)年后,不難完成民族統(tǒng)一。[10]
另有文稱:
要使各區(qū)之淺化民族,與比較先進(jìn)之漢族,如速同化,所謂同化者,即以各族文化為基礎(chǔ),使之吸收漢化及西化,與漢族并進(jìn),如此則整個(gè)中華民族,可以于最短期間,孕育更善更美之新型文化。[5]22
在此背景下,國立中央博物院開展了眾多少數(shù)民族調(diào)查工作,在充分考察當(dāng)?shù)氐拿褡迤鹪础⑽幕L(fēng)俗之外,還致力于推進(jìn)少數(shù)民族與漢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在考察過程中,民族學(xué)者與當(dāng)?shù)鼐用窠⑵鹆松矸荨⒂^念等方面交匯的橋梁,推動(dòng)了民族邊緣的融合與重構(gòu),順應(yīng)了民國整體國族觀念的內(nèi)在要求。1939年末,中央博物院派遣龐薰琹、芮逸夫至貴州苗族村落進(jìn)行了數(shù)月的實(shí)地考察,所獲成果頗豐。中央博物院相關(guān)資料記載:
貴州是夷苗聚居的地方,有仲家、花苗、青苗各種不同的種類。風(fēng)俗習(xí)慣,和漢人大不相同,夷苗的服裝修飾編織物等,尤其是個(gè)有興趣的問題。本處達(dá)滇以后,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在二十八年十二月,派遣龐薰琹、芮逸夫二人往貴州,調(diào)查貴陽安順龍里貴定四縣的夷苗村寨六十余處,收集樣本,并選擇服飾紋樣制成圖片。[11]
本次民族學(xué)考察后,龐薰琹以貴州苗族人民生活為題材,創(chuàng)作了裝飾性民族繪畫作品——《貴州山民圖》系列組畫。這系列作品或?qū)⑷宋锶合裰糜诤泼焐剿?表現(xiàn)苗民的習(xí)俗活動(dòng),或細(xì)致刻畫苗族女子的衣飾花紋,展現(xiàn)其民族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龐薰琹采用了毛筆、絹紙和水彩作為主要繪畫工具,使畫面效果與中國傳統(tǒng)水墨畫十分相近。例如《黃果樹瀑布》一圖表現(xiàn)了山崖處一女子眺望遠(yuǎn)方的場景,與馬遠(yuǎn)的《樓臺春望圖》有著相似的取材和畫面意味。前景處挑著果籃的婦女以背影示人,遙望瀑布山川;中遠(yuǎn)景山川由實(shí)到虛、由深入淺,極具層次感;大面積留白既凸顯了人物形象,又生出無限的意境,表現(xiàn)出貴州山水的幽遠(yuǎn)開闊,深具中國傳統(tǒng)水墨畫的韻味。《貴州山民圖》系列作品皆以毛筆勾線后再賦色,線條婉轉(zhuǎn)流暢,繼承了中國古代繪畫的美學(xué)特征。龐薰琹認(rèn)為線描是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精髓所在,其歷史悠久、源遠(yuǎn)流長,承載了形與意、虛與實(shí)、動(dòng)與靜、剛與柔的多重變化,并認(rèn)為謝赫“氣韻生動(dòng)”的美學(xué)命題可充分詮釋中國傳統(tǒng)線描的表現(xiàn)技法與意趣。[12]此外,龐薰琹早年雖留學(xué)西洋,但他繼承并發(fā)揚(yáng)了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思想,將畫面有無氣韻視為評判作品優(yōu)劣的標(biāo)準(zhǔn),在他看來,藝術(shù)家應(yīng)以“氣”作為情感表達(dá)的出口,立象以盡意。[13]因此,龐薰琹在創(chuàng)作《貴州山民圖》時(shí)即以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思想為依據(jù),將中國水墨畫的繪畫方式及情感內(nèi)涵,用于表現(xiàn)西南苗族人民,既呈現(xiàn)出帶有文人意味的苗族形象,又開辟了傳統(tǒng)人物畫的民族新形式,連通了漢族與苗族各自的民族性格。其中,《垂釣》《賣柴》《跳花》等作品墨色樸實(shí)淡雅,虛實(shí)相生,為貴州苗族的異域風(fēng)情增添了“象外之象”“景中有情”的畫面意味,使苗民形象帶有了漢化特征。相關(guān)文章曾如此評價(jià)《貴州山民圖》:“各幅于線條,構(gòu)圖,顏色三項(xiàng),均卓然成家;而人物之靜美尤能表現(xiàn)東方藝畫之矜持。”[14]總之,龐薰琹以繪畫的形式將漢苗兩族的文化特征融為一體,視覺顯化了苗族漢化這一民族變遷的隱匿蹤跡,《貴州山民圖》亦成為民族邊緣融合過程的繪畫體現(xiàn)。
至此,綜合前文可以看出,龐薰琹對苗族群體的表現(xiàn)具有一定的矛盾性。這種矛盾的成因,一方面在于《貴州山民圖》將苗族的衣飾紋樣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表現(xiàn)對象,突出了苗族的奇風(fēng)異俗,在無形中強(qiáng)調(diào)了漢民族本位觀念,起到了凝聚漢族內(nèi)部共識的作用,從而深化了漢苗兩族的邊緣區(qū)隔;另一方面在于他以中國傳統(tǒng)水墨技法入畫,將苗族的異域風(fēng)情與文人藝術(shù)的淡泊清遠(yuǎn)相結(jié)合,貫通了漢苗兩族的文化藝術(shù)形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漢苗民族邊緣融合的互動(dòng)過程。因此,龐薰琹的《貴州山民圖》對民族邊緣進(jìn)行了區(qū)隔與融合的雙重構(gòu)建,將民族視角與藝術(shù)視角相交匯,在矛盾中分別體現(xiàn)了民國時(shí)期民族學(xué)研究的有限性和多面性。
四、《貴州山民圖》獨(dú)特的民族學(xué)意義
晚清民國時(shí)期,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推動(dòng)了民族學(xué)調(diào)研的蓬勃發(fā)展,新國族觀念也在此時(shí)期得以建立。相關(guān)民族學(xué)者研究梳理了邊緣少數(shù)民族的起源、變遷、語言、文化等問題,構(gòu)筑起我國早期民族學(xué)發(fā)展路徑。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民族學(xué)研究尋找到了更為有效的發(fā)展跳板,也更具現(xiàn)實(shí)意義。抗戰(zhàn)主線與民族研究支線相互交織,共同作用于我國民族邊緣的重構(gòu)。這一時(shí)期的研究成果雖填補(bǔ)了中國近代民族研究領(lǐng)域的空白,但曲高和寡,此般專業(yè)性成果往往主要被研究學(xué)者所接納和吸收,普羅大眾作為民族的構(gòu)成主體,或許無法從中直觀感受到少數(shù)民族的風(fēng)土樣貌。而以《貴州山民圖》為代表的民族主題繪畫打破了這層壁壘,將少數(shù)民族形象赫然呈現(xiàn)在人們眼前,一篇名為《讀龐薰琹的畫》的文章曾如此評價(jià)此作品: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中國讀書人的一句老話,但這句話也適應(yīng)于現(xiàn)代的藝術(shù)家畫家,一個(gè)寫實(shí)的畫家,卻非身歷多方現(xiàn)實(shí)不可。龐薰琹首先就把這一步做到了。走遍湘、黔、川、滇諸省,和中國邊疆區(qū)域苗、夷、傜等民族有過接觸,于是便采集了這些做了最好的素材,我們住在內(nèi)地和沿海一帶的人,對那邊是非常隔離的,但是假藝術(shù)家之手,就輕輕的把二者拉攏了。[15]
同時(shí),中國近代時(shí)期的諸多民族學(xué)考察大致相似,但龐薰琹所參與的貴州苗族考察卻是一個(gè)特殊的存在,因?yàn)樽鳛橹饕蓡T的龐氏并不具備民族學(xué)家、人類學(xué)家、語言學(xué)家等專業(yè)身份,而全然是一位藝術(shù)家。因此,他的存在為貴州民族學(xué)研究規(guī)劃了新的方向,使研究的目光更多投向了少數(shù)民族民間藝術(shù)領(lǐng)域,打破了民國民族學(xué)研究的局限性。在他的參與下,貴州考察團(tuán)收集整理了許多珍貴的苗族民間圖樣,使民國時(shí)期的少數(shù)民族研究成果臻于完善。
與國立中央博物院同為歷史研究機(jī)構(gòu)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以歷史、語言、考古與民族學(xué)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亦開展了眾多民族考察。其所長傅斯年曾在研究所工作旨趣中要求:“凡一種學(xué)問能擴(kuò)充他作研究時(shí)應(yīng)用的工具的,則進(jìn)步,不能的,退步。實(shí)驗(yàn)學(xué)家之相競?cè)缍穼氁话?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xué)和歷史學(xué)亦復(fù)如此。”[16]不僅是語言學(xué)和歷史學(xué),與此相關(guān)的民族學(xué)亦然。作為畫家及工藝美術(shù)家的龐薰琹便為民族學(xué)調(diào)查提供了與藝術(shù)有關(guān)的新方法,即以工藝美術(shù)的規(guī)律研究苗族的服飾紋樣,以窺探中國遠(yuǎn)古的文化風(fēng)貌,并將《貴州山民圖》作為民族民間藝術(shù)的變體形式,使觀看者,尤其是距漢苗邊緣較遠(yuǎn)的觀者群體更易接受。
除此之外,《貴州山民圖》中的民族意識也輻射至此時(shí)期龐薰琹的整體創(chuàng)作過程。龐薰琹曾于1946年11月8日在震旦大學(xué)禮堂舉辦個(gè)人畫展,除了展出《貴州山民圖》組畫之外,還展出了線描形式的“唐人帶舞”。這些線描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shí)間略晚于《貴州山民圖》,因其與敦煌壁畫的飄逸飛揚(yáng)有幾分相像,所以相較于《貴州山民圖》更具民族特色。這兩部系列作品一個(gè)以苗族山民為表現(xiàn)對象,一個(gè)以唐衣舞女為主體,分別彰顯了苗、漢獨(dú)有的文化氣息,二者雖內(nèi)容各異,但都統(tǒng)攝于中國傳統(tǒng)筆墨之法,亦古亦今,亦漢亦苗,將中國筆墨之古意與邊疆民族之靈動(dòng)巧妙融合。
在中國近代整體民族觀念以及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下,龐薰琹在20世紀(jì)40年代前后所創(chuàng)作的繪畫作品多為少數(shù)民族題材,并采用中國傳統(tǒng)繪畫技法,實(shí)現(xiàn)了不同民族間風(fēng)格的交匯融合。其中,《貴州山民圖》作為這一時(shí)期龐薰琹的代表作品,上承他對中國傳統(tǒng)裝飾圖樣的研究,下啟中國少數(shù)民族繪畫的新樣式,是龐氏繪畫生涯的重要轉(zhuǎn)折點(diǎn)。此系列作品誕生于龐薰琹的貴州苗族考察之后,其對于民族邊緣的雙重作用與近代民族觀念的發(fā)展有密切關(guān)系,是民國時(shí)期民族研究發(fā)展歷程的縮影。蘇利文曾說《貴州山民圖》系列作品標(biāo)志著龐薰琹邁入了其繪畫生涯的“灰色時(shí)期”。[17]此“灰色”意指此時(shí)龐氏的畫面的多為藍(lán)灰色調(diào),但對于其整體繪畫生涯而言,《貴州山民圖》連接了漢苗兩族的文化觀念,其內(nèi)核應(yīng)是獨(dú)特鮮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