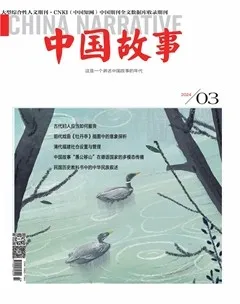論劉亮程散文的文化尋根指向及現代性反思
劉靈巧
【導讀】從《一個人的村莊》到《在新疆》,劉亮程散文記述了新疆鄉村人事與物態風俗的變遷,指出人類不當行為和索取的貪欲造成了鄉村生態惡化與環境破壞,順應了反思現代性的社會思潮。劉亮程以書寫家鄉黃沙梁的方式,對童年經驗進行再挖掘,以此重新領受家鄉曾給予他的民間鄉村之美和被現代性的城市生活湮沒的存在感,尋找自己的精神根基;他對南疆村落的歷史、文化、生態及民情民俗的深刻體驗,反映了他對新疆鄉土的熱愛,對南疆民間“閑懶”生存態度的高度認同以及對現代性弊病的反思。作者呼喚文明的多樣化,希望保留古老的鄉村文化,為現代化社會提供一個精神家園,對城市文明的弊病予以糾偏。
劉亮程,新疆著名散文家,因《一個人的村莊》而成名,之后的十年他游走于南疆和阿勒泰地區,寫成了《在新疆》。從《一個人的村莊》到《在新疆》,劉亮程的地方視野與文學視野進一步拓展,從一個人的黃沙梁延伸至整個新疆。劉亮程直言,“新疆給了他一個站在新疆看全國的視角,是站在西北角上看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本文從文化尋根的角度梳理劉亮程散文中蘊含的現代性反思。他在鄉村必然現代化的境遇下捍衛鄉村文明與新疆古老生活方式的獨特價值,以期待糾正城市文明的弊病,保留一處精神家園。
一、“回望”與“游走”:劉亮程的文化尋根之旅
劉亮程散文集的創作速度是緩慢的。《一個人的村莊》與《在新疆》幾乎都寫作了十年。劉亮程認為,“一部書有自己的生長年輪,少一輪都長不成。”如果說《一個人的村莊》是劉亮程對童年與青年時期家鄉的找尋與回望,那么《在新疆》則是劉亮程以游客和異鄉人的身份對南疆和阿勒泰的歷史、文化、民俗、民情進行的觀察與體驗。想要進入地方內部卻始終隔膜的心理感受,讓劉亮程的寫作呈現出游走的姿態。
(一)回望:以鄉村文明的“慢”抵御現代文明的“快”
劉亮程通過《一個人的村莊》塑造了一個精神故鄉“黃沙梁”,實現了向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模式與文化的回歸。從家鄉到故鄉,需要一個認領的過程。劉亮程認為,家鄉早在我們出生那一刻便把世界的一切都給予了我們,而我們需要用一生的時間把自己還給家鄉。當人長大后,都要重新去領會家鄉的一切,讓家鄉在這個過程中成為故鄉。因此劉亮程筆下的“黃沙梁”不僅是現實層面上的村莊場域,更是心靈層面上的精神故鄉。
黃沙梁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村莊。通過人、牲畜、草木、作物的生死,劉亮程刻畫了黃沙梁時間的單調重復、周而復始,它的節奏是緩慢、凝滯的。劉亮程通過描繪黃沙梁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模式,將其與中國千年的農耕文明傳統聯通,由此黃沙梁時間具有了歷史的綿長與厚重。與中國悠久的農耕文明相比,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還不到兩百年。劉亮程在反思現代性時,就不禁向農耕文明靠攏,在其中尋找答案。
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中塑造了一個反功利性、反目的性、慢節奏生活的閑人,以反叛的姿態質疑現代性的弊端。閑人在合乎自然的慢節律中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居,在自家日升日落的院子里找到了生命的存在感。他打斷了村民快速向前的生活節奏,感官得到充分伸展去感受村莊的生活細節,因此閑人成為黃沙梁一群忙人中的唯一的異類,他不僅是唯一慢下來想事情的人,也是唯一把自然本身看作比勞作更重要的人。他“常常扛一把鐵锨,像個無事的人,在村外的野地上閑轉”,是一個毫無目的的人。他每天操心的事情就是迎接日出和日落,這一儀式在他看來是天下最重要的事,一個卑微的生命由此獲得了生命的尊嚴與自由。
但是他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一步步把家搬進了縣城,當他離去二十年再次歸來,黃沙梁已經破敗不堪。一些村民為了尋求機會與財富,逐漸遺棄黃沙梁,去縣城打拼,而留下的村民則為發展經濟盲目開墾荒地,把草木茂盛的活地折騰成了寸草不生的死地,導致了嚴重的生態破壞,村莊被荒棄的土地也越來越多。
(二)游走:以閑懶的生存態度抵擋盲目的經濟開發
以慢節奏的人畜共居的鄉村生活來抵抗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產生的茫然與困惑,只能起到有限的撫慰。在這之后,劉亮程走出了個人記憶中的黃沙梁,游走于廣闊的南疆與阿勒泰地區,他從南疆農民閑懶的生存態度中悟出,懶也可以成為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自我和諧關系的一種方式。面對盲目的經濟開發,閑懶的生存態度反而使得鄉村世界的社會結構、人倫關系、象征符號以及風俗傳統得以保留,南疆農民自在地生活在古老的鄉村生活里。
劉亮程在《拾的吃》里延伸了他關于“閑人”和“忙人”的關系論說,進一步深化對現代性的反思。他發現村落里總有一些好吃懶做的人,但他并不批評他們,而是認為“一個小地方的活是有限的”,他們完全可以不做什么,單純地度過一種閑懶生活。相反,忙人已把世界折騰得不成樣子,甚至把窮人賴以生存的土地都倒騰壞了。劉亮程質疑懶是造成個人貧窮的原因。懶人把有限的就業機會讓給了忙人,因此才閑下來,成為別人眼中好吃懶做的人,而忙人非但不感激懶人,還以發展經濟的名義反復折騰土地。結果土地倒騰壞了,倒霉的是農民,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劉亮程意識到,在鄉村現代化的過程中,土生土長的農民并非受益的一方。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于土地,很少能參與進現代工程中來,但一旦土地被倒騰壞,他們又是最大的受害者。相較之下獲益最大的則是倒騰土地的忙人,他們以消耗當地的資源與能源為代價進行現代經濟開發,變得越來越富有,最終反過來侵占了窮人的生存空間。“這座城市不久前,還是他們的莊稼地和果園,后來就變成富人的天堂了”。除此之外,因為過度墾荒,導致植被大面積被毀;因為過度開采地下水,導致古爾班通古特的地下水位每年急速下降,并在不久的時間內衰竭。劉亮程引導我們反思城市文明的發展方式。以前人畜共居、美美與共的村莊田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貧困的村落和傷痕累累的沙漠,是什么導致了這一切?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的快速發展與資源、能源消耗是成正比的,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方式終將讓農民受害,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二、現代性批判:文化尋根的背景
現代性是說明現代社會和文化特征的術語。吉登斯指出,“現代性是指大約從十七世紀的歐洲起源的一種社會生活和組織的模式,之后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全球。”歐洲國家是最早一批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通過高度工業化推動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實力。但此種發展方式是以資源、能源的大量消耗為代價的,其弊端在兩百年后以生態危機、資源危機和疾病叢生的形式顯現。此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于拓展市場和積累資本的需要,通過全球的擴張與殖民活動,將現代性的理念傳播并植入到其他國家。
目前,現代性已經成為全球的現象。許多后發展國家為謀求自身的發展與話語權,也積極參與到現代化的建設當中。在反思西方現代化發展方式的基礎上,其他國家也在探尋實現現代化的多元路徑。正如王寧所說,“現代性既是一種單數的宏大的總體性敘事,同時又是一個有著多種形式的復數的變體的現代性”。現代性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讓人們意識到現代性的弊病。葉舒憲認為,“正是在這種涉及生存和毀滅的危機征兆中,文化尋根成為20世紀后期最具普遍性、世界性的文化運動。”
三、現代性反思:庫車老城民間文化書寫
“文化尋根的實質是對自18世紀以來的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原來被壓抑的‘文化他者(如被視為‘異文化的東方文化、作為人類征服的索取對象的大自然等)成為文化反思與再認同的鏡子。”葉舒憲認為,文化尋根的意義在于重新恢復人類的敬畏之心,覺察自身所作所為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不利影響,重新體認大自然的神圣本性,調整自身的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使之適應在地球上生活的需要。
劉亮程對大自然充滿敬畏之心。在《喀納斯靈》中,任何事物都是有靈的,能通過風傳遞。劉亮程相信人、動物、植物皆有靈,應當取消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將人與自然看成一個不可分割、彼此融合的整體。如果人心對自然毫無敬畏,便會對萬物隔膜,將自然異化成一架冷冰冰的工業機器。倘若人拋棄自私之心,敬畏萬物的生命,給靈騰出地方,靈才會居住進來。
劉亮程關注那些已經或正被湮沒的民間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老城里日益稀少的驢車、庫車老城吐迪家世代相傳的打鐵技藝、維吾爾族的割禮習俗、老少都玩的托包克游戲、庫車不斷挖出的龜茲古幣、面臨失傳危機的木卡姆藝術等。劉亮程在《在新疆》中充分表達了對新疆的熱愛和對龜茲古城民俗文化和新疆村民古老的生活方式的高度認同。
《龜茲驢志》中,他寫了毛驢在龜茲(即今日庫車)的千年歷史。曾有好幾種動物與其爭寵,可只有毛驢在這里站穩腳跟。毛驢矮小,能適應南疆干旱炎熱的氣候,能適應庫車田野的粗雜草料。毛驢在庫車不僅是世代相傳的牲畜,更是維吾爾族村民們的親密的朋友與伙伴,是貧苦村民最適宜飼養的家畜。平日里,村民還會給自己的毛驢打驢掌,做驢擁子。毛驢的生命在村民那里得到了尊重,毛驢也陪伴村民勞動直到老死。現在的庫車已是全疆有名的毛驢大縣,每逢巴扎日,庫車就是驢的世界:“庫車看上去就像一輛大驢車,被千萬頭毛驢拉著。除了毛驢,似乎沒有哪種機器可以拉動這架千年老車。”在庫車,圍繞驢興起的打鐵技藝和制皮技藝都享有很高地位。劉亮程認為,新疆手工制品中蘊含著人的用心與溫度,而機器制品則是冷冰冰的,雖然價格低廉,但脆薄易損。劉亮程看到新疆鄉土世界正在受到現代性的侵蝕,原本有溫度的世界正逐漸變得冰冷:“那些延續久遠的東西正在消失,而那些新東西,過多少年才會被我熟悉和認知。”盡管老城人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抵抗與堅持,對流入老城的機器制品視而不見。但劉亮程也不得不承認,雖然變化緩慢,但庫車已經在變了。
四、鄉土文化重建:城市文明弊病糾偏
雖然劉亮程在城市生活,但他的靈魂卻是鄉村的,以黃沙梁以及庫車老城為代表的鄉村是他的精神家園。鄉村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居、蓬勃著生命力的詩意空間,塑造了鄉民們質樸、堅忍、善良的人性,是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五千年不曾中斷的根。面對身體的現代化,劉亮程表示,“我不一定會喜歡未來,我渴望在一種人們過舊的年月里安置心靈和身體。”在他的筆下,城市是冰冷的、聽覺閉塞的、缺乏節制的、沒有敬畏的。他認為在城市里,“我們只知道社會、物質和欲望帶給我們的那些東西,自然的存在似乎被人所忽視”。在劉亮程看來,鄉村的家保留了漢民族的生活理念的完整體系,是萬物共居的家,是鄉村文化的重要載體。他反思道:“當我們推行新農村建設,把農民趕上樓的時候,其實,是在把一整套的文化體系丟棄在鄉村,丟棄在那個破院子里。”
劉亮程雖然在感情上更偏向于鄉村文明,但也未因此就對城市文明全盤否定。劉亮程肯定城市能給年輕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能帶給人更好的物質生活,并表示:“我不批判現代文明,也不批判工業化。村莊是一種地久天長的存在,現代化進程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城市化進程,它似乎是無法阻擋的,但村莊有自己的存在形式和聲音。”面對現代性境遇下人的主體性極度膨脹,劉亮程呼喚我們聆聽自然的聲音,回歸鄉村文明的本真,特別是回歸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積淀下的天人合一的美學理念:人在地球上只占據著一個很小的角落,更多的空間應該是屬于自然的。
劉亮程在菜籽溝村實踐了他的生活理想與文學理想,他買下被荒棄的破敗的院子,重新建構農民與鄉鎮府的中間文化緩沖帶——宗祠與山神廟,讓逐漸現代化的村落的村民們也能夠找到精神的依托,安頓他們的身體與靈魂,他號召更多的藝術家入駐,用文學藝術的力量歸還鄉村本來的面貌,教會村民們保護好村莊本身舊的、古樸的東西,為生活中流浪、在內心中尋找故鄉的人保留正在消失或已經消失的故鄉記憶。這是劉亮程村落文化搶救行動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劉亮程的散文書寫體現了對鄉村生活的回望與肯定,他期望用鄉村文明來糾正城市文明的弊病,倡導文明的多樣化,呼喚對自然本真的崇敬之心。他希望菜籽溝能夠成為喚醒城市居民記憶和人性本真的一處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1] 劉亮程. 一個人的村莊[M]. 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
[2] 劉亮程. 在新疆[M]. 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16.
[3] 劉曉鈺.“地方”與“自然”——人文地理學視角下的劉亮程散文[J]. 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2).
[4] 劉亮程.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
[5] 何新華,王敏. 現代性境遇下的劉亮程散文[J]. 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2).
[6] 何英. 劉亮程的時間[J]. 揚子江評論,2008(5).
[7] 楊維綿. 村莊,生命尊嚴的砝碼——論劉亮程后工業時代鄉土想象[J]. 名作欣賞,2014(3).
[8] 黃增喜. 慢,作為自然的節律——論劉亮程散文的生態意義[J]. 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
[9] 劉亮程. 劉亮程:新疆給了我一個看全國的視角[J]. 新疆新聞出版,2014(8).
[10]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 韓克慶. 現代性、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的現代化[J]. 社會科學研究,1999(4).
[12] 王寧. 文學現代性與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建構[J]. 南方文壇,2023(4).
[13] 葉舒憲. 現代性危機與文化尋根[M].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20.
[14] 高文丹. 葛水平散文集《河水帶走兩岸》的文化尋根指向及現代性反思[J]. 呂梁學院學報,2023(1).
[15] 劉雪明,丁遠洋. 它參與現代文明 卻保持原有聲音[N]. 烏魯木齊晚報,2010-05-21(D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