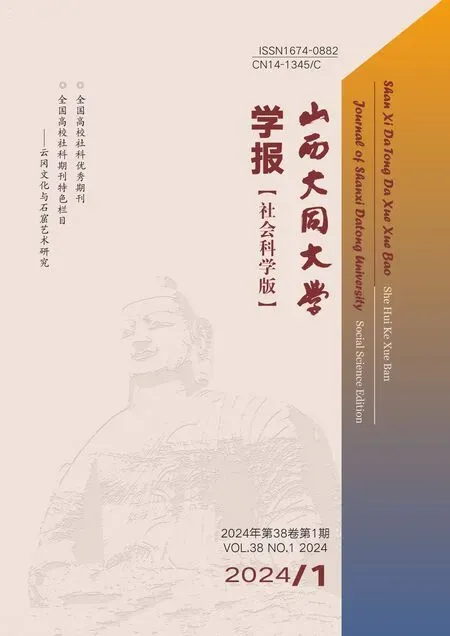流動、傳承、變革:“跨大西洋”關(guān)系的文學(xué)重構(gòu)
譚源星,王影君
(上海理工大學(xué)外語學(xué)院,上海 200093)
起初,“跨大西洋”關(guān)注英國與美國之間社會、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的多重紐帶,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1](P16)隨著對大西洋兩岸地域認知的擴大,研究者的興趣也從最初聚焦在英美關(guān)系轉(zhuǎn)變?yōu)闅W美(美國)關(guān)系、非(非洲)美(美洲)關(guān)系上面。2001 年,“跨大西洋協(xié)會”(Transatlantic Studies Association)成立,旨在系統(tǒng)、綜合、深入地研究大西洋兩岸的經(jīng)濟、文化、社會、政治之間的聯(lián)結(jié)。國內(nèi)學(xué)界對“跨大西洋”關(guān)系的關(guān)注仍然集中在區(qū)域與國別研究的范疇內(nèi),主要圍繞當下美歐政治關(guān)系和經(jīng)濟關(guān)系,研究成果包括《“跨大西洋聯(lián)盟”回得來嗎》[2]《拜登任期,歐洲尋求重塑跨大西洋關(guān)系》[3]《跨大西洋關(guān)系的變化與前景》[4]等論文。有關(guān)大西洋兩岸的歷史、文學(xué)交流,只在比較文學(xué)中有零星涉及,但尚未有關(guān)于“跨大西洋文學(xué)”的系統(tǒng)論述。
作為一個“跨越”的概念,“跨大西洋”里的“跨”(Trans)應(yīng)該放在比較文學(xué)的范疇內(nèi)去討論。在比較文學(xué)的定義中,“跨”是必備的特性。它要求研究對象需要具備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xué)科的條件;其中,跨民族是最根本的標準。[5](P7)可以說,比較文學(xué)為“跨大西洋”研究在文學(xué)領(lǐng)域找到了落腳點;“跨大西洋”也為比較文學(xué)研究提供了新語境下的可能性。如果說“跨大西洋”作為政治概念更關(guān)注當下問題,那么“跨大西洋”的文學(xué)身份則把視角的中心放在了歷史問題上,將大西洋兩岸的文學(xué)連接置于一個龐大、系統(tǒng)的地圖中。
一、“跨大西洋”研究的文學(xué)意識
早在2001年,保羅·賈爾斯在專著《大西洋兩岸的叛亂:英國文化與美國文學(xué)的形成:1730-1860》[6](P70-99)追溯了英美文學(xué)從1730 年到1860 年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探討了美國文學(xué)傳統(tǒng)是如何在與英國文化的談判中形成的,肯定了英國文化對美國文學(xué)身份尤其是獨立戰(zhàn)爭后的身份確立所起到的關(guān)鍵作用。
賈爾斯的另一部著作《虛擬美洲:跨國小說與跨大西洋想象》[7](P22-87)再一次把美國文學(xué)放置在陌生的英國文化語境中,建立起英美文化的跨洋對話和談判。相比第一部著作,這本書更為成熟的地方在于,賈爾斯試圖從文學(xué)身份擴展到國家身份,論證美國國家身份的建立是通過排除對大西洋彼岸的想象而產(chǎn)生的。這部典型的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著作以小說為研究體裁,以“國家身份”為中心話題,從傳統(tǒng)參量(traditional parameters)以外閱讀美國文學(xué)歷史,在關(guān)注焦點、研究內(nèi)容和對象上都有了新的突破。與前兩部著作關(guān)注文學(xué)身份問題不同,賈爾斯的《大西洋共和:英國文學(xué)中的美國傳統(tǒng)》試圖打破限制性的民族主義,揭示英美文學(xué)相互包容又敵對的關(guān)系。事實上,全球化的發(fā)展早已將英國文學(xué)從英語語言文學(xué)中分離出來,將純粹的英國文學(xué)重新定義為后帝國主義框架內(nèi)眾多競爭話語之一。美國文學(xué)是被英國文學(xué)深刻吸引同時又心生厭惡與排斥的異種,它在英語世界制造混亂, 引發(fā)矛盾,并企圖在傳統(tǒng)的、安全的、已知的世界中制造一個更純粹、危險和未知的世界。[8](P127)英國保守的批判思想很容易被美國方言同化,這一結(jié)果又進一步鼓舞美國作家努力重塑自己的身份。
基于賈爾斯對英美文學(xué)關(guān)系的認識,2007年蘇珊·曼寧在其主編的《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一個讀者》[9](P28-59)中提出了如何將跨大西洋模式在文學(xué)研究中發(fā)揮最大作用,圍繞民族主義、世界主義、帝國主義、后殖民主義等議題,進行文學(xué)作品的解構(gòu)與重構(gòu)。這部作品是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第一部學(xué)術(shù)批評論文集,也是首次將跨大西洋研究放在比較文學(xué)理論與實踐中進行探討的編著。在反思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方法的基礎(chǔ)上,2011 年,曼寧主編的另一部著作《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1660-1830》[10](P106-138)聚焦美洲殖民和國家政治分離后的時期;系統(tǒng)定義了“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的含義及其對文化交流和比較文學(xué)發(fā)展的深遠影響;從跨大西洋文學(xué)流派、生平寫作、文學(xué)新聞、海洋文學(xué)、歷史小說、浪漫主義、哥特小說等方向擴大了“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在國際學(xué)術(shù)界的討論。同年,賈爾斯出版了《美國文學(xué)的全球重新定位》,[11]通過對比18 世紀與21 世紀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國文學(xué),論證了美國文學(xué)只在內(nèi)戰(zhàn)后才形成一個獨立的民族主義實體。賈爾斯認為,美國文學(xué)史是一部動態(tài)的、變化的、受不同語境影響的歷史。曼寧與賈爾斯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賈爾斯把美國文學(xué)視為一種成長型文學(xué),從接納、吸收、懷疑到批判英國文學(xué),逐漸形成一種自我滿足、自我教育的模式,強調(diào)美國文學(xué)的動態(tài)發(fā)展。相反,曼寧在對待美國文學(xué)身份的問題上,先是設(shè)置了一個公平的“跨大西洋”模式,然后再將民族、殖民等問題平等地嵌入大西洋兩岸的地域中,進行某個特定時期的靜態(tài)比較,更關(guān)注歷史的偶然性。
此外,伊芙·塔沃爾·本尼特在《跨大西洋故事與閱讀歷史,1720-1810:移民小說》中通過印刷文化構(gòu)建了一個大西洋世界,融入英國人和美國人對大西洋世界的不同看法,從弱勢群體(比如女人、仆人、窮人、無權(quán)力者)的故事的編輯、出版、改寫、重編等變化,探討了為適應(yīng)變化著的讀者、時代與環(huán)境,大西洋兩岸的出版商做出的巨大努力。[12]本尼特對書信體裁也有過系統(tǒng)研究,2005 年和2008 年分別出版了兩部跨大西洋書信指南的著作,[13](P54-94;47-174;295-352)通過書信語言構(gòu)建出跨大西洋兩岸不同的文化觀與價值觀。和本尼特相似,鮑勃·尼克森也關(guān)注了跨大西洋出版歷史以及19世紀以來的數(shù)字化趨勢對英美文學(xué)關(guān)系的影響。[14](P163-174)
二、“跨大西洋”視角下的文學(xué)批評成果
不難發(fā)現(xiàn),在歷史觀的引導(dǎo)下,21 世紀前二十年學(xué)界對“跨大西洋”文學(xué)關(guān)注的焦點集中在三個方面:1.跨大西洋語境下文學(xué)的身份批評,尤其是美國文學(xué)的身份建立問題。2.跨大西洋語境下文學(xué)的社會歷史批評:女權(quán)運動、后殖民、生態(tài)等。3.跨大西洋語境下文學(xué)的審美與語言批評:文體類型、文學(xué)主題、(后)結(jié)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等。可以說,“跨大西洋”這個概念像一個巨大的載體,為現(xiàn)當代西方文學(xué)批評提供了可靠的歷史語境,使得文學(xué)批評本身具備了比較性、互文性的特征。不過,這三個方面的發(fā)展程度和討論深度依舊存在不一樣的特點。
在文學(xué)的身份批評方面,跨大西洋研究重新審視了美洲的原著民文化,還原了印第安文明被入侵、反抗、最終被融合的過程。例如,凱特·弗林特的《跨大西洋印第安人,1776—1930》[15](P26-85)和馬克·里夫金的“跨大西洋印第安問題”[16](P337-355)都對傳統(tǒng)的印第安文化在英國文學(xué)中出于意識形態(tài)目的被利用做了解釋。其實,印第安形象作為一種美洲本土象征,最初是為了幫助英國定義其自身身份。但隨著美洲淪為歐洲的殖民地,印第安原著民反而變成了一種身份不確定的“特殊”族群。有著印第安血統(tǒng)的美國作家應(yīng)該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身份,成為文學(xué)作品中印第安人是否接納自己為‘美國公民’的熱點寫作。也就是說,美國文學(xué)身份的建立經(jīng)歷著印第安血統(tǒng)和歐洲移民血統(tǒng)的不斷碰撞,并且始終被種族歧視和種族消融所影響。正是由于美國文學(xué)身份的特殊性,美國文學(xué)作品中的“印第安人”和“美國人”的形象才會一直被期待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文學(xué)的社會歷史批評中,跨大西洋語境重點關(guān)注的是殖(移)民、女權(quán)、生態(tài)這三個議題。和之前的身份問題不同,“殖(移)民”議題強調(diào)的是其他地區(qū)(尤其是非洲)的原著民到達美國后的身份尷尬問題。美洲殖民地的開拓刺激了奴隸貿(mào)易的發(fā)展,促使美洲出現(xiàn)了一批非裔美國文學(xué)。文森特·卡雷塔就非裔美國文學(xué)中的著作權(quán)、國家定義、種族話語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解決這個作家群體的歸類問題,首先需要設(shè)身處地想象一下第一代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作家的地位問題,英語是否為母語直接決定了他們是否可以被定義為非裔美國人。[17](P11-24)也就是說,非洲血統(tǒng)在美國的身份確立必須首先完成原始語言的消融。其實,在整個殖民過程中,早在到達美洲之前,黑人的身份就已經(jīng)因為被迫離開居住地而變得尷尬起來。保羅·吉爾羅通過《黑色大西洋》描繪了運送黑人奴隸的船只是如何成為大西洋黑人文化的縮影。這種文化并非純粹有關(guān)民族或種族。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涉及復(fù)雜的移民和殖民問題,必然會導(dǎo)致新大陸居民對自身身份的不確定性產(chǎn)生懷疑,有了亟需重新定義族群身份的渴望。對身份的重塑不僅因為殖民問題,還因為美國文化與歐洲傳統(tǒng)文化的矛盾,包括個人主義的發(fā)展等。《“種族”與“文化”之間:英美文學(xué)中“猶太人”的表現(xiàn)》[18](P41-42)分析了猶太人在英美文學(xué)作品里的地位差異。猶太人在英國文學(xué)中是“饑餓困頓”(hunger-bitten)、胡子拉碴(beard?ed)、甚至?xí)砗谒啦〉男蜗蟆N闋柗颉⑹嫣亍蕴睾妄嫷略诟髯缘淖髌分型闯猹q太人的存在,試圖從精神上驅(qū)逐猶太人,并將他們與骯臟的身體器官聯(lián)系起來。而在美國文學(xué)中,約翰·貝里曼則認為,被人認作猶太人沒什么不好的,猶太人和其他人一樣。馬克·吐溫在1898 年有關(guān)猶太人寫作中也對猶太人采取了更加友善的態(tài)度,并且不再把猶太人和疾病絕對聯(lián)系起來,至少馬克·吐溫認為他們是具備公民責(zé)任感的。猶太人之所以在跨大西洋兩岸的形象差異如此之大,是因為19 世紀猶太人的解放與美國膚色矛盾有聯(lián)系。歐洲人的反猶主義建立在身份認同的基礎(chǔ)上,目的是為消滅歐洲人未知的非我。而在美國,一方面基督教傳統(tǒng)沒有歐洲大陸堅固;另一方面,種族問題實際上被膚色問題轉(zhuǎn)移了,加上猶太人能夠參與到19 世紀美國的工業(yè)生產(chǎn)中,并利用西進運動和內(nèi)戰(zhàn)前后經(jīng)濟發(fā)展的機遇在軍事、金融等領(lǐng)域擴大影響力,因此,美國社會總體來說對猶太人更加寬容。
在社會歷史批評的范疇內(nèi),跨大西洋語境也關(guān)注女權(quán)主義下的性別身份問題。女性作家的身份焦慮和女性文學(xué)人物的存在焦慮是女權(quán)運動在跨大西洋文學(xué)作品中的集中體現(xiàn)。路易莎·霍奇森把《小婦人》置于動態(tài)的跨大西洋交流中,通過小說中對社區(qū)(community)的虛構(gòu)來反映女性作家是如何嘗試構(gòu)建更大的歷史社區(qū),[19](P1-14)探索女性作家與跨大西洋社區(qū)的關(guān)系,以及女性作家的性別話語在何種程度上支持或限制了女性作家的文化輸入。從19 世紀開始,美國文學(xué)中出現(xiàn)了一些有自我意識的女性形象,比如悲劇的穆拉塔(mulatto)——一個迷人卻無法融入黑人與白人社會的混血女人,最終淪為了有色人種的犧牲品。她其實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悲劇的繆斯(muse)這一女性形象的延續(xù)和傳承——同樣充滿異域特征的猶太女演員,卻被定義為“墮落的女人”。她們都反映了女性身體在19世紀大西洋兩岸被情色化、種族化、商品化的過程。由此可見,女性文學(xué)在美國的崛起從多方面展現(xiàn)了女性作家對英國甚至整個歐洲傳統(tǒng)父權(quán)的挑戰(zhàn)。女性作家名聲的建立逐漸成為美國社會衡量進步的標準,類似猶太人在美國文學(xué)中形象的改善,這種趨勢實際上宣揚了美國在種族和性別方面的民族品位與能力上的優(yōu)越感。
在生態(tài)問題方面,跨大西洋語境重點審視人與自然的相處方式。海洋運輸、殖民貿(mào)易帶動了皮毛、木材生意,改進了農(nóng)業(yè)等,引發(fā)了兩岸文學(xué)家對環(huán)境問題的再思考。關(guān)于環(huán)境保護的文學(xué)敘述,以及工業(yè)資本主義、城市化的發(fā)展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反映,都成為跨大西洋生態(tài)研究大量探討的主題。在《跨大西洋文學(xué)生態(tài):19 世紀大西洋英語世界的自然與文化》[20](P73-119)一書中,英國浪漫主義時代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沖突、維多利亞時代自然形象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演變、綠色浪漫主義對美國作家和美國讀者的影響,成為跨大西洋區(qū)域生態(tài)流動和生態(tài)傳遞的熱點問題。可以說,“跨大西洋”關(guān)系讓生態(tài)批評首次在跨區(qū)域的廣度得到關(guān)注與討論,開啟了生態(tài)批評與跨大西洋兩個領(lǐng)域之間的交流、補充,強化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無國界”的意識。在漫長的19 到20 世紀,歐洲環(huán)境意識的有關(guān)文學(xué)實踐在美國本土的接受和批評、英國與美國對自然世界的表現(xiàn)方式,成為跨大西洋文學(xué)背景下文學(xué)交流的關(guān)鍵方式之一。
拋開社會歷史批評,跨大西洋語境在審美與語言批評范疇內(nèi)的討論,恰恰又兼顧了文學(xué)本身的意義,避免了文學(xué)完全變成心理學(xué)、社會學(xué)的工具。瑪西亞·阿布勒將小說文體作為跨大西洋文化連接的元素,從小說的閱讀、翻譯、傳播(貿(mào)易)三個方面,論述了19 世紀歐洲文學(xué)在巴西的影響,企圖建立起巴西與歐洲的文學(xué)歷史橋梁。[21](P15-38)阿布勒尤其強調(diào)用民族語言書寫的文本的傳播。他認為,民族語言文本放在跨大西洋語境下,就不再是對單一國家的討論了,目標讀者對小說的傳播,對打破國家和民族的界限起決定作用。阿布勒在語言批評范疇內(nèi)的嘗試,讓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首次系統(tǒng)地跨越到了南美洲的領(lǐng)地,對于拉美文學(xué)在歐洲大陸的身份構(gòu)建有開拓性的意義。除此之外,歷史小說、哥特小說、自傳小說等不同的小說類型,戲劇、表演、新聞等其他文學(xué)體裁在大西洋兩岸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傳播與演變。同時,跨大西洋語境重視“海洋”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存在。歐洲大陸早期的大西洋殖民運動為美國移民后代積累海上生活、探險生活的經(jīng)驗提供了先例。跨大西洋海洋運輸過程中出現(xiàn)的海盜威脅、船舶擱淺、船員溺死等航海事件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為海洋旅行小說、科學(xué)發(fā)現(xiàn)散文、海上勞動頌詩的寫作提供了新素材。
總的來看,跨大西洋語境一方面讓文學(xué)作品找到了跨區(qū)域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依據(jù);另一方面也讓跨區(qū)域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歷史在文學(xué)中得到了藝術(shù)表達與呈現(xiàn)。跨大西洋語境由大西洋連接起兩岸大陸,更多地考慮外部因素對一個國家、民族文學(xué)特征的塑造作用。目前國際學(xué)界重點關(guān)注的是跨大西洋關(guān)系在19世紀是如何打破性別、種族、國家和文化的等級模式,通過可塑性主體與有關(guān)階級、奴隸制、自然知識、民主、宗教等主題的互動,挖掘出美洲本土文化、宗教在英國和歐洲文學(xué)話語中的表現(xiàn),為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英美文學(xué)之間的傳遞(trans?fer)和延續(xù)(continuance)關(guān)系提供更龐大、更多重、更混合的想象空間。
三、“跨大西洋”范式下新的想象空間
現(xiàn)有的研究通常把“英美”(Anglo-American)關(guān)系等同于“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關(guān)系,事實上,英美關(guān)系是包含在更廣義的跨大西洋關(guān)系中的。跨大西洋為歐洲、非洲、南北美洲文學(xué)搭建了溝通的橋梁。21世紀20年代以后的跨大西洋研究需要更兼容地去探討洲與洲的關(guān)系,并將各種關(guān)系理論化,在流通(circulation)和交換(exchange)的新概念(有別于此前的傳遞與延續(xù)關(guān)系)下,將“跨大西洋”語境發(fā)展成一種方法論。
比如,在體裁的選擇上,需要關(guān)注除小說之外的散文、詩歌等題材的跨洋交換。約珥·佩斯曾在浪漫主義“想象力”這一話題下探討過非裔美國詩人菲爾斯·惠特莉和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詩歌的互文性,但局限在奴隸貿(mào)易下的人權(quán)想象。[22](P113-123)他將想象力解釋為“意象—國家”(Imag-I-Nations),導(dǎo)致意識形態(tài)掩蓋了詩歌的藝術(shù)性。梅雷迪思·麥吉爾和托拜爾斯·梅勒里也從經(jīng)濟貿(mào)易文化和廢奴主義等移民色彩語境對詩歌進行過解讀,[23](P37-80;55-78)但忽略了詩歌本身的語言藝術(shù)在歷史傳遞中的變化,也未從詩歌語言本身傳遞的歷史信息中進行閱讀。對跨大西洋詩歌藝術(shù)的興趣,是近年國際學(xué)界對英國文學(xué)遺產(chǎn)在美國的接受與批判的研究的一種延伸。弗吉利亞·杰克森試圖找到英國古老詩歌流派(維多利亞時期的詩歌)應(yīng)如何通過海洋航行,運用科學(xué)技術(shù),流傳到另一個大陸并成為活著的詩歌(living poetry)的方法。杰克森舉例了英國傳統(tǒng)民謠(ballad)、挽歌(el?egies)、頌歌(odes)等不同詩歌形式在19 至20 世紀美國的發(fā)展狀況。[24](P157-164)這種把傳統(tǒng)詩歌流派代表的文化與美國新意識相結(jié)合的嘗試,有利于消除維多利亞詩學(xué)與美國詩學(xué)的分離,豐富了跨洋關(guān)系,以及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的關(guān)系。在跨洋詩歌互文關(guān)系的探討上,馬克·桑迪(Mark Sandy)避免了過多的政治參與。他在“美國書寫”一文中說到,盡管濟慈從未去過美國,但在美國文學(xué)中的想象力卻不曾減弱。[25](P300)作為具有高度感知力的詩人,盡管跨越時空,濟慈和狄金森的詩歌經(jīng)常在理論和情感上不謀而合。這種不謀而合,是狄金森作為被貶低的女性詩人的身份,對濟慈作為下層中產(chǎn)階級詩人的身份被當時主流詩人團體排外的共情。不被當時主流詩界承認的濟慈和狄金森,在懷疑聲中清理出自己的空間,對自我(the self)和他者(the other)的關(guān)系站在生存哲學(xué)的角度進行再思考,從而產(chǎn)生了極具共鳴的身份焦慮。
在文學(xué)與文化的產(chǎn)出上,新的跨大西洋研究需要更關(guān)注過程中傳遞性(transitive)的、循環(huán)的、偶然性的經(jīng)歷。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的初衷是以美國文學(xué)為中心,發(fā)掘歐洲大陸對美國文學(xué)的影響,現(xiàn)有的文獻已充分展現(xiàn)出歐洲文學(xué)、英國文學(xué)對不同時期美國文學(xué)的塑造。然而,因為他們思索的起點在美國,是站在美國文學(xué)對歐洲文學(xué)“要”的角度而非歐洲文學(xué)對美國文學(xué)“給”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所以未形成“跨大西洋”的傳遞意識。比如,維多利亞文學(xué)作為英國工業(yè)革命的產(chǎn)物,在英國本土就是一場浩大的革新。這一時代產(chǎn)生的生態(tài)問題、階級矛盾、性別沖突、民族紛爭等對美國本土文化的主動沖擊是非常顯著的。美國作家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短篇小說《公證人巴特比:一個華爾街的故事》與英國維多利亞作家狄更斯的小說《荒涼山莊》中雖然律師角色的說話方式、敘述表達、思維模式是高度相似的,但在講述司法制度腐敗的根源和人物被異化的原因上卻是完全不同的。[26]這種相似性源自作家相同的語言、文化傳統(tǒng)和思維模式,而差異則是時代、地域、社會背景不同的產(chǎn)物。巴特比從始至終面對的就是針對其個體的“高墻”(the walls),在他被異化之前就已經(jīng)被社會孤立了,作品中的人物從一心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取悅老板、奮力進取的辛勤勞動者轉(zhuǎn)變?yōu)榭床坏焦ぷ饕饬x、看不到未來前景的失望者。但是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勞動者們是被孤立的整體,沒完沒了的法律案件讓所有勞動者都深陷法律系統(tǒng)的斗爭中,以致耗盡所有的精力和財富。在兩部作品里,人物被異化過程的差異需要從英美社會矛盾的差異去解釋。狄更斯所處的工業(yè)革命時代更多聚焦的是階級與階級之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即集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而麥爾維爾呈現(xiàn)的是個人與整個社會環(huán)境的矛盾,這是因為美國當時的社會是資本主義剛崛起的時代。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突飛猛進對個人生活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重大沖擊,對個人尤其是勞動工人的忽視改寫了個人在社會當中的存在模式。這種傳遞性、偶然性的文學(xué)人物的經(jīng)歷,需要跨大西洋文學(xué)用全球性的變化著的視角去感知。
在文學(xué)與政治的關(guān)系上,新的跨大西洋研究要嘗試改善文學(xué)服務(wù)于政治的邊緣地位,避免在文學(xué)研究中出現(xiàn)某種“中心主義”。愛德華·薩義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雖然審視了英國女作家簡·奧斯汀和愛爾蘭詩人威廉·葉芝對帝國主義國內(nèi)經(jīng)濟模式的塑造和生活品質(zhì)的刻畫,為去殖民文化和新政治的建設(shè)做出了貢獻,但顯然某些章節(jié)的政治色彩仍然過于濃厚。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界定問題上,薩義德認為東方主義是西方文化主導(dǎo)下的文化現(xiàn)象,作為西方文化的欲望對象而出現(xiàn),隸屬于歐洲文化;而美國則是超越歐洲所有國家、最具影響力的超大國,具備文化主導(dǎo)的能力,這明顯受到地域中心論的影響。[27](P70)在新的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中,歐洲中心主義或美國中心主義需要隱退,在美國討論歐洲,或在歐洲討論美國,才能讓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保留多元文化的特色。
科琳·格倫尼·博格斯(Colleen Glenney Boggs)在對待文學(xué)與政治的關(guān)系上,則非常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地位的平衡。她定義了馬克·吐溫的小說《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對大英帝國殖民范圍內(nèi)的非洲大地的兩種想象。第一種想象是殖民文化下的移民、殖民和基督教黑奴通過改變宗教信仰構(gòu)建出來的;第二種想象則建立在現(xiàn)代散居黑人回憶中的群體意識中。不過,博格斯的視野不光停留在文學(xué)作品本身,更從作品延伸到與跨大西洋浪漫主義有關(guān)的性別政治、奴隸貿(mào)易、種族主義等其他問題上。她認為,跨大西洋提供了洲際種族構(gòu)建的空間,為支持奴隸制的民族主義提供了條件。而跨大西洋背景下的殖民活動又為一部分黑人和白人作家建立超越種族差異的文化烏托邦提供了支持。同樣,這也適用于浪漫主義時期的印第安社會。美國本土文化其實是放在被種族化了的語境中去閱讀的,這非常影響美國作家的寫作風(fēng)格。“跨大西洋浪漫主義”研究是一個交錯復(fù)雜、需同時著眼全球(global)與地域(na?tional)文化的話題。同時,也帶給我們新的思考:如何主導(dǎo)文學(xué)分析——應(yīng)該強調(diào)作者和文本或者歷史和地理,還是種族和性別?[28](P231)這些偏好的選擇將直接塑造或重塑我們的研究對象。其實,關(guān)注跨大西洋文學(xué)的歷史、政治問題時,可以運用文學(xué)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如“后殖民主義”“女權(quán)主義”等,保留不同文學(xué)作品的民族性,又避免“文學(xué)”或“文本”始終處在邊緣、參考位置。
四、結(jié)語
跨大西洋語境為文學(xué)研究提供了新的想象,促進了大西洋兩岸文學(xué)作品特征的概念化,為現(xiàn)代文學(xué)批評中關(guān)注的種族、殖民、性別、生態(tài)問題呈現(xiàn)出新的研究范式。跨大西洋文學(xué)不僅關(guān)注跨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也關(guān)注自然生態(tài)文明,重新看待人類與動物種群的脆弱性,將殖民運動給土著民帶來的滅頂之災(zāi),聯(lián)想到農(nóng)業(yè)發(fā)展與城市化造成的生態(tài)問題對本土物種生存的威脅,為討論19世紀土著民和本土動植物的環(huán)境意義創(chuàng)造了新的空間。由于跨大西洋敘事具有流動性的特點,它更新了對種族、性別的理解方式,模糊了外來人與土著人、土著生態(tài)之間的界限。回到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的關(guān)系問題上,“跨大西洋”文學(xué)要守住文學(xué)研究的邊界,避免文化研究取代文學(xué)研究,不要讓文學(xué)本身陷入身份危機中。[29](P11-17)現(xiàn)當代文學(xué)理論已經(jīng)有將文學(xué)研究向文化研究方向轉(zhuǎn)型的趨向:解構(gòu)主義將文學(xué)向符號、修辭學(xué)上引導(dǎo),性別主義、后殖民主義將文學(xué)向社會學(xué)上引導(dǎo)。文學(xué)作品中的讀者與作者接連死亡,這些現(xiàn)象值得我們警惕。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的意義之所以區(qū)別于跨大西洋研究,就在于它是從文學(xué)本身出發(fā),最后必須回歸到文學(xué)當中。任何脫離文學(xué)作品的討論,或者僅把文學(xué)作品充當背景而不解決文學(xué)問題的研究,都應(yīng)該歸為跨大西洋研究而非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中。跨大西洋文學(xué)研究學(xué)者,必須權(quán)衡好文學(xué)與文化的關(guān)系,讓文化更好地為文學(xué)服務(wù),不應(yīng)該顧此失彼,或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