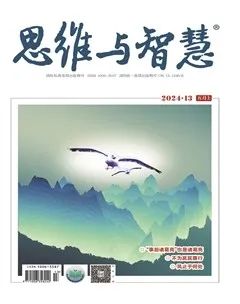頓悟的婆那娑
嚴(yán)奇
波羅蜜是長(zhǎng)在樹(shù)上還是長(zhǎng)在樹(shù)下?南方人大體記得,波羅蜜多長(zhǎng)在樹(shù)上。
入春第一天,辦公樓外波羅蜜樹(shù),樹(shù)梢無(wú)果,樹(shù)干結(jié)果,樹(shù)根滿果,眾人謂之奇,紛紛說(shuō),這棵樹(shù)“頓悟”了。
數(shù)十年前興建辦公樓,主持奠基的領(lǐng)導(dǎo)便在院子一側(cè)栽下這棵波羅蜜樹(shù),一來(lái)寓意興旺發(fā)展,二來(lái)為物資匱乏的那個(gè)年代增加一些甜味。
波羅蜜樹(shù)在風(fēng)雨的澆灌下茁壯成長(zhǎng),結(jié)出了一批又一批熟果,一顆顆如碧綠色彗星般懸掛樹(shù)梢,成為眾人期待的美味佳肴。起初那幾年,常有身手敏捷的年輕人爬樹(shù)摘果,搬來(lái)與人分享,歡聲充盈辦公樓。
波羅蜜之美味,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于《瀛涯勝覽》中形容得貼切:“如冬瓜之樣,外皮似川荔枝,皮內(nèi)有雞子大塊黃肉,味如蜜。中有子如雞腰子樣,炒吃味如栗子。”同事們不懂那么多,只知道波羅蜜取果肉,浸泡鹽水,香甜便四溢而開(kāi)。
春去秋來(lái),這棵“半野生”的波羅蜜樹(shù)漸漸長(zhǎng)到了人手難以企及的高度,斗大的波羅蜜藏在茂密的厚葉間,摘果子的人越來(lái)越少。
有人說(shuō):“果子結(jié)得老高,樹(shù)根的養(yǎng)分輸送不到果子里,肯定不好吃。”
有人說(shuō):“這棵樹(shù)平時(shí)不施肥,不驅(qū)蟲(chóng),不補(bǔ)光,果味必定一般。”
還有人說(shuō):“生活富裕了,不缺水果吃,何必爬樹(shù)費(fèi)那個(gè)勁?”
再后來(lái),每每結(jié)果,環(huán)衛(wèi)工人便早早打下,以免招引蚊蟲(chóng),或落地傷人。曾經(jīng)眾星捧月的熱帶果王,成了一棵乏人問(wèn)津的景觀樹(shù),潦潦草草又活了十?dāng)?shù)年。
長(zhǎng)期受人冷落,較之其他果樹(shù),波羅蜜樹(shù)的不滿總是表達(dá)得慢一些。今番悄無(wú)聲息地將樹(shù)果從樹(shù)上“挪”到樹(shù)下,著實(shí)令人大吃一驚。樹(shù)根上的波羅蜜飽滿緊致,散發(fā)誘人的色澤。還未入夏,蜜甜又濃郁的氣息便沁入辦公樓,吸引不少同事開(kāi)窗聞香。
某天清晨,大家還商討著何時(shí)摘果,夜里樹(shù)根上的波羅蜜如似與人約好逃婚一般,被悄悄撿去,再也找不到了。
相傳,波羅蜜于隋唐時(shí)從印度傳入中國(guó),那時(shí)對(duì)照梵文音譯被稱為“婆那娑”,有“成果”之意。宋朝時(shí),世人隨經(jīng)書(shū)釋義“波羅,此云彼岸,蜜多此云到”,將其改名為“波羅蜜”,并沿用至今。
如今一想,眾人采擷的果實(shí)結(jié)在根上,不在云端。稱其“婆那娑”應(yīng)比“波羅蜜”更妥帖一些。
人生漫漫,不知道有多少成果結(jié)在樹(shù)上,又有多少成果結(jié)在樹(shù)下。身處一個(gè)競(jìng)爭(zhēng)激烈又充滿機(jī)會(huì)的時(shí)代,海量的選擇充斥世人的眼眸。世人低頭看路的時(shí)間比抬頭看景的時(shí)間多,能在低頭看路的過(guò)程中獲得的果實(shí),當(dāng)屬世間至寶。
此岸近人的成果終究能得到世人的青睞,得以解饞;彼岸遠(yuǎn)人的成果哪怕?tīng)N若星辰,也鮮為人知。或許,我們無(wú)法主導(dǎo)從生到滅的成長(zhǎng)軌跡,但我們能控制如何分享成長(zhǎng)果實(shí)。無(wú)論樹(shù)有多高多大,無(wú)論果實(shí)是否得到世人稱贊,我們都應(yīng)該學(xué)會(huì)樹(shù)下“結(jié)果”,降低姿態(tài)與世人同樂(lè)。
成果不入世人之口,怎能得到世人的認(rèn)可?頓悟的“婆那娑”或比“波羅蜜”更有智慧。
(編輯 兔咪/圖 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