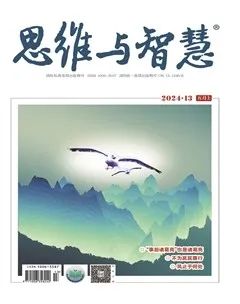與詩詞約會的青春
彭晃
詩詞,是青春歲月里不可或缺的美妙樂章。大抵很多人的青春,都是有詩詞相伴的吧。
我最初接觸詩詞,是初中時的語文課本,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解,令我嘆服。我出生在農村生長在鄉下,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他們對我的教育,是質樸的方言土語構成的言傳與身教,所以當我接觸到那些或激昂或婉約的韻律文字時,為之叫絕,并深深喜歡上了詩詞,而我人生中幾個重要朋友,亦是因詩結緣。
艷芳是我初中三年級才認識的同學,因為都喜歡語文課,因為課堂上對古詩詞熟練的背誦,我倆總是同時受到老師的表揚,彼此逐漸有了惺惺相惜的感嘆并成為最好的姐妹。因為她,我開始品嘗到珍貴的同學之誼。
學校距離我家五里地,若想節省時間,則需要沿著山路翻越一道小山梁,只需要二十分鐘的時間。艷芳的家就在下山后去學校的轉彎處,從她家到學校只需再走十幾分鐘。每天早上,她會準時在家門口的柿樹下等我到來后,再一起去上學。下午放學后,我倆再一起從學校搭伴到她家門口。艷芳長我一歲,每次分手時,她都會囑咐“下山時慢著點”,我則喊“明天見”。我中午帶飯在學校吃,遇著雨雪天氣,她怕我吃冷飯對胃不好,便邀我去她家吃午飯。那時候的我還有些青澀靦腆,她便死拉活拽,竟至有一次倆人一起摔倒,弄得滿身的泥水,而后又哈哈大笑。
艷芳的父親是老中專畢業生,在外地工作,母親曾經做過教師,她受父母的熏陶,自小吟詩誦詞,很有些文藝氣質。當年那樣的家庭背景,曾經多么令我羨慕!她曾把精心抄錄的詩詞本子贈送給我,我至今記得當我坐在山間青石上,初次讀到戴望舒的《雨巷》中的詞句,“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她是有,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的芬芳……”我的眼前浮現出如詩如畫謎一樣的江南風景。
大學舍友曉菩,喜歡唐詩宋詞,吟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感情飽滿抑揚頓挫。我與她“一見傾心”,很快成為最知心的朋友,坐同桌,睡上下鋪,吃一個菜盆里的菜。我們一起訂《星星》詩刊,共同喜歡著北島、食指和席慕容。
學校毗鄰一座小山包,山上植被很好,登上山頂,可以俯瞰整個校園。我與曉菩經常在周末爬山,鍛煉游樂。每次出行,包里都會裝上本唐詩宋詞。行途中,我倆喜歡“對詩”,我說“忽如一夜春風來”,她便接“千樹萬樹梨花開”,她說“身無彩鳳雙飛翼”,我馬上接“心有靈犀一點通”。若接得順暢,便相視會心笑,若有誰對答不上來,便馬上被指控為“小笨熊”,而后一起開心地大笑。
有個喜歡我的男生,為了討好我,便投我所好,每周兩封洋洋灑灑的情書后面,都附上一首詩,變換著各種筆體抄寫,其中徐志摩的浪漫抒情詩最多。他練了字,也最終俘獲了我的感情。
我缺少才情,至今不會寫詩,但激揚的青春歲月里,對于詩詞我曾經那樣地癡愛過。我確信,人間所有的愛恨情仇,都可以升華為詩意的語言。“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掀開時光的帷簾,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與詩詞約會的青春歲月,好像一幅幅唯美的山水畫卷,漸次展現在我的面前,令我沉醉其中,久久不愿醒來。
(編輯 高倩/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