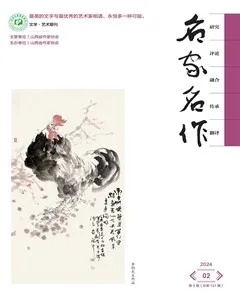植物影像的怪異生態學與錄像藝術實踐
張承昊
[摘要] 當代藝術家制作的錄像藝術以及其他影像中的植物,標志著人與植物以及自然之間新的情感關系得以生成。通過怪異生態學以及情動的去主體性、差異與生成的力量的視角,將討論建立于一種比電影生產更具自由性的影像生產模式,重新考慮錄像藝術或影像中被再現的植物,以及這些植物影像所體現的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觸碰,影像中的植物、人與自然之間的新聯系將被重新審視。
[關? 鍵? 詞] 植物影像;怪異生態學;非人再現;情動;差異與生成
我們如何看待以DV或移動設備為介質的植物影像的再現?我們何以感受它們,無論它們是在城市、公園、都市綠地或近郊,乃至荒野之中?我們如何討論以“恐樹癥”為主題的影像與視頻,以及與之相關的那種奇怪的親密感?很明顯,聚焦于植物的視頻與錄像藝術,并不是以敘事操控單純的情感關系,也不屬于那些早已被批判過多次的凝視機制。由此,它們揭示了錄像藝術所能提供的不同的解讀可能性。在這些錄像的世界中流動著的,是純粹的非人(non-human)影像實驗所生產的強度。將怪異理論[1]加于生態學之上,以此評估這類錄像作品,甚至以此來重新考慮電影中的植物以及它們的再現、它們與人類的聯系,一種視角以及一種邀請或許能夠顯現,它將推動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觸碰。
一、反向戀物、植物與性別
在各類影像中,植物仿佛有了人一樣的生命,在歷史范疇里的各種各樣的文本,擬人都能作為一種賦予物質具有靈魂般的生命的方式。無論是鄭波所制作的錄像藝術,還是我們自行拍攝的視頻,人與植物之間的關系與其隱喻的能指,可能會使觀影者對植物的類人生命感到恐怖或敬畏。在它們被影像化的過程中,一種擬人的幻覺產生,而那些在植物之間的人(男性主體),在影像的機制下自然而然地被物化了。這里存在著雙重的物化:首先,電影媒介將人類進行影像化而產生的物化機制,以及與它緊密相連的,通常被加諸女性角色及人物的物化——包括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提到的切分身體的戀物(fetish)模式以及觀眾認同的窺淫癖(scopophilia)模式,配合俄狄浦斯軌跡(Oedipus trajectory)的敘事,將女性永恒地置于被看的客體位置[2];其次,通過場面調度,人類中心主義的空間關系被重新導向、重新影像化并置。
反向戀物反對基于依賴母親身體的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合寫的電影工業所依靠的系統,即穆爾維所宣稱的對女性的戀物的經濟剝削。[3]“最早的物戀只是關于巫術,以及對于女性的控制”[4],這一巫術般的時刻使得鄭波鏡頭中的非人與人類再現被重新物化、組合。實際上,無性別的自然一直以來都被話語視作是女性的,或者說,它被指派為一個古老的、陰性的性別;由此,這野性的、暴力的以及混亂的女性“自然”,成為男性的科學所要駕馭的客體[5]。文學與哲學的歷史都顯示著資源/女性在奪取行為之間的共通性。而那些蕨類植物與非蕨類植物是無性別的嗎?我們無法像指定人類的性別那樣定義蕨類植物的孢子生產,但無性別可能是人為制造的假象,一種巴特勒(Judith Butler)式的二元性別結構的原型可能廣泛存在,并可能被復制、粘貼,成為一種從古典文學到控制論社會的計算機模型中都能找到的陽性主體—陰性客體的父權等級摹本。但是,即使發現了它的不真實,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種實際上是被建構起來的本質就一定能夠被成功挑戰——它有可能通過顛覆的行為而再次強化自身。[6]
巴特勒做出了回應:物質至關緊要。[7]而人類生產物質與附屬產物,利用各種工具介入自然,進行著新陳代謝,人生產著非人。物質也生產著人:肌肉纖維的無休止的斷裂,通過碳水化合物、脂肪與蛋白質得以重新建構,甚至增殖——這是肌肉生長的辯證運動,通過無生命的非人的物質,人的身體獲得更大的體積。這是一個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式的身體,又一直處于性別的權力關系在歷史的延續中,不斷被類似于表演性(performativity)銘寫社會性別的機制形塑。巴特勒認為,異性性存在矩陣(heterosexual matrix)也在生產生理性別;那些看似是用來形容身體的語言,實際上卻塑造了這一身體。[8]麻省理工學院的主控基因研究為巴特勒的論述提供了科學話語,他們關于TDF決定因子與性征轉化的研究,其部分所依據的推測是,多達百分之十的人有染色體的變異,不符合XX-以及XY-的歸類。[9]既然如此多的人在主控基因而非染色體的語境中,不能契合于二元生理性別的矩陣內,那么它究竟該怎么再去定義?而鄭波的影像則反映了,泛靈論般的植物所再現的性別體系如同埃舍爾和瓦胥本爾所指出的,文化偏見事實上是一系列關于“什么才能構成一項有價值的探究”的定見,而整個胚胎學領域也因為過于偏重細胞核在細胞分化中的中心角色而受到批評。[10]當親密超越既定的主體,進入一個人與植物、自然或生態之間的關系網絡。那么何為自然?“自然而然”之物如何被建構?這也與影像制作的批評與實踐有關。
二、朝向一種怪異生態學
具有獨特繁殖模式的蕨類植物所給予藝術家的,更多的是一種聯通:從作為他者的植物映射作為他者的其他物質,以重新揭示非人存在的能動性。而這一切都借由錄像與視頻藝術更進一步的形式自由而實現,這種自由標示了超越古典敘事模式與主流的電影制作體系的影像生產模式。此處對植物的再現,是將鏡頭重新對準非人物質的一次嘗試。怪異理論的介入使得知識生產經歷跨學科化以及對科學既定話語的解構。[11]
變動,即“怪異”。透過影像中的植物,對于它們葉片或枝蔓舒展或擺動的調度,暗示了怪異生態學的一種文本現實。城市可以被一種主流男性知識分子的空間吞噬,牧場、鄉村或荒野也能被建構為一種男性征服自然以確證自身的神話。具有語言優勢的主流系統卻自如地征引、遮蔽著其他的經驗;同樣地,電影作為一種再現系統,仍然復制著相同的生產模式。
如前所述,在一個將女性、動物、自然與性存在去價值化的文化中,某些主體被陰性化、動物化以及自然化。[12]因而,不只是伊麗莎白·格羅茲(Elizabeth Grosz)倡議一個與非人存在共在的理想的世界;不同的空間分配伴隨著主體的建構,非人的性、它的多元性,以及生態問題的解決,也許都可以寄希望于怪異理論——不僅是類比于怪異動物的多元取向[13]所體現的。另外,德勒玆(Gille Deleuze)裝配(assemblages)的怪異生態學具有跨學科、塊狀統籌的特性,啟示著一個“多于人”的復數的肉身(more-than-human corporealities)[14]:這將提供另外一種打破圍繞著菲勒斯霸權的等級化的剝削體制的工具,這種體制廣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對古典好萊塢的挪用之中。由此,怪異生態學還提供了更多的影像可能性,正如鄭波的錄像藝術挑戰著影像再現的陳規與非人物質的從屬地位。這與羅安清試圖改變人類中心主義的方式類同,使一種朝向人的知識的物質回歸其自身的互相呼應,運用一種工具去直觀物質與世界之間的參與,使物質獲得其本身的生命[15]。看似中立的科學、技術與存在實踐(practices of being)也難以改變人類中心主義,非人(nonhumans)將保持著消極、非能動的狀態。[16]
三、人與非人之間:非人再現與怪異情動
鄭波偏愛的蕨類植物的葉子像是四肢,延伸于層層疊疊的綠墻、綠霧間。人的身體在仿佛沒有邊界的綠墻的裂縫里移動,在被我們稱之為植物的物質及其質地(texture)[17]之間游移;而鏡頭則可以不斷地重構或置換空間關系。所有這一切身體與植物之間的親密,并非任何一個地區的主流電影工業模式所能盡數體現。此時此刻,人的有機體與植物的有機體之間不但相互連接,更仿佛已經失去了能動性上的差別:鄭波4K畫質錄像作品的影像特質給我們一個例證,它契合勞拉·穆爾維在20世紀70年代所呼吁的對主流電影快感的抵抗[18],使不同的戀物模式得以體現。那么,它的作用機制可能是什么樣的?它何以觸動觀影者的情感,又如何借此來模糊主體的邊界,從而促成新的生成(becoming)以及人類與非人物質之間的新關系?新泛靈論(the new animism)[19]開啟了新思考模式,然而,泛靈論也將其禁錮于一種人類意向性中,如果物的“靈”按照泛靈論成為人類情感的延伸存在,那么物與物之間的交互就不再那樣明朗;回歸一種重新思考的裝置,可能需要邁克爾·馬德(Michael Marder)的“植物思考”(plant-thinking)——“讓我們進入一種多物種關系,在那里意識與意向(intention)也許不是起點。”[20]
由此,這種多物種關系顯現于錄像藝術、視頻與電影中的植物——這些非人的存在的再現之間。在德勒玆看來,藝術創作的目的在于“從知覺及其主體狀態中提取感知物,從各種狀態轉換的情狀中提取情動”[21],與此同時得以強調的正是“差異”的潛力:“如果哲學是將語言從對概念和問題的簡單定義和定見的固化之中解放出來,那么藝術則是創造感受和感知。”[22]而藝術在這里所創造的包含著情動的聚塊并不來自人們固化了的定見,在柏格森的意義上,這些定見漠視了情感的狀態。因此,在差異的力量之下,藝術家應當將各種感受與感知不斷地增添到這個世界,當創作完成之后,作為觀眾的我們還會被拽進感覺復合體,我們便與情動一同生成。[23]由于情動是非個體的、流動的,它承諾了一種混淆主客體的開放性質:“我在感覺中生成……同一個身體既給予它也接受它,而這個身體就既是客體又是主體。”[24]同樣地,德勒茲引述塞尚,論述了去主體式的思想[25],并且塞尚對模糊輪廓的思考、回歸物本身與主客體的取消也已被梅洛-龐蒂論述過[26],德勒茲似乎往前更進一步,思考如何生成為非人。
“被體驗的知覺上升到感知物,從被體驗的情感上升到感受(情動)。”[27]由此,在這種消弭主體邊界的思潮下,現象學與德勒茲理論似乎相交錯,反應并生成關于肉身的論述;從梅洛-龐蒂的肉身觀念出發,德勒茲認為“世界和身體作為對應物彼此交流”,而電影實現了這種交流[28],從肉身的混沌之中被訴諸框架結構的形成,再由此產生新的情動[29]。換句話說,在電影與影像藝術中,正是這種“差異”促成了新的轉化與生成:“我感覺,我生成為女人……生成為通靈者,生成為純粹物質”——科勒布魯克等諸位學者由此探討了有關德勒茲與巴特勒的主體間性以及德勒茲理論的怪異性。奈基亞尼(Chrysanthi Nigianni)在序言中引用德勒茲與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并進行論述,認為巴特勒理論中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與德勒茲與加塔利的思考相似,他們使得怪異遠離通過再現與指認而實現的再生產[30]。德勒茲以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取代精神分析,試圖詢問中產階級家庭模式對欲望的壓抑,詢問為何我們應該接受慣例、標準和價值,又是什么阻止了我們去創造未來的新欲望或新形象;換句話說,通過反對合理化,創造和轉變的權力被推進了:“不存在原初的心靈,而只有原初的部件,是‘精神分裂或非人的、可移動的碎片。”[31]因而,影像中非人生命的再現使主體的情感得到另類的觸發,人類的主體性邊界被許諾以瓦解的可能,響應著關于差異與非人的論述:“存在著多樣化的人類綿延和非人的綿延,我們要超出被空間化了的和秩序化了的視角,才能思考其他的綿延。”[32]
四、結束語
錄像藝術中的怪異生態學與跨物種的非人物質再現,將重新錨定跨物種的情感與情動生產以及相關的擾動的力量。離開主流電影生產模式的凝視與戀物機制以及敘事生產的束縛,將更自由的影像形式與數字制作納入考量的范圍,那么這種力量恰好可以通過以下方面得以顯現:首先,植物影像的怪異生態學標定了新物質主義的轉變,強調植物以及非人物質,從泛靈論的介入情動理論的攪擾,我們能夠看到一種開放的潛力,這將使人與物質之間的層級重構成為可能;其次,人與非人之間的影像再現背后的情動生產機制保障了使這種可能性得以實現的潛力,由差異而生成,這使植物影像的實踐能夠對穩定主體邊界的消解與新的情感關系的生成之間的聯動作出承諾。
參考文獻:
[1]王逢振. “怪異”理論[M].陳俊,譯.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2][18][英]勞拉·穆爾維. 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M]//楊遠嬰主編. 電影理論讀本.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
[3][英]勞拉·穆爾維. 戀物與好奇[M].鐘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美]威廉·皮埃茲. 物戀問題[M]//孟悅,羅鋼.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1.
[5][美]卡洛琳·麥茜特. 自然之死:婦女、生態與科學革命[M].吳國盛,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
[6][8][美]朱迪斯·巴特勒. 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M].宋素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7][9][10][美]朱迪斯·巴特勒. 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M].李鈞鵬,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139-142.
[11]Valentine,D. Imagining Transgender:An Ethnography of a Category[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140.
[12]Mortimer-Sandilands,C. and Erickson,B. “Introduction:A Genealogy of Queer Ecologies”[M]// Mortimer-Sandilands,C. and Erickson,B. eds. Queer Ecologies:Sex,Nature,Politics,Desi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1-47.
[13][14]Sandilands,C.“Queer Ecology”[M]// Adamson,J.,Gleason,W. A. and Pellow,D. N. eds. Keywords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6:169-171.
[15][16][19][20] Tsing,A.“When the Things We Study Respond to Each Other: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Material”[M]//Harvey,P.,Krohn-Hansen,C. and Nustad,K. G. eds. Anthropos and the Material.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9:222-243.
[17]Donaldson, L. F. Texture in Film [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14.
[21][23][25][27][29][法]吉爾·德勒茲,菲利克斯·加塔利:什么是哲學?[M].張祖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439-440,456,413-445,439-440,473-476.
[22][31][英]克萊爾·科勒布魯克.導讀德勒茲[M].廖飛鴻,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26-27,6.
[24] [法]吉爾·德勒茲.哲學的客體:德勒茲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1..
[26][法]莫里斯·梅洛-龐蒂.意義與無意義[M].張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28][澳]雷克斯·巴特勒. 導讀德勒茲與加塔利《什么是哲學?》[M].鄭旭東,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9.
[30][32] Nigianni,C. and Storr,M. “Introduction” [M]// Nigianni,C. and Storr,M. eds. Deleuze and Queer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1-10.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