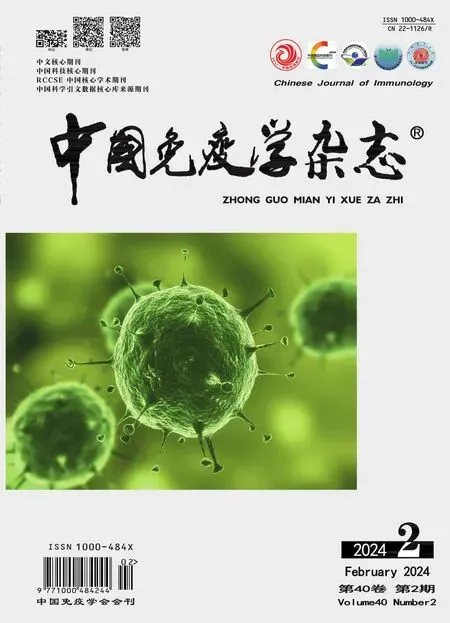低密度中性粒細胞的表型和功能多樣性
李佳玉 張野 黃長形 (空軍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傳染病科,西安 710038)
中性粒細胞是人體數量最多的白細胞,占循環白細胞的50%~70%,在機體發生感染時首先被招募至感染部位,是宿主抵御外來病原體入侵的第一道防線,在清除病原體方面起重要作用[1-2]。中性粒細胞可通過吞噬、排出顆粒內容物和釋放中性粒細胞胞外誘捕網(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等方式發揮免疫防御及清除病原微生物等作用[3-4]。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中性粒細胞是一種非特異性終末分化細胞,具有特定細胞核形態,功能單一,半衰期短,轉錄活性低[5-6]。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中性粒細胞是一種更為復雜的細胞,可合成細胞因子、趨化因子,對適應性免疫也發揮調節作用,具有不均一性和可塑性的特點[7-10]。在炎癥反應中,中性粒細胞受多種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誘導發生活化使其壽命延長并呈現不同細胞表型[11-12]。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在不同生理或病理狀況下,循環或組織中的確存在不同中性粒細胞表型和不同功能的中性粒細胞亞群[2,6,11,13]。
中性粒細胞的異質性是免疫病理生理學的重要特征[5,13]。有研究者已提出基于其成熟程度評估中性粒細胞亞群的策略[14-15]。但近20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根據中性粒細胞密度進行分群。密度梯度離心采用Ficoll分離技術,這種技術在1976年開始應用,常用于從人外周血白細胞中分離單個核細胞[16]。血液白細胞分層于Ficoll溶液,在離心過程中根據密度不同導致包含不同細胞類型的層形成。由于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密度較低(包括淋巴細胞和單核細胞),位于血漿和Ficoll之間的界面,而正常密度中性粒細胞和紅細胞位于底層。膿毒血癥、腫瘤、病毒感染、過敏性哮喘及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病理情況下,將患者全血密度梯度離心后,PBMCs中存在一個與正常密度中性粒細胞功能不同的低密度中性粒細胞亞群[14,17-23]。人們將中性粒細胞這個重要且獨特的亞群稱為低密度中性粒細胞(low density neutrophils,LDNs)。
LDNs名稱的由來是相對于紅細胞層分離出的正常密度中性粒細胞(normal density neutrophils,NDNs)或高密度中性粒細胞(high density neutrophils,HDNs)而言的。LDNs由活化的成熟中性粒細胞和不成熟的中性粒細胞共同組成[14]。在細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所致感染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中性粒細胞被招募和激活,一部分NDNs活化脫顆粒,導致密度降低,浮力改變,還有部分未成熟的中性粒細胞從骨髓中過早釋放,這兩種原因都使LDNs與PBMCs在同一密度梯度中共存[7,22]。流式細胞術測定表面標志物表達可區別PBMCs中的單核細胞和LDNs。單核細胞高表達CD14和低表達CD15,LDNs高表達CD15和低表達CD14[24]。LDNs的表面標志物主要為CD66b、CD11b、CD16、CD10等,CD66b是一種特定的粒細胞標志物,參與呼吸暴發[8];CD11b存在于明膠酶顆粒膜,分泌囊泡;CD16是成熟中性粒細胞標志物,參與脫顆粒;CD10亦是一種中性粒細胞成熟標志物,有研究發現CD10表達可將LDNs明確分為成熟和不成熟細胞,成熟的CD10+亞群表現為抑制T細胞增殖,而不成熟的CD10-亞群則表現為促進T細胞增殖[6]。不同疾病的LDNs表面標志物不同,如多發性骨髓瘤患者LDNs表達為CD11b+CD14-CD33+CD15+HLA-DRlow/-;HIV患者LDNs表達為CD15highCD33highCD66bhighCD62LlowPD-L1low[8]。目前研究發現,在多種疾病中LDNs比例明顯升高,在固有和適應免疫反應中發揮重要作用[14]。而在健康人體內,LDNs比例極低[6]。
中性粒細胞表型在表面標志物功能表達方面也存在異質性[25]。根據其功能LDNs可分為促炎LDNs[也稱低密度粒細胞(LDGs)]和免疫抑制性LDNs[也稱粒細胞源性抑制細胞(PMN-MDSCs/GMDSCs)]。如在SLE和牛皮癬患者中發現的LDNs具有促炎功能,而在癌癥、慢性細菌和病毒感染、創傷和敗血癥多種病理條件下,PBMCs中發現的骨髓衍生抑制細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則具有免疫抑制功能。下面重點介紹SLE和癌癥中LDNs的表型和生物學特征。
1 SLE與促炎LDNs(LDGs)
SLE是一種嚴重的慢性且無法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SLE患者血液中出現大量不成熟的嗜中性粒細胞,中性粒細胞失調與SLE的發病機制有關[21,26]。1986年,研究者從成年SLE患者獲得的PBMCs制劑中發現了“低浮力密度中性粒細胞”[27],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采用密度梯度法可在PBMCs中分離出LDNs。
SLE患者的LDNs表達CD15、CD16b、CD33和CD11b,與NDNs不同的是,SLE患者的LDNs表達更高水平的激活標志物CD11b、CD66b、CD63和CD107a。LDNs的表面標志還發現了CD11c、CD31、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受體和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受體。重要的是,SLE中LDNs執行中性粒細胞功能的能力是兩極分化的,基于成熟的CD10+和不成熟的CD10-中性粒細胞。SLE患者的HDNs中90%為成熟細胞,而LDNs中60%為成熟細胞。
LDNs在SLE患者循環中明顯升高,CARMONARIVERA等[27]發現其檢查的成年SLE患者PBMCs層均存在LDNs。LDNs能積極產生炎癥細胞因子并在體外殺死內皮細胞,具有促炎功能。研究表明,SLE中的LDNs分泌的促炎細胞因子水平升高、吞噬功能受損、NETs形成增多[14]。值得注意的是,SLE患者的LDNs顯示NETs形成增強,生成NETs能力增強依賴于線粒體ROS,通過增強線粒體ROS生成的NETs,在誘導Ⅰ型干擾素和其他炎癥細胞因子方面比其他刺激生成的NETs具有更強的免疫刺激性,提示這種類型中性粒細胞的存在可能是其他形式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基礎[28]。值得注意的是,LDNs產生NETs的能力因疾病而異,如在SLE和銀屑病中,LDNs比同一患者的NDNs產生更多NETs;而在類風濕關節炎中,NETs形成似乎無差異[7];高血壓中NETs形成減少[22]。MISTRY等[21]也證實了LDNs的這些特性,利用個體和單細胞轉錄組學、表觀遺傳學和功能分析發現SLE患者的LDNs具有顯著轉錄和表觀遺傳異質性,LDNs的轉錄因子基序分析與NDNs和健康對照中性粒細胞存在差異,各亞群在NETs形成、氧化線粒體DNA釋放、趨化性、吞噬作用、脫顆粒、損害內皮能力以及對Ⅰ型干擾素刺激的反應等方面差異明顯。
SLE的致病因素與Ⅰ型干擾素密切相關,超過50%SLE患者的干擾素通路被激活[29]。研究發現,SLE中的LDNs可增加Ⅰ型干擾素分泌,有助于炎癥和組織損傷循環[14,21]。與其他免疫細胞亞群相比,LDNs的干擾素基因表達最高。不同LDNs亞群與狼瘡的具體臨床特征和冠狀動脈疾病的存在和嚴重程度相關。LDNs在SLE中促進免疫失調和顯著血管損傷[21]。
目前不少研究者將LDNs作為SLE治療的新靶點,認為對致病性LDNs亞群的識別可能有助于開發靶向中性粒細胞群體的藥物,同時保留中性粒細胞介導的宿主防御。LDNs中促進NETs形成或促進NETs清除的藥物可能為SLE提供新的治療策略。
2 癌癥與免疫抑制LDNs(PMN-MDSCs/G-MDSCs)
中性粒細胞在腫瘤微環境中具有功能可塑性,同時具有促腫瘤和抗腫瘤功能,在癌癥進展中起重要作用[30-32]。癌癥早期,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s)可能顯示抗腫瘤特性,但在癌癥晚期,中性粒細胞發揮增殖、侵襲和擴散以及免疫抑制功能促進癌癥進展,因此多數研究將中性粒細胞描述為癌癥進展的主要驅動力。一項對數千例人類癌癥的薈萃分析發現,中性粒細胞與疾病預后差相關[33]。越來越多的研究將循環中的中性粒細胞數量和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的比例作為評估癌癥進展的預后標志物[15,34-35]。
值得注意的是,中性粒細胞的表型和功能在腫瘤進展過程中變化較大[36]。大量關于癌癥的研究都報道了一種中性粒細胞的亞群——LDNs,其比例隨著癌癥進展顯著升高,因此LDNs往往成為循環中性粒細胞的主導群體[37]。LDNs已在乳腺癌、肺癌、頭頸部癌癥、泌尿系統癌癥和淋巴瘤患者中被發現。據報道,晚期肺癌患者LDNs比例越高(>10%)預示生存率越低[2]。癌癥中的LDNs由未成熟的MDSCs和成熟的細胞組成[15]。癌癥研究中,LDNs具有免疫抑制特性,通常也稱為PMN-MDSCs/GMDSCs。
MDSCs是2007年提出的術語,代表未成熟髓樣細胞的異質群體,參與疾病免疫調節各方面,包括癌癥、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創傷等[38]。其中,MDSCs在腫瘤微環境內為抑制細胞并能防止腫瘤細胞被免疫消除[39]。MDSCs由兩大群細胞組成:多形核MDSCs(PMN-MDSCs)和單核M-DSCs(M-MDSCs)[39-40]。PMN-MDSCs/G-MDSCs在表型和形態上與中性粒細胞相似,而M-MDSCs與單核細胞相似。
目前,從PMN-MDSC中分離中性粒細胞的唯一方法是梯度離心。最初使用術語“G-MDSCs”描述PMN-MDSCs,但目前發現PMN-MDSCs能更好地定義MDSCs這個亞群。PMN-MDSC在表型上不同于正常成熟的中性粒細胞,PMN-MDSC顆粒減少,浮力改變,CD16和CD62L表達減少,精氨酸酶1增加,CD11b和CD66b表達增加[38]。
人類PMN-MDSC的特征為CD11b+CD14-CD15+HLA-DR-或CD11b+CD14-CD66b+,小鼠PMN-MDSC特征為CD11b+Ly6GhighLy6Clow細胞和類似中性粒細胞。人類M-MDSC特征為CD11b+CD14+CD15-HLADRlow/-,由于HLA-DR低表達或缺失,M-MDSC可與單核細胞區分,小鼠M-MDSC特征為CD11b+Ly6GLy6Chigh[39,41]。可見PMN-MDSC和M-MDSC不僅在表型和形態上不同,且具有獨特(雖然部分重疊)的功能特征和生化特征,這些特征反映其在不同病理條件下具有不同作用。
PMN-MDSCs的標志是其抑制T細胞功能的能力,與LDNs在SLE中的研究結果不同。兩項調查SLE患者MDSCs的研究表明,PMN-MDSC表型細胞水平與升高的疾病活性和干擾素信號相關,但未抑制T細胞增殖或激活,因此是LDGs而非MDSCs[23,40]。
早期癌癥發展過程中,NDNs占主導地位,導致整體抗腫瘤反應。隨著癌癥進展,LDNs成為主導,導致整個中性粒細胞表型轉向促腫瘤功能。SAGIV等[37]研究發現,成熟的NDNs能夠以依賴TGF-β的方式轉換為LDNs,這種轉換會成為LDNs——未成熟粒細胞骨髓源性抑制細胞(G-MDSCs),丟失了抗腫瘤特性卻獲得免疫抑制特性。雖然HDNs和LDNs可能來自共同的祖細胞,但其進入循環的釋放受到不同調節。LDNs在循環中迅速積累,而NDNs在循環中出現的時間要晚得多。盡管不少研究證明中性粒細胞表型在體內發生了轉換,但由于中性粒細胞回收程度低,這種轉換的全部程度難以在體內評估[37]。
3 結論
中性粒細胞具有異質性和可塑性,在疾病中發揮復雜多樣的功能,已證實中性粒細胞具有不同亞群。近20年來,具有促炎和免疫抑制功能的LDNs亞群得到廣泛關注。研究表明,LDNs是一個異質群體,通常有很大比例的未成熟細胞。成熟細胞和不成熟細胞的比例與疾病種類及病情均有關。LDNs在固有和適應性免疫應答中發揮重要作用,活躍地參與病理性損傷,這是一個有希望干預的新治療領域。研究該亞群有助于開發對疾病有針對性、有選擇性的藥物,如在SLE中,促炎LDNs能通過線粒體ROS產生增加NETs形成,因此直接靶向LDNs為研究新的治療藥物提供策略;癌癥過程中,CCR5在引導免疫抑制性LDNs動員中起關鍵作用,因此建議將阻斷CCR5作為癌癥治療的方法。目前尚無明確的標志物確定LDNs這個群體的深度特征。LDNs亞群的表型和功能差異需要進一步研究,作為一種新的治療目標為疾病提供新的治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