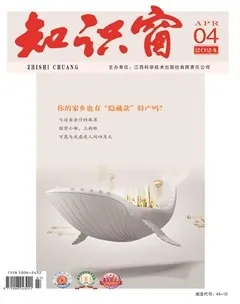飛過宴會廳的麻雀
朱成玉
我現(xiàn)在越來越不喜歡動,而喜歡就那么坐著,一邊思考,一邊打盹。比如此刻,我靜坐在這里,一動不動。其實(shí),我正騎著一匹馬,向夢里的光飛奔。
當(dāng)你睡下,光就不存在了嗎?錯,光一直在,只是你沒有看見它罷了。況且還有夢,那里有更多的光涌出來。
我夢見一面墻,墻上長出很多舌頭,貪婪地吸吮著陽光,但是它再貪婪,也沒有辦法把陽光全部吸干。陽光生生不息,過了一個夜晚,必將再次照亮世界。
我夢見一棵樹,投下巨大的樹蔭。而那些濃蔭正在被無數(shù)搬家的螞蟻合力搬走。看,螞蟻需要陽光的時候,會迸發(fā)出多么強(qiáng)大的力量。
而我們呢?多少人喜歡活在殼里。這樣就免受傷害了嗎?恰恰相反,傷害你的是你自己——你若是一枚哀傷的蛋,就只能孵出憂郁的小鳥。
多少人,被黑暗涂抹著,面目全非。其實(shí),只要我們肯往內(nèi)心里再挖掘一毫米,總會找到一點(diǎn)磷,點(diǎn)亮生活。
再漆黑的老屋,也會被白花花的日光叫醒。可是,如果窗子久久不開,而且掛著厚厚的窗簾,那么陽光也無能為力。這就需要你做一個晴朗的人,勤奮工作,努力愛人。一個晴朗的人,不是說他的心頭沒有烏云,也不是說他沒有暴怒的閃電雷霆,而是說他活得通透,懂得愛與取舍。一個晴朗的人,不論陰天或雨天,內(nèi)心的枝干上都能長出幾片追逐陽光的葉子。
甘心平凡,但不甘心黯淡無光。即使自己不發(fā)光,只要有光的時候,就要懂得承接、積聚和擴(kuò)散。你可以不具備制造光亮的能力,但請務(wù)必?fù)碛幸活w接納光亮的心。如此,你便也是晴朗的人。
納博科夫說:“搖籃在深淵上方搖著,而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存只不過是兩個永恒的黑暗之間瞬息即逝的一線光明。”比起納博科夫,圣彼得的說法更明朗些:“人生就像一只飛過宴會廳的麻雀,從黑暗中來,又沒入黑暗,其間只有光明的一刻,而那一刻的光明,就是我們必須抓住的。”認(rèn)真生活,在活著的光陰里,找到被人生偷藏起來的糖果,以及那一束有甜味的光。這人生啊,順流而下和逆流而上,都可以活得很精彩。只有竭力對抗過嚴(yán)冬的雙手,才能捧起春天最美的花朵。
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精神小鎮(zhèn),在那里,我們可以布置自己喜歡的東西,比如風(fēng)車、玫瑰園、圖書館。圖書館的巨幕上,一定要投放納博科夫?qū)Χ砹_斯文學(xué)那一段形象的論述。他當(dāng)著學(xué)生的面,把教室里所有的窗簾都拉上,教室里漆黑一片,他打開一盞臺燈,微弱的光線射在講臺上,他說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著,他打開屋里所有的日光燈,他說這是普希金;最后,他拉開所有的窗簾,陽光照亮了屋子,他說這是列夫·托爾斯泰。
皆為照亮,臺燈、日光燈和陽光,對比鮮明。這當(dāng)然是為了表明托爾斯泰的偉大,但我更愿意相信這是對托爾斯泰作品深層次的闡釋。托爾斯泰的“照亮”,與魯迅的“喚醒”,殊途同歸。
我想,真正的寫作者,應(yīng)該是一直在尋找打開自己的那把鑰匙,然后從善中提取惡,把它掐滅,或者從惡中提取善,將其點(diǎn)亮。
懷有晴朗之心的人,面對納博科夫和尼采口中的深淵,甚至都不必惶惑。在我看來,那不過是彎曲過多的、向下的曲線而已。只要有光的穿針引線,深淵也可以通向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