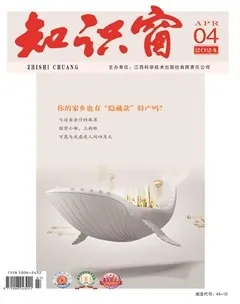想起老師的訓誡
韓煥忠
我讀碩士時的導師李景明教授,已經從曲阜師范大學退休十余年了,平常居住在曲阜鄉下的農場中,以種莊稼、養家禽為樂,過著許多當代人都很羨慕的耕讀生活。李老師是研究秦漢儒家經學史的,曾經在論文中指出,秦朝以水為德,數用六,色尚黑,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極其重大而深遠。李老師對我的訓誡和教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終身受用,甚至在我做了研究生導師后,也經常引用來指導我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
讀研時,我的想法很多,閱讀過某個領域的一兩部著作、幾篇論文,就覺得自己對這個領域很有研究,可以深入下去。讀了周桂鈿的《董學探微》《虛實之辨》,就很想探討先秦兩漢時期的天人之辨;讀了楊俊光的墨子研究,就很想去研究實用主義在中國興盛的普遍性與必然性;讀了潘富恩、陳來、楊國榮關于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著作,就覺得宇宙吾心、古今一念、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讀了大衛·格里芬關于后現代主義的小冊子,就想對解構主義之與中國思想文化的重建表達點看法。
現在想來,那時正是我思若飄風、意若涌泉的時期,各種想法紛至沓來,但都像過眼云煙一樣,很難穩定下來,所以未能真正形成什么氣候。大多時候,李老師都是提著杯子,靜靜地聽我絮絮叨叨,不置可否,偶爾也會鼓勵我認真讀、讀完整。有一次,好像是1998年元旦,我和幾個同學在李老師家里吃飯時,李老師說:“你們想學這,想學那,想在很多領域都成為專家,這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我們這一輩子,也許可以干好一件事,也許一件事都干不好。記住‘一招鮮,吃遍天;招招會,活受罪。”真是一語警醒夢中人,當時我心頭一震,原來滿肚子的話語竟然一下子都煙消云散了,長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后來,李老師又說了一句:“你必須將自己的想法集中在一個學科上。”可以說,李老師的話如同重錘一般,敲在我的心上,讓我至今都記憶深刻。從那以后,我就只關注思想史方面的問題了。
李老師見我不再嘟囔,就接著啟發我們:“你們一定要多寫文章。要知道,想想是氣體,多想只是比較容易形成氛圍而已;說說是液體,多與人討論雖然也可以增長知識,但最多也就是鍛煉一下口頭語言的表達能力罷了;只有寫出來才是固體,才是可以展示的成果。你們要將自己的想法寫出來,這樣才有用。”自那以后,我的話語逐漸變少,開始進入勤奮寫作的階段,兩三個星期就寫一篇文字交給李老師。有時是寫儒家的,有時是寫宋明理學的,具體怎么寫的,現在都忘了。當時,我還沒有電腦,都是手寫的,我先是起個草稿,將自己的所有想法一股腦兒都寫出來,然后整理成自己還算滿意的文稿,再重新抄寫一遍。30 000個空格的草稿紙,我幾天就寫完一本,抄好了就交給李老師。李老師對我的這些所謂文章有時不置可否,有時也會說點今后應該注意的事項之類。有一天晚上,李老師見我在教室里與一個同學討論,就加入進來,閑扯幾句,很自然地就聊到寫論文上。李老師說:“寫論文一定要寫系列性的專題論文,無論多少篇,主題都要單一,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斧頭,胡砍亂榷,那樣很難成氣候的。”我馬上意識到,這是針對我胡亂寫作而說的。自那之后,我進一步集中關注領域,決定只寫儒家人性論方面的東西,其他的即便讀了,也不再去寫了。
后來,我寫孔子的人性論,寫好了交給李老師;寫孔門后學的人性論,寫好了交給李老師。寫孟子的人性論,寫荀子的人性論,寫董仲舒的人性論,寫韓愈的人性論……我就這樣寫呀寫呀,也不管李老師是否受得了,反正寫好了就交給他。讀書、寫論文,讀書、寫論文,幾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在別人看來,這種生活也許是單調的、枯燥的、乏味的,但我沉浸其中,覺得充實而有味。
李老師時不時地會與我談如何寫論文。有一次,李老師說:“讀書的時候不寫作,寫作的時候不讀書。”我對這句話的體會是,讀書的時候不寫作,可以防止有意無意地抄襲別人的東西;寫作的時候不讀書,可以保證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有一次,李老師說:“思考的時候,過程在前,結論在后;寫作的時候,結論在前,過程在后。”之后,我幾乎所有的論文是開門見山,先把本文的核心觀點寫出來,所謂下文,無非就是對這一觀點的解說、闡釋和論證而已。有一次,李老師說:“你要將自己的觀點和想法錘煉成一句通俗易懂的口號。”說起來慚愧得很,直到今天,這一點我還是做不到。我那時年輕氣盛,對于與自己看法不同的論文和著作,有時不免信口雌黃。李老師很嚴肅地對我說:“煥忠,你讀一本書,關鍵是要學習其中的知識、思路和寫作方法,學習作者的優點和長處,在作者的啟發下展開深入的思考。”自那以后,我的文字中便沒有了批評、嘲笑和譏諷別人的語言。后來,我在專業期刊上連續發表了不少文章,這都要感謝李老師的指導。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李老師已不愿再與我談論學問,而是時常巡視他的稻田,驅趕他的鴨群,棲息在遠離名利喧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