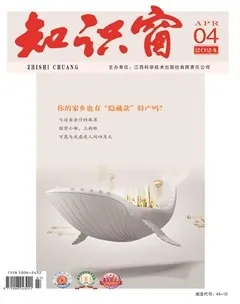行走真是一本書
劉紹義
常言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話一點(diǎn)不假。我喜歡讀書,更喜歡旅游,在“玩”中,我又學(xué)到了不少知識。
2024年春天,我應(yīng)朋友之邀,去了趟揚(yáng)州。當(dāng)我與揚(yáng)州的文友談到樂府《吳聲西曲》里的詩時,文友笑著告訴我,南朝樂府民歌中寫的揚(yáng)州不是現(xiàn)在的揚(yáng)州,而是今天的南京市。我驚得目瞪口呆,“江陵去揚(yáng)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聞歡下?lián)P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不斷流”……這里的“揚(yáng)州”竟然與李白“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lián)P州”中的“揚(yáng)州”不是一個地方!看來讀古人的詩文,是絕不能望文生義的。
南朝時,揚(yáng)州是今天的南京,而現(xiàn)在的揚(yáng)州,當(dāng)時稱江都,是南兗州治所,隋朝時才把江都作為揚(yáng)州治所。唐朝初年,又在今天的南京置揚(yáng)州,將今天的揚(yáng)州改稱邗州。到了唐武德九年,也就是626年,又將邗州改名為揚(yáng)州,所以701年出生的李白筆下的揚(yáng)州,就是今天的揚(yáng)州了。
2023年,我到武夷山水簾洞游玩時,見章堂澗路邊碩大的鵝卵石上刻著“漱石枕流”。我駐足良久,也沒想出個中原因。同來的解君脫口而出:“不是‘枕石漱流嗎,怎么寫反了?”
是的,山高水長,天地為房,山石為枕,以清流沐浴身心,以鳥獸為自己的伴侶,這樣的閑情逸致是“枕石漱流”的真實(shí)寫照。多少文人雅士為此留下了大量的篇章,陳壽《三國志·蜀志·彭羕傳》的“枕石漱流,吟詠缊袍”,朱熹《天心問禪》的“漱流枕石心無語,聽月煮書影自橫”。可是,曾幾何時,誰把這個詞作以顛倒,細(xì)細(xì)品味,不僅沒有影響詞性,反而讓人進(jìn)入一個更高的境界。
“枕石漱流”源自兩漢,成于三國,但用得最多的還是兩晉南北朝。讓人沒有想到的是,西晉才士孫楚一個失誤,讓漢語寶庫里多了一塊瑰寶——枕流漱石。“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dāng)枕石漱流,誤曰‘枕流漱石。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里這段話是說,孫楚想要隱退山水之間,有一次和駙馬王濟(jì)聊天,說自己要“枕石漱流”,結(jié)果一時口誤,說成“枕流漱石”。王濟(jì)奚落他說:“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楚隨機(jī)應(yīng)變:“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他這是借用了《高士傳》中許由在潁水之濱洗自己耳朵的典故,凸顯自己對隱逸生活的向往。
現(xiàn)在品品“枕流漱石”這個詞,確實(shí)要比“枕石漱流”有色彩得多。明代文人顏繼祖也曾說過:“無樹非臺還是佛,枕流漱石即為禪。”想想看,“枕流漱石”比“枕石漱流”境界要高遠(yuǎn)得多,這也算是孫楚歪打正著了。
與之相比,泰山的“五松亭”卻有些讓人啼笑皆非。當(dāng)年秦始皇封禪登泰山時,遇到了暴風(fēng)雨,于是就躲在一棵大樹下避雨。事后,秦始皇就把這棵為自己遮風(fēng)擋雨的松樹封為“五大夫”。后來人以訛傳訛,就把它說成是五棵大松樹。到了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有好事者還特意補(bǔ)植了五棵松樹,這就是我們?nèi)缃窨吹降摹拔逅赏ぁ薄?/p>
當(dāng)然,誰也無意去更改這些古跡,相反它們的存在,讓這些地方多了一層神秘的色彩,也增加了這些地方的文化內(nèi)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