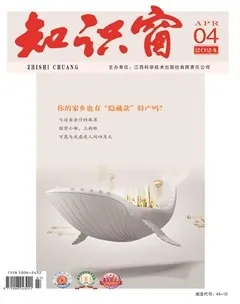古人筆下的海洋巨獸
康丹蕓
陸地上最大的非洲象可達四米高、六噸重,如此龐大的體型卻在很多海洋巨獸面前不值一提。我曾在海洋館里見到過長三四十米的鯨魚,游過來時跟一幢樓似的,壓迫感十足。不過,現實中的海洋巨獸和古人筆下的海洋巨獸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比如,戰國時期的列子在《湯問》中就曾記載,共工撞倒撐天的不周山后,女媧折斷鰲足以重立四極。后來,蓬萊和瀛洲等五座仙山在海上漂浮不定,天帝“乃命禺強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鰲即生活在海里的大龜或大鱉,能頂天立地,背負神山,海鰲之大遠超常人想象。
莊子也是寫海洋巨獸的一把好手,他在《逍遙游》里描寫過一種叫“鯤”的大魚,其體長“不知其幾千里也”。《外物》篇里,任公子用五十頭肥牛作餌所釣得的大魚更加夸張,切塊腌制成魚干后,居然能讓制河以東、蒼梧以北方圓幾千米的人們大快朵頤一番。試想一下,眼前出現這樣一只巨獸,那場景該有多么震撼。
自列子、莊子之后,古人在描寫海洋巨獸方面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脈,尤其在各種筆記小說中,有關海洋巨獸的故事層出不窮。如漢代劉歆著、東晉葛洪輯抄的《西京雜記》里有這樣一則故事:有一伙人在海上航行時遇到風浪,漂到了一個孤洲上。正當大家在孤洲上煮飯時,孤洲居然開始下沉了。眾人趕緊解纜離開,回頭才發現,“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云”。魚大如洲渚,著實令人瞠目結舌。
唐代戴孚所著的《廣異記》中也有不少關于海洋巨獸的文字,其中有一則寫道:“海中有山,周回數十里。每夏初,則有大蛇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蛇飲其海,而水減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十匝,然后低頭飲水。久之,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許,其山遂拆,蛇及山被吞俱盡,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能輕松吞掉數百米長的蛇,真不敢想象它有多大。
古人之所以如此熱衷于描寫動輒幾千米、數萬鈞的海洋巨獸,除了受“以大為美”的審美文化影響,主要原因在于對海洋的認識不夠,而他們又對海洋充滿了憧憬和想象,于是一些海洋動物和航海冒險故事,在傳播過程中漸漸染上了魔幻的色彩。而隨著航海技術的大力發展和與海外諸國交流的日趨頻繁,古人對海洋的認識逐漸深入,對海洋生物的書寫也更加真實。據《宋史》載:“至道元年十二月,廣州大魚擊海水而出。魚死,長六丈三尺,高丈余。”明代人謝肇淛《五雜俎》中所述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這些海魚的描寫就基本是真實的了。
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古人書寫海洋生物還是會夸張一些。這種夸張寫作模式實際上映射出來的是古代中國人直面危險的民族精神。心理學研究表明,對海洋巨獸的恐懼是深海恐懼癥的典型表現,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類集體潛意識。如唐代劉恂在《嶺表錄異》中寫道:“海,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說,固非謬也。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貨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復一年,便成斑白……設使老瞋目張喙,我舟若一葉之墜眢井耳。寧得不皓首乎?”航行海上,突然看見一只比船還大的巨魚之眼,能不把人嚇得白頭嗎?
但在這些強大到令人恐懼的海洋巨獸面前,我們的先祖并沒有因為害怕就悲觀地選擇退縮和逃避,而是以無限的勇氣、智慧和意志積極抗爭,奮發進取,展現出英勇慷慨的氣魄。比如《太平廣記》中記載,人們在海上碰到了一只巨大兇猛的海,激起的海浪差點將船掀翻,于是“及近魚,即鼓船而噪,倏爾而沒去”。人們抓住海畏懼鼓聲的弱點奮力反擊,最終成功趕跑了它。又有《寶慶四明志》云:“俗傳有漁人獲一巨蝤蛑,力不能勝,為巨螯鉗而死,今廟即其地,前賢多呼四明曰蝤蛑州。”其所述的是一海民與巨蟹英勇抗爭的事跡,即使最終戰死,他也受到了眾人的尊敬和紀念,其精神更是深深鼓舞著后來者。
正如李澤厚先生在《中國美學史》中所論,中國人高度肯定和欣賞自然界的強大力量,但又不會在其面前自慚形穢,相反,他們意識到了人有不被自然所束縛的偉大力量,是以同自然的力量相互比拼。海洋巨獸無疑是強大的、兇猛的,但也是可以欣賞、戰勝和超越的。古人筆下這些夸張到極致的海洋巨獸,實際上是他們對強大外力的詩意想象,更是自身頑強斗志和必勝信念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