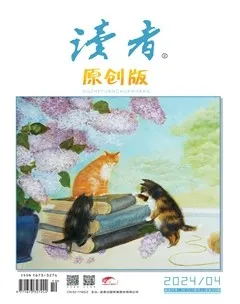水井
南在南方
外爺去世多年,只要我回老家,都要去老屋看看。山墻外的石頭縫里流出來的泉水依舊晝夜不息,那股勁兒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喜歡去外爺家,也喜歡那股泉水。外爺用銅壺燒水,銅壺放在火爐上,不一會兒就響起來了,再過一會兒水就開了,撲進火灰里。外爺說這是銅壺在發脾氣,我們都笑了。一壺喝完,外爺提著銅壺又去接水。為啥不用水缸儲水呢?外爺笑笑,沒說什么,只是繼續接水。
我艷羨他的泉水,是因為我們那兒缺水,喀斯特地貌,存不住水。奇怪的是,我們那兒的半山腰有個溶洞,常年有水。雖說缺水,但我們那兒也有水井,里面存下來的是雨水,看上去綠汪汪的。我們那個地方叫“干溝”,遠近的人聽了都要搖頭。
離家幾里外有個地方叫“蘭草洼”,那兒的半山腰是有點兒水的,但只有筷子粗的一股兒,是常流水。我聽老一輩人說,當年請人選了一個地方,挖了三丈多深的大坑,見著水后,就用方條石砌了起來。這口井打了一年多,架起了轆轤。據說當時鄉親們高興極了,有點兒像先秦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水是好水,只是離我們比較遠,解不了近渴。平日沒有東坡“聞道君家好井水,歸軒乞得滿瓶回”的雅興,我偶爾經過時看見有人打水,就要走上去討半瓢水喝。
那時的井邊總有很多婦女在洗衣服,沒有肥皂,用砸茸的皂莢或成筐的草木灰也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凈凈,一邊洗一邊晾,不然背濕衣服回家太沉了。架竹竿、拉繩子,周遭的石頭上也晾滿了衣服。太陽落了,我們這些小孩兒幫著收衣服,母親喊著要我們幫著拉一拉被面或床單,方便疊整齊。母親們和孩子們在夕陽下回家,帶著金光的背影,看著也是干干凈凈的。
有些旱季里我們總要為吃水發愁,起早貪黑地去找水。最發愁的是牛羊,只能順著河道,趕著它們去20里外的河邊,那里有一條地下河。牛羊像是聽見了水聲,隔著很遠就跑起來,踩著河道里的石頭咣咣作響,到水邊后,個個把頭埋在水里,久久不肯抬起。
好在這樣的時候不多,總是會突然下一場雨,水井中再次有水,盡管渾濁,可總能澄清。過了很多年,我們長大了,有一年縣里送來了許多水管,又派來技術員,把山上溶洞里的水引了下來,水嘩嘩嘩地流著。我站在新修的井邊發愣,祖父說了一句老話:“一人不進廟,二人不看井,三人不抱樹,獨坐莫憑欄。”我后來明白了,這話不是說人心叵測,只是注意點兒沒毛病。

到處都能看到水井,南方很多老井邊的青石被井繩磨出了豁口,長長的歲月痕跡留在了那里。李時珍認為每天早晨第一次汲的水叫“井華”,打水的吊桶滴下的水叫“沒有根”,說是能治病,不知有什么道理。不過,“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曹丕的這個法子確實好。
有一陣子,我在離家幾百里外的商州學著當皮匠,和許多年輕人住在一起。那時真是囊中羞澀啊,夏天的月圓之夜,我們坐在井邊東拉西扯,說要是有一個西瓜該多好,當然,有啤酒也是好的,可是什么都沒有。不知誰出了個主意,打了滿滿一桶水,月亮在水中晃來晃去,我們玩石頭剪刀布,誰輸了就喝一瓢水,好像也能“對水當歌”。這么多年過去了,井水沖進喉嚨的清涼感我依然沒有忘記,當然還有一肚子水響。
《莊子》里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貢路過漢陰,看見一位老農用水澆菜。老農抱著壇子,來來回回,費了很多力氣卻收效甚微。子貢建議他改用桔槔汲水,這樣打水用力少且效率高。老農覺得這么做是投機取巧,有點兒心術不正。子貢聽了頗覺羞愧,無話可說。
其實也沒啥羞愧的,抱甕澆園是老農自己的事情,隨心所欲就好。就像外爺一輩子提著銅壺接水一樣,他喜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