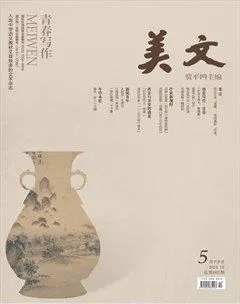記憶中的炊煙
炊煙是我迷戀和喜愛的東西,也是中國鄉村的一個獨特標識和符號。
故鄉的炊煙曾伴隨著我的成長,是我童年中一個很難以忘懷的東西。故鄉縷縷的炊煙升起,我也隨著炊煙的“生長”而逐漸地長大。
費孝通先生在他的《鄉土中國》曾明了地指出——鄉村與鄉土是中國社會一個最基本的形態,也是中國一個不可或缺的社會形態。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這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原始形態和基礎形態,炊煙自然也是伴隨著鄉土社會而產生的。
童年時期,我在奶奶家的大院里長大,低矮的茅草筑成的院墻,籬笆圍起的雞舍,木板搭起的狗棚……都是我童年時期的美好回憶。奶奶家在村南頭住,出了奶奶的院落便是一望無際的大麥田和橫排豎行的楊樹林,這是豫東平原鄉野的獨特景象,亦是我童年時期揮之不去的美好回憶。
童年時期,豫東鄉間滿是我金色的腳印,田野里、池塘邊、樹梢上,都曾充滿著我和小朋友們的歡聲笑語,都曾留下過我們銀鈴般的笑聲。
在奶奶家里,我度過了自己生命中最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那是我生命中的流金歲月。低矮的草房、甘甜的井水、盛夏的蟬鳴……時至今日,仍深深地刻畫在我的腦海里,成為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美好的回憶。
老家的炊煙是我難以忘懷的,那縷縷升騰起來的煙霧,似乎時時刻刻地縈繞在我的心頭,揮之不去。
在我的老家,廚房一般都喊做“灶火”,奶奶家的“灶火”很簡單,就是用秋收后還未晾干的玉米稈圍成的簡易的灶房,這樣有兩點好處——一來是節省了材料,不用再用磚瓦去砌筑,節省了很多的開支,二來是同樣可以遮風擋雨。雖然只是普普通通的玉米稈,但爺爺用繩子一捆扎,再用長棍上下各一道一夾,再用棉瓦一搭,便夾成了一堵堅固的“玉米秸稈墻”。無論刮風下雨,風不能穿透玉米稈,雨水也不能淋濕秸稈墻。在風雨的時日里,我常安心地躲在溫暖的灶房里,享受著那一份獨特的安寧。
爺爺在灶房里燒著火,燒火的材料也是來自大自然的饋贈——冬日的枯枝、落葉、被丟棄的樹根,當然還有一秋收獲而來的玉米秸稈。奶奶在案板前、鍋前有條不紊,不慌不忙地為她的孫兒做著飯,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是會沖出奶奶家的灶房,跑到外面,不為別的,就為看裊裊升起的炊煙,這是我在故鄉的時候一直很喜歡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在傍晚夕陽西下的時候,我一般都會跑到村子里地勢比較高的地方,爬到樹梢上,就為了看一眼夕陽夕照下的“鄉野炊煙迷霧圖”。
我對于故鄉的炊煙一直有著一種別樣的愛意,每當嗅到炊煙氣息的時候,都會讓我有一種難得的心安,無論我當時是焦慮還是其他。每當看到故鄉的裊裊炊煙升起,我便能感受到故鄉的一種獨特的訊號。
灶膛里的火明明亮亮地燃著,爺爺奶奶安詳地為他們的孫兒做著晚飯,炊煙順著煙囪裊裊升起,這一切都定格在我的記憶里,成為一幅永恒的,揮之不去的定格在我記憶深處的畫面。
而今,光陰晃晃悠悠地,一閃而過,我亦長大成人,出走在外,和故鄉似乎也開始有點漸行漸遠,但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總會想起我的故鄉,想起我少年時期的美好的時光,流星劃過,就如同那消逝的炊煙一樣,飄過,而今再難覓蹤影,但在夢里,在寂靜的夜空中,在漫天的星辰里,我又似乎再次看到了它的身影,聞到了它的味道,再次相遇——我記憶中的炊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