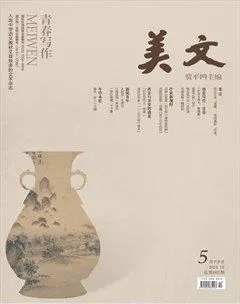年輕的魯迅:世界會回應那個堅持理想的人
王僡蘐
提起魯迅,大家第一時間會想起的大抵是留著不加修飾的短發,蓄著胡須,表情嚴肅,為啟蒙中國人嘔心瀝血的中年魯迅先生形象。不過,年輕的魯迅先生是什么樣的呢?退學、失業、30歲找不到工作,等等,這還是我們熟悉的魯迅先生嗎?
家道中落的童年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家。
魯迅小時候家境尚可,他在自敘傳略里回憶說:“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里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并不很愁生計。”這就是他出生那時候的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貴之家,但多少稱得上現在的“中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是一位進士,做過正七品官員。放到現在相當于處級,和縣長一個級別。周福清也確實曾在1875-1878年擔任江西省金溪縣的知縣,現在在金溪縣也能看到他當年頒布的告示石碑。
可惜,魯迅祖父的官運不好,遇到了一位苛刻并且經常彈劾下屬的領導——兩江總督沈葆楨。沈葆楨1878年給光緒皇帝上了個奏折,一口氣彈劾了自己手下12個官,魯迅祖父也名列其中,于是,他這個知縣只做了三年便被調職成內閣中書——是個京官兒,但是錢少事多離家還遠。
魯迅的爸爸叫周鳳儀,中過秀才。不過光是中秀才當不了官,還得通過鄉試。可惜的是,周鳳儀考了一年又一年的鄉試,一直沒上岸。
雖然爸爸的事業差一些,借著家底和祖父的為官的威望,魯迅家的生活本來也是非常不錯的。然而,在魯迅十二歲那年,他們家突遭橫禍。
清朝于1893年舉辦了一場鄉試,浙江省的正主考叫殷如璋,魯迅的祖父周福清與殷如璋是同一科取中的進士,有同年之誼。親友家中有要去應試的秀才的,就托周福清去向主考殷如璋行賄。殷如璋性格很剛正,當場告發此事,諭旨明確要求“嚴行審辦”。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審訊時的情形,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里是這樣說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并不是神經病,歷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事情弄得不可開交,只好依法辦理。”
折騰了一圈兒,周福清免去了死罪,仍然被判了無期徒刑。周家地位一落千丈,魯迅和家人們一夜之間,從官員的家屬,變成了罪犯的家屬。
屋漏偏逢連夜雨,祖父那邊的情況已經糟糕透頂,魯迅的父親周鳳儀偏偏又病倒了。周家花了大價錢請了紹興城里頂有名的中醫來治病。魯迅和周作人甚至一起按醫生的要求捉過“同巢原配”的一對兒蟋蟀來充當藥引,各種奇奇怪怪的法子都用過了,也沒治好父親的病。
兩年后,年僅三十六歲的魯迅父親過世。家里的四五十畝水田,為了給父親看病,給祖父擔負獄中支出,全部都賣掉了。周家從一個中產小康之家,變得一窮二白。
魯迅后來孤單地在《吶喊·自序》中寫道:“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家里沒錢,生活困頓,面臨著世人的惡意。為了逃開這一切,17歲的魯迅選擇出門遠行。
輾轉的求學之路
魯迅于1898年離家去了南京,到一位周家遠房叔祖父在那兒當老師的江南水師學堂上學。正是在這個時候,魯迅改了名字。魯迅原名周樟壽,周樹人這個名字是后改的。改名的理由是當時那個年代,江南水師學堂初辦,讀這個學校在社會上會被人看不起。遠房叔祖父覺得魯迅讀這個學校挺丟臉的,不能用家譜里的名字,就給魯迅改成了周樹人這個名字。在水師學堂沒待多久,魯迅就另行投考了更吸引他的礦路學堂,錄取后他轉入了礦路學堂就讀,專業主修地質學、采礦。沒錯,魯迅的大學本科專業是挖礦,他還曾經下過南京觀塘煤礦象山礦區的礦井去學習。
1927年,魯迅應邀到黃埔軍校去講《革命時代的文學》,他說:“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里聽文學。其實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
魯迅這話不是吹噓,他開礦掘煤學得相當不錯,以一等學生成績畢業,并獲得了國家的公費赴日留學的資格。1902年,魯迅前往日本,在弘文學院(留日預科班)學習了一段時間順利畢業后,1904年,魯迅決定去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此時他23歲。
之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在仙臺醫學院學了一年半,魯迅經歷了著名的“幻燈片事件”,意識到學醫救不了中國人。1906年3月,魯迅告別醫學院里非常關愛他的藤野老師,從醫學院退學了,決心以文學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此時,魯迅25歲。
退學后的艱難生活
魯迅媽媽魯瑞特別憂心魯迅的婚事。我們可以想象一下,25歲的魯迅,家境不好、沒工作、留學退學沒拿到學位……未來前途堪憂。魯瑞焦慮地找人給魯迅介紹了個沒文化的女孩兒叫朱安,安排他們結婚了。這段強行撮合的婚姻沒有任何愛情可言。
1906年9月,在國內剛結完婚,25歲的魯迅很快就選擇和弟弟周作人回到日本。弟弟周作人學了土木工程專業,魯迅則不上學了,貫徹自己“以文學為終身事業”的想法,每天在家自學德語研究翻譯。當時,魯迅學德語常常學到半夜,很是用功。26歲那年,魯迅又學了一段兒時間俄語,學了不到半年,因掏不起每月6元的學費無奈放棄。
在日本這兩年,魯迅同時也和朋友們試圖辦《新生》雜志,很遺憾地創業失敗,雜志胎死腹中。不過,他倒是在河南留學生主辦的《河南》雜志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其中包括《摩羅詩力說》這樣功底非常深厚的學術論文,充分體現出魯迅的思辨能力與文學素養。遺憾的是,這雜志很快就被清朝駐日本公使以“言論過于激烈”為由停掉了。
1909年8月,28歲的魯迅終于回國了。他在好朋友許壽裳的介紹下,獲得了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杭州師范大學)任教的機會,做生理學和化學的教員。但是在這所學校,魯迅沒有獨立教學的機會,實際工作是給日本老師做翻譯。后因為該校校長換了個迂腐之人,魯迅選擇辭職。
1910年,29歲的魯迅受到老家的紹興府中學堂(今紹興一中)的邀請,就任該校的生物學老師。干了沒多久,魯迅又辭職了。
1911年,30歲的魯迅變成了無業人員。他曾經動過“想去一個書店做編譯員”的心思,卻沒有通過那家書店的考試。沒有收入,雪上加霜的是,他還得幫扶弟弟,每月都要給還在日本留學的弟弟周作人打錢。一直到辛亥革命爆發,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邀請魯迅來教育部就職,魯迅的生活狀態才變好起來。而直到1918年,我們熟悉的魯迅第一篇小說名作《狂人日記》才刊載到《新青年》雜志,此時魯迅已經37歲。
梳理魯迅年輕時的經歷,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如果把魯迅當時的人生經歷與現在的時代環境相對應,魯迅著實是一位非常有個性、堅持自我的年輕人。
正如前文所言,魯迅出生時是縣長的孫子,沒幾年縣長祖父就坐牢了,父親生病35歲就去世,家里從中產變成家徒四壁,魯迅的人生開局并不好。
在這樣家庭背景下,除去和朱安的包辦婚姻,魯迅的所有大的人生選擇,卻仍舊都是依自己的心意和興趣走的。他兩次退學,兩次辭去穩定工作(注:嚴格來說是三次,魯迅還因張勛復辟而短暫辭任教育部的工作,亂平后返部),他始終在為自己的理想與信念生活,不因生活的瑣碎與艱難有絲毫妥協。
在這個物欲高漲,人人都很容易陷入焦慮的時代,我們不妨和當年的魯迅先生一樣,降低一些來自外界的焦慮感,問一問自己:“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畢竟,人生的終極追求永遠需要你去望向自己的精神世界,只要你在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在活成你想要成為的樣子,這就是屬于你的完美的人生。
而其實,到了最后,一心不亂地不為外界所動,堅持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往往才會真正取得巨大的“成功”。魯迅先生當然是其中一例,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巨量寶貴精神遺產中一項尤其值得我們深思的內容。在抬頭望月與俯身撿拾六便士的抉擇中,總得有人選擇奔赴心中那輪代表理想的明月。正是這樣的一群人里,誕生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圖騰與文化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