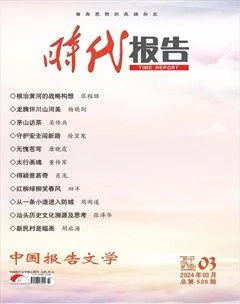星辰是這樣閃爍的
張國寶 羅賢
屬于他的水稻世界
我國水稻良種培育人管仁欣,他僅僅初中結業,幾乎是一直在業余進行著此項科研,最后卻大獲成功。他的米質優異的粳稻后季稻優良品種選育成功,他培育出的“雙豐系列”晚季水稻全國14個省市推廣種植,累計達2332.8萬畝,增產的稻谷若按彼時奉賢50萬常住人口計,可以足足吃上12年……
2023年9月16日早上,我如約趕到他家。在解放新村踏上他家樓梯時,不禁極為吃驚且懷疑自己的眼睛,40年前的老公房,可謂“老破小”,樓棟之間空域狹窄,綠化稀少,破舊的樓梯踏步板裂縫如齜牙咧嘴……
1973年10月21日的《文匯報》,以《育種“專家”》為題的報道提到:“想收千斤稻,要種‘雙豐號。”這是廣大貧下中農對奉賢縣莊行良種場管仁欣辛勤培育后季稻優良品種“雙豐一號”的贊語。一天,他走進一塊“農墾58”品種的稻田,仔細觀察時突然發現了幾個成熟早、桿子粗、穗頭大、谷粒飽滿的穗頭,就一穗一穗地把它們剪下來放進背包里。這一年,他步行了半個月,跑了4個公社,先后收集了1000多個稻穗。接著,他在場里開會,把1000多個稻穗拿出來,請領導和職工一起鑒定。大家經過認真比較,共同鑒定了370個穗頭。管仁欣將這370個穗頭曬干后,一穗一穗編上號,裝在紙袋里掛起來,一冬一春檢查了好幾次。第二年,場里成立了科技小組,試種了370個穗頭稻種。從浸種、移栽一直到施肥、治蟲、收割,管仁欣始終和大家戰斗在一起。然后,再從370個種穗中挑中了4個優良穗系。第三年,4個小區繼續實驗,最后從中挑選出一個理想品系,這就是“雙豐一號”。他又將“無芒沙粳”與“矮腳南特”雜交。培育出“向陽一號”至“向陽四號”,又從“向陽號”中選育出“矮早粳”;將“科睛三號”與“桂花黃”進行雜交,培育出“科花一號”早稻優良品種。還有水稻與稗草雜交、糯稻與粳稻雜交。他為此苦戰整整28年。
為了更深了解并理解其中的專業知識,我購置了很多與水稻繁育相關的書籍及講義,意通過研讀與學習,讓我能更深地走近他與水稻的世界。
17歲立志當育種專家
1956年,早春,東風拂揚。
傍晚時分,位于上海縣(現閔行區)馬橋鎮吳會村西稍,頗顯氣派的兩棟橫排相距的三開間瓦房,瓦房后有一個牛棚,棚內那頭壯實的水牛正大口咀嚼著草料,門口后一側,17歲的管仁欣正手握大鍘刀不停地把一捆捆稻草鍘成短短的草料,棚內漾起陣陣稻草清香。
“喂,知道哇,這次蘇州農校辦培訓班,聽說畢業后就是國家干部。你去考嗎?”村西本族的阿介,年齡與管仁欣相仿,不知何時鉆進了牛棚,右手卷成個喇叭狀神秘兮兮地說。
“喔,去的!去的!”管仁欣驚喜地說。
他的人生幸運又有些曲折。祖父繼承了50多畝耕田,父親又攢錢買下7畝薄田。父親把20畝田出租,其他40畝自家耕種,父親與母親兩人每天晚上收工回家,總是累得直不起腰,父親篤信農民唯有伺候好莊稼才能過日子。管仁欣從小學4年級開始學習成績奇好,擔任少先隊中隊長。初中在馬橋鎮念書,每天來回要走16里路。但管仁欣學習極為認真,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并擔任班級學習委員。念完初二,父親鐵了心叫他停學。然而在田地間,他仍是得力干將,耕田耙地的農活都會干,挑重擔也如一個大漢子,但他的心仍充滿憧憬。“我得出去干大事!”他暗自想。
管仁欣是幸運的,報名時在所屬的鄰松鄉政府,那位40多歲的干部對登記的青年說:“農民家孩子都是靠勞動吃飯,讓他們去吧!”青年爽快地給他們開了介紹信。
考試那天凌晨,管仁欣悄悄起身出門,到官路上跟阿介會合,去設在閔行鎮上的縣農業局考場參加考試。管仁欣發揮優異,數學是他的超強項,按照初中畢業程度出的試卷他考了近80分;另外一門科目是語文,他最近看的《青年報》上的一篇文章,恰巧與考卷上作文命題相近。
發榜時,他名列其中,遺憾的是阿介沒考中。
可父親堅決不讓他去,說:“讀書讀書,都讀書去了誰在家里種田!”母親雖然一直支持他念書,但在家里作不了主。管仁欣在牛棚里邊流淚邊鍘牛草,事情鬧得姐夫都過來了,姐夫是小學教師,對岳父說:“考上不容易啊,讓他去吧!他個子小,干農活吃力。培訓班不要書費學費,國家還發生活費。”
父親最終同意他去念書。
管仁欣肩上背著用草繩捆緊的被子,腳上穿著大腳趾破口的鞋子去了。“我不管,我是去念書的!”他笑說。身上沒一分錢,縣農業局干部專門陪送他們去農校。
培訓班為期3個多月,需要學習《栽培學》《植物學》《土壤學》《農業氣象學》等8門課,老師上課速度如同灌水一般。盡管學習條件一般,課本是由老師的講義復印裝訂的。可這所1907年創辦的江蘇省立農校,畢業的學生中有5位后來分別成為我國花卉學、果樹學、家蠶育種學、蠶體病理學、昆蟲學的先驅,并有多位成為農林植物學、微生物化學專家。
許是受上述大家們浸潤,在寫畢業總結時,管仁欣居然揮筆:“我立志成為水稻育種專家!”
曙光村里冉升理想之光
培訓結束后,大多數人都被分配到不錯的工作崗位上,管仁欣在內的200名學員大多被分配到省農業廳、農業研究所,還有的被分配到其他省辦農業中專擔任政治教師。他和10多位同學分配到奉賢縣農業局,其中一位女同學黃式申,金山縣朱涇鎮人,出身名門,后來與管仁欣喜結良緣,這是后話。
可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要成為專家不啻天方夜譚。希冀與現實水火不容——在所屬松江專區的畢業生分配會議上,原專區農業局艾局長的山東普通話聲嘶力竭,極富激勵:“你們中將來一定會出現一批農作物栽培專家,出現一批果樹栽培專家,還有如蘇聯米丘林那樣的果樹嫁接大專家……”而蘇州農校教導處主任徐國楨,1944年獲金陵大學碩士學位的副教授的話如一盆冷水:“3個月的培訓,對于你們今后的工作,僅僅擺了個渡,而且是個‘野渡,你們掌握的知識,只適宜在農科推廣推廣。”
奉賢縣農業局專門設立4個農科推廣站,每個站負責所屬區四五個鄉。當時是小鄉體制,一個鄉轄四五個行政村。管仁欣和賀連云、楊樹林等3人被分配到南橋區推廣站,推廣站設在曙光村,借住在村中破舊房子里。他們都是外縣人,40多歲的站長是奉賢人,性格憨厚直率。他在會上音階拉高八度:“我們的工作就是搞好農業科技推廣……”
管仁欣常常說起米丘林,“小米丘林”也是他后來在整個農業局被大家熟知的外號。
“蘇聯的米丘林、美國的摩爾根,他們能夠成為大科學家,我為什么不行?!”他時時在鞭策自己,“不,我自學一輩子知識足夠了吧!”
上班的第一個周末,站里的其他3位同事周六晚上已經回家。管仁欣周日清晨出門,乘公交車輾轉勞頓5個小時,來到市區福州路上全市最大的新華書店。
管仁欣要買下米丘林遺傳學方面和摩爾根的細胞遺傳學方面的書。米丘林成功地將北緯30度的果樹嫁接到北緯50度的果樹上,除此之外,他嫁接的許多果樹都獲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管仁欣要買下這些書,要把“野渡”變作大海上的勇敢遠航。當他已經買了四五本書時,又發現《中國水稻》這部大著書非常有價值,愛不釋手。可看那價格,倒吸一口氣。他走出書店,在街邊躑躅好一陣,咬咬牙下決心買了下來。
為了節省乘車錢用來買書,他三四個月才回家一次,回家總是把每月工資中近3成交給母親,以此資助弟弟妹妹們上學念書。
工作繁忙且艱辛。奉賢與整個市郊一樣,水稻種植由過去的直接撒播谷種改變為秧苗移栽。移栽的分蘗大而產量高,可是病蟲害多,防病治蟲極為關鍵,可當時我國農藥制造業落后,農藥價格貴。除了水稻,棉花、三麥和油菜全都提倡合理密植,大幅度提高了產量,致使防病治蟲壓力極大。所以,要緊日子里他們必須天天觀察所轄鄉農田里的莊稼,還有水稻生長期不同的灌水厚度、棉花急需施階段肥等等,農事上都需要他們拿出方案,由鄉領導指揮實施,同時還要匯報縣農業局,縣農業局匯總資料上報縣政府領導。
然而,奉賢的地域大多由大海沖積成陸,因而處處見河流,婉轉曲折的小河,河面頗寬的中等河流,還有人工開掘的運河,而被奉賢人稱為“養魚溝”的一條條小溪,遍地都是。一次下午,他們在樹浜村,觀察三麥的生長情況,傍晚回來走了整整2個小時,還沒有走出河流的“包圍圈”,最后只能從一條水深半腰的河中涉水而過。他們還經常參加合作社的勞動。管仁欣初二停學扎實務農的一年時間,讓他在干農活上成為一把好手,農民和局里領導經常表揚他。但那一次,竟差一點兒害他丟了性命。大暑天的一個下午,他們給村里一個合作社的棉花噴農藥,棉株很高,直至胸口,天氣十分悶熱。管仁欣和兩位同事噴完一桶農藥后到河邊配灌藥液,不禁脫了衣服跳入河里去去暑氣。清洌的河水涼爽舒服,可腳下河床陡然走深,足有三四米。管仁欣不會游泳,慌忙雙手亂拍打河水并喊救命。不一會兒,身子往河底下沉。此時,賀連云、楊樹林正游向對岸。還好被岸上碾米廠的老楊看見,奔過來跳入河里把他救了起來。
工作條件艱苦,吃飯也得來回走4里多路到鄉政府食堂用餐。
如此不堪,他卻說那是天堂一般的生活。白天積攢實踐經驗,晚上學習理論知識。
10月的一天早晨,只見他站在一塊麥田里頗似“范進中舉”情景。那是他邁出異想天開第一步:一個月前的星期天,他到南橋鎮上自己掏錢買了嫁接用的切刀、鉗子、器皿和花盆,回來把放在熱被窩中保溫催發了芽的數十粒小麥,以一個型號為母本,另一個型號為父本,進行嫁接。嫁接的麥苗不僅全部成活,而且一派生機勃勃。
一心鐘情水稻科研事業
1957年冬季征兵開始,他積極響應局領導號召報名參軍,體檢合格,兩天后將穿上軍裝到部隊歷練。他無比渴望,那里是大展人生宏圖的地方。他匆忙把自己的30多部書,還有自己訂閱的《農業通訊》雜志等,打包放在一個布袋里,急急送到馬橋鎮上一個親戚家,寫信給父母請他們去取。然而第二天,局辦公室主任來電話給他:“小管,到部隊去的人員已經滿額,領導決定你留下來做原來的工作。“好的!好的!”他連連答應。
然而倏然3個月過后,他又得去“流浪”——得益于他們10多位同學工作能力見長,縣農業局決定改變推廣站模式,為每一個鄉配備一名農技員,他被分派到胡橋鄉。胡橋鄉還不通公路。他乘水上交通,一只響著“突突”柴油機炸聲的小木機船,自南橋鎮余慶橋碼頭出發,往西往南又往西往南,逶迤航行3個小時才到達。在鄉政府,分管干部看到他不禁有所失望,“這么小年紀哇”。
他工作的地方在胡橋鎮北約2里路地方的窯橋村,約三四十戶人家。村長領他到了村東頭一戶農民家,那是一戶極為殷實的人家,夫婦倆都40多歲,兩個女兒,待人不無親熱親切。村長對雙方做了熱情介紹,更是特地囑咐夫婦倆,一定要為技術員搞好伙食。
工作不多久的管仁欣簡直成了半個科技副鄉長(該年下半年鄉政制改為人民公社),對于全鄉農作物的農事安排,都是由他與鄉政府指定的專職植保員商量,拿出建議方案,報鄉政府主管領導。肩上壓重擔,他得幾乎每天對全鄉的農作物作抽樣觀察,極為仔細。除此之外,還要按照局里和鄉里要求,指導種植兩塊試驗田,各兩三畝,分別為水稻與棉花。農民講究看得見摸得著,鄉里領導號召做事情,可是怎么做?便帶了村長與合作社的干部來觀看“先走一步”的試驗田,那是立竿見影的。為了種好試驗田他必須付出十二分努力。棉花苗移栽時,他特地搞了一根劃下等距離記號的繩子,要求社員嚴格按照記號栽種。水稻秧田的耕翻,深度必須是30厘米,他在現場用尺子多處測量,水田的耙田他親自干……雖然這些日子艱苦辛勞,但他感慨自己人生收獲頗多。如合作社老金社長,從互助組組長干起的,身為老黨員,一心為集體的精神讓他折服。在確定試驗田時,老金社長就告訴他,這兩塊田肥力足。8月的一個晚上,滂沱大雨下了4個多小時,他擔心稻田積水,撐著雨傘,打著手電筒趕到試驗田,然而老金社長已經在田埂上用雙手扒掉了排水口前堵塞的亂草。
“科技副鄉長”干得風生水起。鄉里的領導會上布置工作時常常講“農業局的小管怎么說怎么說”,那兩塊試驗田更不含糊,水稻與棉花單產預測比通常的高出兩三成。《奉賢報》有個記者叫陳肅勤,聞訊后乘了小木機船趕來采訪,拍下新聞照片又寫了文字報道,發表于該報,管仁欣一夜名聞全縣。快秋收時,市農業局舉辦農業大豐收展覽,縣農業局要送標本過去,選送的同志特地趕到他的試驗田,拔了好幾大把水稻,放河里洗干凈了根須部分,欣然而去。
他沒有顯現春風得意。農業副鄉長趕來,問:“小管,我們的試驗田水稻單產報多少?”
“我測算過,畝產800斤多一些。”他說。“可人家報2000斤啊!”副鄉長說。他說:“我們只能這個數。”
那天下午,發生了一件令人尷尬的事情。他去試驗田里的摘棉花,幾個40歲上下的婦女嘰嘰喳喳地笑說:“小娟前世修來的福份呢!什么技術員寄飯,原來是村長介紹的上門女婿啊……”
管仁欣怔住。
“哪跟哪啊!”他簡直手足無措。
小娟,雖身形柳條卻很結實,農業勞動一把好手,小學畢業,特聰明。管仁欣在她家寄飯,她那雙烏黑的大眼睛總是含著笑意,尊敬地叫他仁欣哥,管仁欣對她也如對待自己的親妹妹一樣,別無他意。
那一晚上,他天快亮才入睡。第二天清晨,他急匆匆趕到已經是胡橋公社的機關,給分管的公社副書記老陳匯報了這個情況,并提出不再吃寄飯,要趕到公社食堂吃飯。陳書記同意了他的請求。
將水稻科研作出成績
1964年2月一天,在奉賢縣農業局出現一場非同尋常的談話。
局長說:“小管,今年的糧食作物三熟制種植試驗,關系明年能不能全縣全面推開。砂北大隊徐家村生產隊的徐壽均隊長很得力,各方面基礎都不錯。局里這次特地派你去農技領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啊!個人有什么困難盡管提出來,局里給予幫助解決。”
“請局長放心,我必全力以赴!”他如軍人一般霍然站起身,話語鏗鏘。
縣農業局此番盡銳出擊,管仁欣一行5人,一位擔任蹲點隊隊長,還有4位是上海農學院畢業生,另外一位則畢業于七寶農校。而此期間,分管農業的南下干部副縣長侯尚進,多次騎自行車來試驗田查看,盡管他是個“外行”,可總是在田頭激勵大家:“好!這個長勢很好!那個也很好!”
10個月后,試驗田結果終見分曉:面積21.435畝,平均畝產1962.4斤,其中大麥畝產304.4斤、早稻畝產843.4斤、后季稻畝產814.6斤;同比去年,比稻麥兩熟畝產增62%,比綠肥田雙季稻畝產增24%。并且,奉賢糧食三熟制試驗種植單產居市郊之首。
彼時,以市郊350萬畝糧田計算,三熟制生產若僅僅以畝產增300斤計算,一年可增產10.5億斤,而10年可累計增產105億斤,一個千萬級人口城市由此增加2年多糧食支撐。市科委、市科協與市農業局組織市縣農技員到錦江飯店撰寫糧食三熟制高產經驗,以此指導下年全郊區普遍種植。《上海郊區糧食一年三熟制生產經驗》一書于1965年3月出版于上海科學出版社,其中匯集了郊縣7位農技員撰寫的成功經驗,而管仁欣的文章置于7篇之首。
在砂北村種試驗田是一場苦戰。試驗田早稻秧苗播種時,恰逢妻子生產,管仁欣為了撒播谷種顧不上去醫院。因為他曾到松江參觀學習陳永康的種植水稻技術,其中包括撒播谷種,回來練出功夫——每平方厘米3粒谷子,必須不多不少,這件事他必須親自完成。他上午完成了試驗田播種,下午搞雜交水稻播種,一刻也沒有停歇。管仁欣從1960年搞起水稻雜交,有秈稻、粳稻和糯稻。雜交水稻播種不同品種的種籽一粒也不能混淆,他特地做了一個精致的無底籬笆筐,一個品種種籽撒播一個籬笆筐內,然后再用鑷子,把那些撒播稍疏密不均的調整勻稱,細致到可以說是繡花針功夫。下午直至太陽快下山才完成。管仁欣把其他事情托付給徐隊長,腳上泥土還沒洗凈,就拔腿往縣醫院奔。
“農業科技工作很辛苦,與農民種田沒多大區別。分配來奉賢的農學院農校的畢業生,后來大多調走去當教師什么的了。我們培訓班出來的,除了其中到部隊的,同樣剩下不多,有多位干脆回家種田了。”他說,“也有堅持不懈的,極少。”
1959年,縣里成立農業研究所,他調入。研究所置于縣農場內,農場共100多畝耕田,共50多位職工。他的工作一是為農場領導提供全場農作物防病治蟲方案,包括其他主要農事方面的建議;二是專職于水稻和三麥的良種科研培育。1964到1965兩年他在砂北村搞三熟制,同時辟建“自留田”繼續水稻三麥良種科研。
黃式申剛分配來的時候在縣農業局當技術員,1958年因機關干部調整而下鄉勞動,又經輾轉后調江海公社信用社工作。她小個、丹鳳眼,美麗的荷包嘴,智商很高。可她因神經衰弱,晚上難以入睡,導致身體虛弱,最后竟不能從單位集體宿舍走到江海公社機關食堂用餐。當時管仁欣的單位距她所在單位都在南橋鎮地域上,相距僅約2里路。她便托人轉告老同學管仁欣,請她幫忙從農場食堂買了飯幫她送來。不久,兩人墜入愛河。半年后的1961年10月1日,他們結婚了。結婚儀式很簡單,到公社機關打了結婚證,買了2斤糖果在各自單位分發了一下,然后叫上雙方家人在一起吃了頓午飯。
結婚后,管仁欣更是一心撲在科研上。他為充實自己的大腦不斷學習,參加縣機關夜校語文班,通過學習取得高中語文單科畢業證書;市科協舉辦遺傳學講座,他都一次不落地趕到市科學禮堂聆聽;他加入了市遺傳學會、市種子學會、市作物學會、市農藝學會……他的良種培育科研一路向前。
1965下半年,縣農業局成立莊行良種場,旨在為全縣主要農作物做好種子提純復壯,以減緩作物的退化。同時,全縣引進的農作物新品種在此地先行試種,然后全縣推廣種植。整個良種場200余畝耕田,80余位職工。農業局派他去當技術員,莊行良種場一年得提供全縣種子10萬斤,他的責任更加重大。所幸,他在做好場長“農事參謀長”的前提下,也可名正言順從事良種培育科研。
整個良種場技術員只有他一個,因此他的工作很忙,他每年參加生產勞動200天以上。甚至良種場的廁所臟了他都會去沖洗,場地臟了他都會去清掃。1972—1973年兩年時間,他的肝炎病情嚴重,可醫生每次開的病假條,他都沒有交給領導。他常常一邊勞動,一邊身上虛汗直冒,但他不顧這些,病倒了也不吭一聲。面黃肌廋的他自己制作個煤油爐,用于熬藥與晚上燒點菜粥作夜宵。為了工作為了科研,他甚至犧牲自己的節假日。場領導經常命令他回家休息,但是他仍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領導心疼他,局里決定給他發放20元補助,讓他用于改善營養,早日恢復身體健康,可他堅決推辭。
10多年里在莊行良種場搞水稻雜交和小麥雜交,總是從上午一直搞到中午1點,才去食堂吃飯。有幾次下起雨來,為了保護好雜交水稻,他就把帶來的雨衣蓋上去,不顧自己身體淋濕。科研探索搞水稻和稗草雜交,為了弄清稗草的開花時間,他和3位職工4天4夜輪流值班查看,終于發現稗草開花于凌晨2點至3點。
…………
這樣的場景比比皆是。
莊行良種場率先搞早稻尼龍培育秧苗,是一項大幅度提高早稻單產的創新。可是播種時間提早至3月中旬,而場里經濟不寬裕,無力購買長筒雨鞋,他只能光腳在冰冷的水田里帶領大家干活。谷子播種后,每天上午氣溫升高時需要打開每個尼龍棚兩端放風,傍晚,又要把放風的尼龍棚兩端再拉下來。此般操心活他自己干才放心,每天早晚插在水田里的雙腳凍得通紅。一星期后“倒春寒”,夜里一場大雪,第二天早晨他帶幾個年輕人光腳站在水田里掃雪……
要開始早稻播種了,卻缺少耕翻秧田的人手,他親自開手扶拖拉機干,10多畝田精細耕翻得整整一天。場長王金發見了,急忙奔過來,連連擺手,叫喊著:“危險!你不能干!你不能干!”秧田左側田岸數米高陡直的下坡,如果操作不慎拖拉機翻下去后果不堪設想。他從拖拉機座位上跳下來,雙手抓著操縱柄,兩腳跟著前行。“沒事了!這樣沒事了!”他沖著場長喊道,但他這樣干簡直會累死。
是年秋,全場100畝水稻已經稻穗灌漿,再有一個半月左右可獲豐收,他的10多個雜交水稻同樣長勢良好。但這兩天突然稻飛虱爆發,每一畝達到數萬只。那是第三代晚季水稻稻飛虱,接下來以至有第六代爆發。鬧不好百畝水稻將會歉收,更何談外供提純復壯的種子。但目前場里沒有農藥了,而百畝棉花需要施的棉鈴肥也得趕緊購買。上午,他擅自拉了行政干部周洪才,搖了場里那條可載重一噸的木船去莊行鎮購買。老周50多歲,不太會撐篙,管仁欣叫他“頂住”,不讓船首撞岸邊,他自己搖船水平搭漿,令人擔心的是他還不會游泳。他剛剛搖動幾下木櫓就打飄了,而且一個趔趄跌倒,差一點滑出船外。“不行!你這樣要出大事的!”老周大叫。“什么不行,行的!你干好你的事!”他大吼。把長約4米的木櫓重新接到鐵榫上,又搖起來。到莊行鎮水路6里長,其中主要航行于潮汐很大的巨潮港,只能逆水行舟……那天他們購了農藥化肥回來,已經是晚上月上東山,但萬般慶幸的是安然無恙。
翱翔在自由的水稻王國
深秋的清晨,莊行良種場莊稼地上薄薄一層水氣霧,在一股微風吹拂下消逝。他習慣早起,洗漱過后,走在田埂上。眼前的百畝水稻品種為“農墾58”,那是我國從日本引進,是近些年上海市郊種植面積最多的品種,可目前已經出現退化。水稻的一個品種,優勢壯盛期一般6~8年,出現退化后單產將逐漸降低。
望著稻田,他不禁沉思,腦海中竟出現了他和黃式申手拉著手,站在推開的窗子前賞景的情景。窗外院子里,那棵梨樹紫紅的花蕊潔白的花瓣,滿枝簇擁。“農夫,我學的農學知識都還給老師啦。可我感覺,你的水稻良種培育選育與雜交兩條腿走路很有價值……”黃式申說。
黃式申是有主見的,他想。然后習慣性地抬頭遠眺,突然回過神來,他收住將跨出的右腳,目光凝視前面。突然看到一棵異樣稻穗,身影很大。他搖搖頭,定睛一看,然后脫了鞋襪,快速闖入稻田。
世界的一切是動態的,人類種植的作物同樣。它們通常表現為退化,但同時極個別的朝著優勢方向變化,植物學上稱變異分離。
“好一棵優勢株啊!”他激動萬分。陳永康、洪群英和洪春利,他們同樣是先發現優勢株,然后精心繁育,在全國多個省市推廣種植,并獲得高產。他仔細數了數整穗谷粒,100多粒,比通常多10余粒,并且谷粒飽滿。更喜人的是已經成熟,早熟足有10天。“過了立秋收秕谷”,說的是后季稻秧苗移栽日期一定得在立秋時令之前,否則歉收乃至絕收。他又走上田埂,邊行走邊不斷查看前面每一塊稻田,場內的水稻田里有類似優勢株上百棵。他顧不上吃飯,回去拿了工具,趕來走入水稻田里。他把那些優勢株一穗一穗用剪刀剪下來,分開放置在一個個紙袋中封閉好,接著裝入一個布袋。
趕回的路上他想,附近公社種的水稻中有這樣的優勢株嗎?他把想法告訴王金發場長,老王很支持他。接著就有了前述《文匯報》報道的內容,他10多天跑了4個公社的水稻田。
《文匯報》報道的還有一段:“奉賢縣地處東海前哨,有10多萬畝鹽堿地。‘雙豐一號耐不耐鹽堿?星火農場用‘雙豐一號與其他20多只品種的水稻一起試種,這年由于鹽堿地返鹽嚴重,其他品種都漸漸枯死了,唯有‘雙豐一號長得清秀挺拔,郁郁蔥蔥……”
成功的喜訊如春雷滾過奉賢上空。
1971年6月調來奉賢的縣委書記王杰,已經注視著這場“大戲”展開——該年全縣種植“雙豐一號”5400畝,平均畝產729.6斤,同比增約8%。1972年全縣種植4萬畝,又呈現一派豐產景象,抽樣測算比1970年增產10%,個別生產隊畝產將達到近千斤。這位原來為我軍炮兵團團長、先前作為軍管會負責人調任來的領導,對此常常興奮不已。
10月的一天,王杰書記穿著他那套沒有了領章的軍裝,坐著那輛草綠色吉普車,在縣農業局黨委書記于建福陪同下,來到莊行良種場(此時已經通了公路)。在場里,他在場長的帶路和介紹下,興致勃勃地查看了全場種植的水稻與棉花。這期間,局黨委書記于書記吩咐食堂同志,帶了幾斤“雙豐一號”的谷子到附近村的碾米廠輾成大米,又到鎮上買了一只小公雞、一瓶上海“土燒酒”,搞了個簡便中餐,請縣委書記品嘗水稻優良新品種。王杰書記破例吃了這頓中飯,席上,他連連舉杯祝賀管仁欣的成功,舉杯感謝良種場全體干部職工的艱辛努力。遺憾的是管仁欣恰巧不在場里。第二天,王杰書記在縣委常委會上對自己此次違規吃飯做了深刻檢查,并補付了中餐飯錢和糧票。
第二年秋,王杰書記再度破例。那是管仁欣再度向場黨支部提交入黨申請書,可因為當時管仁欣出身特殊,黨支部不知如何是好,并匯報局黨委。局黨委于書記小心翼翼請示,“你們把材料送過來,我好好看下。如果沒有其他負面情況,這樣的同志不入黨誰入黨啊?!”王杰書記說。兩個月后,管仁欣光榮加入黨組織。
“又10多年里,他用雜交方法培育成功早稻秈稻品系‘771‘772‘773,又把‘773與糯稻雜交成‘1026,‘771‘772兩者都具有成熟早與不自然落谷的特點,適應機械化大面積收割;選育成大麥新品種‘741‘746,兩者畝產均在400斤以上,增產15%以上;選育成功油菜‘764,具有植株高大、抗病性強的特點。”縣農業局資料記載。
1988年,市人事局、市科技干部局合制的一份報表顯示:“雙豐一號”比當時普遍種植的“農墾58”單產增產7%~18%,而且出米率高、米質優、口感好,自1972年至1983年市郊累計種植514.8萬畝。1968年,他從“農墾57”中成功選育“雙豐四號”比種植的“滬選19”單產增產8%~15%,比“桂花黃”單產增產12%~20%,并具有早熟、耐寒、抗病與省肥的特點,市郊種植18萬畝;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山東等14個省市,自1980年至1985年每年種植300萬畝(統計資料不全)。據安徽省《中國水稻品種系譜稿》資料記載,安徽省1985年種植“雙豐四號”103萬畝。縣農業局那份資料記載,奉賢那些年外供“雙豐號”系列水稻種子2000萬斤。1985年管仁欣已經調至川沙工作,仍然有安徽的同志來信要求支援調撥“雙豐四號”種子。
鹽堿地產量基礎極低,增產幅度往往奇高。筆者1989年采寫的報道《奉賢農業綜合開發效益巨大》中提到過:“奉城地區10個村的近萬畝鹽堿田,過去后季稻單產僅200~250公斤,今年平均370公斤,最高達到500公斤。”按最保守估算,彼時江、浙、滬及山東省瀕海灘涂鹽堿地種植水稻不下百萬畝。
除了在錦江飯店撰寫的那篇大作外,上海科技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種子工作手冊》,29萬字,他撰寫良種繁育和比較試驗兩部分共計8萬字,此書1979年2月再次出版;1975年出版的《作物育種》一書他撰寫萬余字;撰寫農業科技方面論文和指導文章50多篇共計20萬字,其中近10篇由上海市《科技雜志》發表。
1978年3月18日,管仁欣不敢相信自己居然置身于莊嚴、神圣的北京人民大會堂。他作為全國3478名科技人員代表之一,前來參加全國科學大會。
會上,他獲得全國科技先進工作者稱號,為全國獲此項殊榮的1192人之一。
長達14天的與會,他激動得每個晚上久久無法入睡。會議結束后,他制訂了一個更宏大的科研計劃。
管仁欣,是我國農科人星空板塊上一顆卓著星辰,其閃爍極為光彩動人!
(因人物要求,文內小娟大娟為化名。文中領導干部職務以事件中任職為準)。
作者簡介:
張國寶,上海奉賢人,中共黨員,在職研究生學歷。職業農民、遠洋海員(二副)、記者、企業總經理。紀實類作品《娶新郎》《秀發拂著鋼槍》《獄中‘紅與黑》《深藍上的交響曲》等,曾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全國多家媒體發表作品,并獲得多則獎項。
責任編輯/趙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