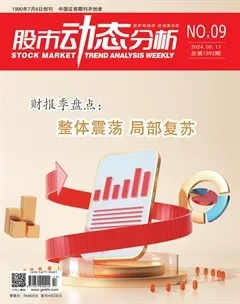居民消費回暖的結構性特征
去年以來有觀點認為,房價與消費之間存在因果聯系。本文我們主要討論與地產因素無關的消費邏輯。
房地產周期中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差異
我國房價走勢本身存在較強的周期性。從2000 年前后至今,房價走勢已經歷五輪周期(1998 至2006年,2006 至2009 年,2009 至2012 年,2012 至2015 年,2015 年至今)。
由于地域間經濟發展水平、人口流動、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差異,房地產周期在不同等級城市中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差異。
2005-2015 年,房價指數的年度同比漲跌幅呈現出明顯的等級差異性,其中超一線城市的房價增長領先,其次是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則相對滯后。
2015-2018 年,房價指數的年度同比漲跌幅排序與前一時間段相似,超一線城市繼續領先。然而,到了2017 年下半年至2018 年的市場底部時,三線城市的房價表現出較強的韌性,超過了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而超一線城市的抗跌性相對較弱。
2018-2020 年,這一時間的上行階段,三線城市的房價增長領先,其后是二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超一線城市的漲幅最小。在疫情期間,三線城市的跌幅最為顯著,而超一線城市則顯示出最小的跌幅。
2020 年至今,超一線城市在上行階段的房價增長再次領先,而在下行階段,2023 年之前,超一線城市的跌幅較小。2023 年以來,一二三線房價有企穩態勢,超一線城市仍在下行通道。
房價走勢與整體消費 變化的關系并不緊密
房地產市場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可通過四種主要效應來解釋:財富效應、流動性約束效應、預算約束效應和潛在購房者的替代效應。具體來說,財富效應和流動性約束效應主要影響已有房產的消費者:當房地產市場價格上升時,這部分居民的名義財富得到增值,從而可能激發更高的消費水平。相反,預算約束效應和潛在購房者的替代效應則主要影響承擔房貸的居民以及潛在的房屋購買者:房價上漲導致這些群體需要將更多的收入用于購房,從而不得不增加儲蓄,減少其他消費。
數據顯示,自2005 年至2023 年,中國的社會零售總額增長了7 倍,而同期全國住宅平均價格上漲了3.5倍。我們選取了70 個大中型城市的新建住宅價格指數的月度同比增長作為房價周期的代理變量,社零消費額的月度同比增長作為消費增速的代理變量,回歸分析發現,房價上漲對消費增速的正向拉動效應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從趨勢上看,其抑制效應也不明顯。
理論上而言,不同等級的城市在房地產市場和消費市場方面存在顯著的區別,因此房地產市場與消費之間的關系在各地區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特征。我們通過采用“房價收入比=城市二手住宅市場均價×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式,對不同等級城市(包括超一線、新一線、二線及三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房價收入比增速的擴大在一定階段會導致居民消費增速的下滑,在房價收入比增速較快的城市中,無論是已購房者還是潛在購房者,都可能因為短期內的大量儲蓄消耗及較高的還款壓力而出現消費能力的下降,但長期來說,這一規律同樣并不明顯。
在多輪房地產周期中,長期來說,由于四種效應的對沖,房價的直接變化并不能對社零消費增速產生明顯的影響,而房價收入比的快速增加對消費起到抑制作用也并非適用任一階段。
從現實的房價和消費數據并未看到兩者緊密的關系,但從預期角度看,對房價是否上漲的預期會明顯影響居民是否增加在消費方面的支出。從央行公布的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中看,居民預期房價上漲的比例提高時,居民在消費、儲蓄和投資中選擇“ 更多消費”的比例會明顯上行,但2022 年以來二者相關程度有所趨弱。
從社零的細分項中可以看到,在最近幾年的房地產價格同比表現較差的時間里,與地產后周期產業鏈相關的家用電器和音箱器材類、家具類、建筑及裝潢材料類商品零售額受到的負面影響較大。
今年內需會有哪些可期待的亮點?
從數據上看,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居民消費支出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當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時,居民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消費,從而推動消費支出的增長。這種增長同樣會反映在社零上,表現為社零增速的提升。換言之,拋開地產因素判斷消費的表現應該更聚焦于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的變化趨勢。
近幾年,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穩步增長,中位數逐年抬高,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穩定在43%-45%,這意味著我國居民仍有增加消費的財富基礎。
此外,失業率的高低直接反映居民就業情況,失業率高的階段,居民消費增速會出現明顯下降,換言之,就業是否穩定已成為我國居民消費的主要驅動力。2023 年12 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更加突出就業優先導向”,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多措并舉穩就業促增收”,在多項穩就業政策的支持下,今年大概率能完成城鎮新增就業1200 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 左右的主要發展目標,這也將為增加居民的消費支出提供堅實基礎。
觀察最近幾年的數據可以發現,隨著房價下行,我國居民在居住項中的消費占比出現回落,除此之外,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的過程中,居民消費結構發生較大變化:衣著、生活用品及服務的消費占比逐漸下降;醫療保健的消費占比穩步提升;疫情期間,教育、文化和娛樂、交通和通信、其他用品及服務等偏“體驗型”消費的占比受到階段性沖擊,2023 年這些商品的消費占比出現明顯回升;食品煙酒的消費占比在疫情前呈下降趨勢,2020 年以來出現反彈。當然,從2023 年以來CPI 衣著分項表現可知,疫情影響消退后,服裝需求明顯上升并延續至今。
從上面分析可知,房價走勢只是影響部分商品消費,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穩步增長、失業率維持低位的背景下,隨著居民消費結構變化,2024 年內需仍有值得期待的結構性亮點。
第一,受疫情影響沖擊大,增長趨勢逐漸向疫情前靠攏(甚至超過疫情前水平)的部分商品:飲料類、煙酒類、文化辦公類、體育娛樂用品類商品,甚至衣著類消費或也將跟隨出行等需求而保持高增態勢。
第二,受擴大內需政策扶持力度大,可享受“以舊換新”補貼的部分商品:汽車類、家用電器和音箱設備類商品。
第三,2024 年,居民出行意愿依然高漲,9 城地鐵客運量持續超過2019 年,景點門票價格高于往年,今年春節和清明的旅游人數及旅游收入均超過2019 年,我們推斷今年出行和旅游相關的服務性消費仍會保持強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