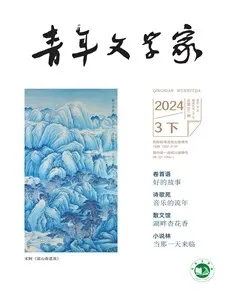高適第三次出塞的邊塞詩探析
牛靜靜



天寶十一載(752)秋,高適第三次出塞,赴西塞入哥舒翰幕府任左驍衛兵曹參軍,充任掌書記。同年末,隨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在玄宗面前對他大加稱贊。高適在哥舒翰幕府任職四年,身遇知己,受到重用,頗為得意,成為他仕途升遷的起點,但是由于他生活地位和思想情感的變化,給他的創作帶來不利影響。這一時期高適所作邊塞詩約有三十首。
一、唐蕃戰爭對高適詩歌創作的影響
(一)從唐蕃關系中看九曲之戰
大約在唐貞觀七年(633),松贊干布在拉薩建立了奴隸制的吐蕃王朝。而吐蕃與唐王朝的聯系是相始相終的,據《新唐書·吐蕃傳》記載:“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后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
在藏族古代史上,有兩個著名的歷史人物,其中一位就是吐蕃王朝的締建者松贊干布。大約在貞觀年間,吐蕃在松贊干布的治理下變得強盛起來,所以松贊干布開始注重加強與周邊各民族的關系,而唐王朝當時是經濟文化強國,因此他覺得要與唐王朝打好關系才會使自己的王朝發展壯大。吐蕃在唐貞觀八年(634)開始和唐王朝建立了友好關系,向唐王朝遣使朝貢,唐蕃進入到一個友好的階段。這也得益于松贊干布的王后文成公主,即漢藏民族友好團結的先驅,她是將中原文化帶到吐蕃地區的傳播者。唐太宗時,王朝宗室女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和親以后,吐蕃就與唐王朝關系密切起來,罷兵和好。可是,這樣的和親是有目的性的,“是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雙方統治階級因彼此利益而作的暫時的讓步和妥協。松贊干布死后,吐蕃大論祿東贊掌握大權,唐蕃的親密關系開始發生逆轉。龍朔三年(663),吐蕃占有吐谷渾,其北部直接與唐王朝的河隴地區相接,威脅著唐王朝的河隴、西域地區。從此,唐王朝與吐蕃進入了一個爭戰頻繁的階段。就像高適《塞上》中所描述的“轉斗豈長策,和親非遠圖”,事實正如其所料,睿宗景云元年(710),吐蕃在金城公主嫁到吐蕃時,以賄賂手段,在唐王朝手里騙取九曲之地,以致成為唐蕃關系走向對抗的新一輪導火索。九曲,指的是今青海貴德東河曲一帶地區。吐蕃統治者以欺騙的手段想取得九曲這片寶地,《舊唐書·吐蕃傳》中就有記載,吐蕃試圖用九曲這塊地方來攻打唐王朝,天寶十二載(753),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莫門等城,吸收九曲部落,奪取了吐蕃的后勤基地。哥舒翰收復九曲之地時,約在天寶十二載五月,收復九曲是當時唐王朝與吐蕃戰爭成敗的關鍵戰役。九曲一度成為吐蕃侵犯唐王朝邊境的跳板,哥舒翰收復此地,在一定程度上徹底解除了唐王朝在西部的邊患,這一功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二)哥舒翰在唐蕃戰爭中的表現
哥舒翰是天寶年間唐玄宗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將領之一。天寶六載(747),哥舒翰在任隴右節度使后,唐蕃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作為唐玄宗時期最強有力的將領之一,哥舒翰也成為那個鼎盛時代最強有力的軍事實力的象征。他和麾下的將士們為了維護唐王朝的繁榮穩定局面,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成為后人永遠的追憶。他也成了玄宗天寶時期最受關注的人物之一,玄宗皇帝給了他很大的恩寵,哥舒翰被封為“西平郡王”。
二、高適詩歌中的哥舒翰
高適在第三次出塞河西時,得到了哥舒翰的舉薦,詩人心中理想抱負得以實現,所以有“一朝感推薦,萬里從英髦”(《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的深切感慨。哥舒翰收復黃河九曲之地,高適寫詩予以歌頌,如《九曲詞三首》其一:“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為在疆場。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中異姓王。”“將軍”指的就是哥舒翰,歌頌他顯赫的地位和巨大的功績。哥舒翰以身許國,廟堂所倚,奮身疆場,最終因功業卓著,故封侯進王。這正與高適一生的理想目標相契合,詩人內心的欽佩之情溢于言表,感嘆至深,因此造語高華,氣勢雄偉。還有同樣寫哥舒翰不畏戰爭的艱苦,英勇從軍報國的英雄主義情懷的,如《塞下曲》中描述的“結束浮云駿,翩翩出從戎”和“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哥舒翰收復九曲,是唐王朝與吐蕃之間的一場大的戰爭,最后唐軍取得了勝利,解除了西部的一時邊患,因此,高適作詩來歌頌哥舒翰英勇殺敵的大無畏精神。高適在《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中寫道:“遙傳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氣群山動,揚軍大旆翻。奇兵邀轉戰,連弩絕歸奔。泉噴諸戎血,風驅死虜魂。頭飛攢萬戟,面縛聚轅門。鬼哭黃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與巖險,鐵騎皆云屯。長策一言決,高蹤百代存。威棱懾沙漠,忠義感乾坤。老將黯無色,儒生安敢論。解圍憑廟算,止殺報君恩。唯有關河渺,蒼茫空樹墩。”“遙傳副丞相”中的“副丞相”指的就是哥舒翰。“作氣”以下四句寫唐軍的氣勢浩大。“泉噴諸戎血”以下六句寫戰爭后敵方失敗的慘狀,同時用“黃埃暮”“白日昏”的哀景來襯托,給人倍加凄涼的感覺。“石城與巖險”到結尾歌頌了主人公的聰明與威嚴。“長策一言決,高蹤百代存”二句寫他的睿智決策。“忠義”感于天地,使老將失色,停止殺戮以報君恩,憑“廟算”來解重圍。“唯有關河渺,蒼茫空樹墩”二句描寫出戰后的慘烈場景,敵人的樹墩都已被消滅全無,四下杳無人煙。這首詩主要贊頌了哥舒翰在戰場上的英勇殺敵,足顯唐軍威勢。
哥舒翰英勇殺敵,保衛祖國不被侵犯的大無畏精神,在一定時期內解除了唐王朝的邊患,使得百姓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高適在《九曲詞三首》其二中寫道:“萬騎爭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此詩描寫了“萬騎爭歌”“千場對舞”等場面,展現了百姓對和平到來的無比渴望。詩人用當時美好的景色“楊柳春”來襯托,用“繡騏驎”來形容,加之“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寫出了全天下的人們普天同慶,掩飾不了人們久已對和平的期待。又如《九曲詞三首》其三:“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只今將飲馬,黃河不用更防秋。”此詩歌頌了哥舒翰部將團結一致,立志保衛國家邊疆的精神,至此“青海”一帶可以悠閑地放牧,而“黃河”一帶也無須用兵把守。高適的詩作中還有哥舒翰收復九曲之戰后的塞外奇景和戰后邊地的和平景象,如《部落曲》《金城北樓》等,體現了收復九曲之戰后邊塞奇景無限,生產得到發展,百姓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這充分體現出哥舒翰收復九曲之戰的正義性。
哥舒翰在百姓心中是“北斗式”的人物,當時西北邊境的百姓在《哥舒歌》中歌頌了這位將領:“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在哥舒翰死后,唐德宗對其子哥舒曜說:“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新唐書·哥舒翰傳》)還有如李白、杜甫等詩人也對哥舒翰收復九曲給予肯定和贊頌,把他稱贊為“英才”“英雄”。《東城老父傳》中言及對蕃戰爭則云:“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蔥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這對哥舒翰的戰功作出了精練的概括,并成為人們經常懷念談論的話題。因此,哥舒翰已經成了盛唐軍事鼎盛時期的象征性人物,也展現了他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形象。
三、高適在第三次出塞中的認識
以上諸多論述,可以看出高適在出塞中的經歷和認識,《舊唐書》中記載高適的人生理想是“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而高適五十三歲時才入哥舒翰幕府,在此前,他懷才不遇,立志要有大的抱負,但終因當時社會和統治階級的壓抑而坎坷無奈,現在得到哥舒翰的推薦,心中無比欣喜。在趕赴河西、登上隴山的途中(隴山歷來為西行者的必經之路),他滿懷興奮地吟唱道:“淺才登一命,孤劍通萬里。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登隴》)從這首詩可以看出他感恩哥舒翰的情感溢于言表,而自己一心建功,決心“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塞下曲》)。在送別友人時,他寫了“長策須當用,男兒莫顧身”(《送董判官》)二句,極其真誠。同時,在《入昌松東界山行》中,他勉勵自己“王程應未盡,且莫顧刀環”。在經歷九曲之戰后,他用熱情的筆觸來寫詩歌頌,與百姓共同慶祝和平的時光,他希望國家統一穩定,百姓安居樂業。而在此同時他體會到了時光短暫,直至人生的末尾又開始惆悵嘆息。高適在《奉寄平原顏太守》一詩中寫道:“上將拓邊西,薄才忝從戎。豈論濟代心,愿效匹夫雄。”就因為軍中無事,因此他惆悵萬分,同時渴望援引之意出現。他在《陪竇侍御靈云南亭宴詩》中寫的“河漢徒相望,嘉期安在哉”,以及《陪竇侍御泛靈云池》中的“誰憐持弱羽,猶欲伴鵷鴻”等詩句,可以看出他想另謀出路的念頭。還有,高適在人生最后所寫的邊塞詩中,將個人的功名與建國立業相結合,對一些對外侵略戰爭作了錯誤的歌頌,如《李云南征蠻詩》中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另外,他在詩序中對朋友的恭維也表現明顯,與自己剛開始主張和平的理念大為迥異。所以,這些詩的內容空洞無物,夸贊過度,因此詩的價值就略顯低俗了。
綜上所述,高適第三次出塞,在哥舒翰幕府任職,當時主將戰功卓著,自己也比較志得意滿,多年以來夢想總算實現,同時他這次所寫邊塞詩的風格內容與前兩次相比略顯低迷。高適此次出塞所作的邊塞詩,主要以歌頌戰功為主,而揭露邊塞中所見腐朽的詩已然沒有。高適對哥舒翰在安定西部邊塞所作的貢獻予以歌頌,為了迎合最高統治者,詩人總是盲目歌頌他們,而無微詞。剛開始哥舒翰收復九曲之時高適所作的詩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比如當地百姓稱頌的“至今窺牧馬,不敢過臨洮”(哥舒翰的觀點)與高適渴望戰爭勝利的愿望一致,這樣的愿望體現在《九曲詞三首》其二中,與哥舒翰的情感相吻合。但高適大多數詩已經失去了人民性的色彩,盲目歌頌不義之戰,如《李云南征蠻詩》。還有《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中的“泉噴諸戎血,風驅死虜魂。頭飛攢萬戟,面縛聚轅門。鬼哭黃埃暮,天愁白日昏”,歌頌哥舒翰戰功時,過于頌揚嗜殺的場景,也是他邊塞詩思想內容下滑的原因。抒寫建功立業、壯志的激昂情緒成為高適詩歌的主要思想,他個人懷才不遇的呼聲已銷聲匿跡,如《塞下曲》就是他典型的代表作,詩中寫到“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感慨他理想的實現。《金城北樓》中的“為問邊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無窮”,寫出了詩人悠閑無所事事的感慨,同時也是異域鄉愁的自然流露,不過這樣的感慨再也不是讓他焦慮和懷才不遇的無奈之嘆,這種鄉愁早已在知遇之感中得到慰藉,如在“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登隴》)的詩句中深有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