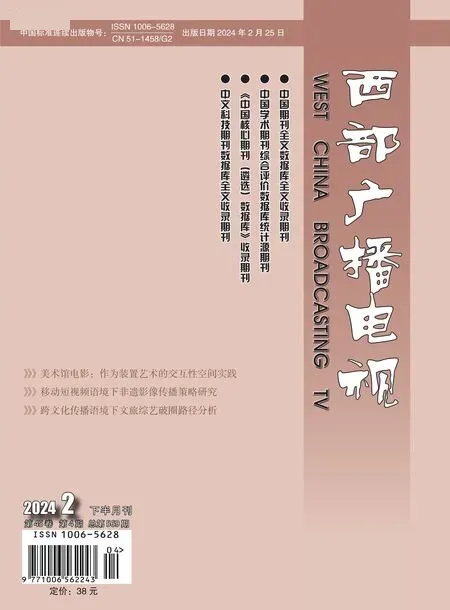想象與消費:短視頻平臺中的懷舊景觀建構
——基于“懷舊鋪子”探析
崔宇航 張學知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1 研究緣起及目的
一直以來,人類對于“懷舊”的認識不斷延伸。17世紀,懷舊被定性為一種精神疾病,即“思鄉病”。18世紀,盧梭等人又將懷舊定義為對過往某段時間的回憶。在這之后,懷舊陸續被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納入研究范疇,其內涵的演變反映了社會的變遷和話語的變化,所以有學者認為不同的社會氛圍、不同的群體中則會產生不同的懷舊現象。但懷舊的基本特性無法改變,即作為人類的內生情感和心理需求,加之情感已囊括進消費社會的發展邏輯中,因此以懷舊為主題的情感化商品,得以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信息社會,媒介技術則充當“擴音器”,放大懷舊情感,控制懷舊想象,意圖拓寬懷舊消費景觀。諸如常見的老品牌、老字號的懷舊廣告,時常可以掀起社會的“懷舊風潮”,刺激社會大眾的懷舊消費,但刺激消費并不等同于對消費者的“收割”。
此外在消費社會的理論視域下,景觀是消費邏輯和文化現象的綜合體,且側重于視覺化的呈現,而短視頻無疑是視聽表達的重要渠道,平臺中表達懷舊的短視頻更是屢見不鮮,主要表現為年代影視劇的剪輯片段、懷舊金曲合集、昔日的鄉村生活、兒時的卡片電玩等。筆者通過調查發現,有關懷舊的短視頻在抖音平臺上的播放量已破億,毫無疑問,懷舊類短視頻成為大眾公開表達懷舊情感的重要渠道,同時也成為販賣懷舊商品的新窗口。譬如,短視頻平臺中一批以兒時零食和村頭小賣鋪為展演內容的短視頻賬號,已成為懷舊零食“售貨站”,其會開設懷舊零食的銷售櫥窗且定時直播售賣,開辟了懷舊零食的線上售賣渠道。
因此,本文將研究重點放在此類以懷舊零食為主要內容的短視頻上(以下簡稱為“懷舊鋪子”),意圖通過懷舊零食的端口,探析短視頻平臺中懷舊消費的景觀空間是如何建構的;消費社會的邏輯下,大眾是如何陷入資本設定的想象空間中的;找到并審視短視頻平臺中懷舊消費的倫理問題。
2 想象:懷舊符號的疊合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中,資本的再生產會借助媒介技術,塑造出眾多符號,以此來建構景觀消費社會,人們也由此產生出欲望與幻覺,這表明人們對于物品的真實需求轉變為對符號的追捧和迷戀。但除了符號本身創造的欲望,懷舊本身也是一種“幻象”,是“逆托邦”的表現,是為了緬懷過往,回到過去的時空,所以懷舊被認為是應對現代性癥候的浪漫主義想象,甚至把懷舊看作一種敘事方式,橫亙于社會機制及其當事人主體之間,以縫合的方式來處理現代性所帶來的一系列分裂所造成的主體認同危機[1]。因此,在懷舊的消費景觀中,懷舊符號實則是一種想象的消費符號。
此外,懷舊被認為是復雜情感、認知(如回憶)和動機(如渴望)的混合體,僅需熟悉的氣味、聲音、紀念品、參與對話或感到孤獨等契機就能被激發[2]。因此,要想建構起“懷舊鋪子”這樣一個景觀空間,少不了用于“催化”的懷舊符號,即品牌符號、空間符號與聲音符號。零食的老包裝、老名稱與老標志都屬于零食的品牌符號,可以瞬間勾起人的味蕾記憶;兒時小賣鋪熟悉的空間布局、貨架上的零食擺放,能使人直接進入場景;熟悉的零食購買對話與短視頻的老歌配樂,能使人輕松代入身份。通過這三種懷舊符號,懷舊景觀的吸引力得到了增強,大眾沉醉其中無法自拔;另外資本也獲得了掩蓋其本質的“外衣”,在消費中牢牢占據主體地位。
2.1 品牌符號:味蕾懷念
食物的發展見證了社會的變遷,塑造著人們對味覺的記憶,就好比云貴喜酸、湘人愛辣,味蕾也就成為人們想念過去的窗口。首先在物質資源相對匱乏的年代,人們對于食物味道的印象會深深鐫刻在腦海里,以至于進入物質充盈的時代后,人們雖然常會想起“熟悉的味道”,卻怎么也吃不出當初的感覺;其次在品牌較少的年代,無論是帶有品牌名稱的“牛羊配”或是只有昵稱的兒時零食成為“80后”“90后”揮之不去的記憶,所以“懷舊鋪子”中的零食品牌符號異于可口可樂、奔馳等百年品牌的經典廣告語,其本身早就在往日的消費者心中具有一定的意義。
常見的名稱、口號、標志、包裝等都可以成為品牌符號[3]。老品牌、老包裝本就充斥著童年回憶,當短視頻將其進行集中復現時,會強烈地刺激消費者的味蕾記憶,既讓消費者自己加強對懷舊的想象,又能成功維護懷舊系列零食的品牌形象,從而使得營銷價值得以延續。而對味道的懷念本質上是公共情感的流露,資本將其轉移到現今銷售的商品中進行“賦魅”,進一步節省了塑造品牌符號的營銷成本。
2.2 空間符號:場景再現
空間的符號化進程代表著空間的媒介形象生成,空間符號促進了公眾對空間的想象與感知。建構“懷舊鋪子”的空間符號,既是一種空間表現,又是一種話語文本,能夠激發人們內心深處的懷舊情感。就現實空間而言,“村頭小賣鋪”本就是鄉村內部標志性的聚合地,日常生活中,村民會前往小賣鋪購買食品,其不僅是重要的活動空間,也是一個娛樂空間。
隨著大多數人離開鄉村,“村頭的小賣鋪”也逐漸消失。但是,通過空間符號,“小賣鋪”得以“復原”,遠離家鄉的人們得以實現數字化的懷舊“在場”。而且,資本也在最大化地復原場景,貼滿報紙和明星海報的墻壁,陳舊的商店門窗和老式的食品展覽柜,成為構建空間符號的基礎元素。空間符號在短視頻平臺中得到了有效的傳播與擴散,景觀得到了懷舊群體的凝視,近似于“真”的舊,只為吸引消費者來懷舊,聚集平臺流量,將場景的回憶特性置換到實際的懷舊產品中,以達到情感性的經濟交易。
2.3 聲音符號:身份認同
人類的聽覺行為本質上是融入環境的過程[4]。而聲音在短視頻平臺中是重要的元素,可以支撐起懷舊景觀的建構,優化大眾對懷舊的感官體驗。
在與“懷舊鋪子”相關的短視頻中,其視頻配樂常選擇兒歌或老歌,以此烘托短視頻的懷舊氛圍。比如,《粉紅色的回憶》《往事只能回味》等歌曲,每當前奏一起,聲音符號便能吸引大眾對懷舊的信息感知,形成人與懷舊的聲音符號互動。
另外,在與“懷舊鋪子”有關的短視頻的劇情演繹中,相應的對話也是聲音符號的組成部分。例如,“小孩前往村頭小賣鋪,跟老板說要兩根辣條、一個大頭雪糕”這樣的劇情在視頻中較為常見,而買東西的對話與人們在兒時前往小賣鋪的對話幾乎無差別。查爾斯·霍頓·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認為,語言本就是人際傳播的中介,聲音語言同樣承擔著傳播情感的作用,且具有“冷媒介”的特征。因此,在受眾與“懷舊鋪子”之間進行細膩的懷舊情感交往時,“懷舊鋪子”充當聲音的發出者,而受眾則作為接收者,通過聽覺想象的形式實現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3 消費:情感邏輯的操縱
符號構建起了懷舊景觀,并放大了此景觀下的懷舊想象,但景觀最終的使命是刺激消費,這也是資本發展的根本動力。在消費社會持續完善的發展態勢下,情感加入了社會的經濟生活,以色列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資本主義的情懷》一書中便提出了“情感資本主義”這一概念,詳細闡述了資本主義如何利用、加工并生產消費者的情感[5]。通過強化情感生活,資本主義成功將情感轉化為商品,懷舊也就成為資本操縱的消費工具。懷舊情感本是人們有意識地去營造過去的時空,是加速社會中人們的精神棲息地,但在資本生產的懷舊景觀中,人們只能按設定的情感邏輯去行進,否則便會脫離資本所圈定的懷舊群體。
而且,人類要想獲得身份認同,就必須融入懷舊景觀,遵守懷舊群體的秩序,不過人們為此付出的代價便是落入消費的“泥沼”。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評論區與直播間中,關于懷舊的話語雖然能夠烘托氛圍,但是會裹挾消費者購買懷舊商品,疏解情緒的表面下是消費的異化;第二,個體在投入懷舊情感后,通過媒介技術繼續向他人傳遞情感,在懷舊的“共同體”中為他人提供陪伴,進行情感勞動,會使其成為商品,促使勞動的異化;第三,商品與情感的價值都轉移到增殖資本上來,公眾對商品的品質視而不見,情感也被囚禁于“櫥窗”,導致了商品與情感價值的異化。
3.1 話語裹挾
短視頻平臺給予了公眾自由表達的權力,公眾的話語權力看似獲得了公平的分配,但在網絡空間充斥著多方話語勢力的博弈,且互相滲透。資本對話語的控制,也是促成消費的重要途徑。“懷舊鋪子”的話語控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短視頻評論區中發表懷舊傾向的評論,形成了身份圈層;另一方面是售賣懷舊零食的直播間中主播的“話術”鼓動,通過話語裹挾住懷舊人群,售賣懷舊的標簽。
評論區中常出現的話語,諸如“小蛋糕怎么買啊”“小時候吃的這種小蛋糕真的超級好吃”等,恰好烘托了評論區用戶的懷舊情緒,并具有及時性,乃至引發從未體驗過的獵奇者提問,“以前的辣片真的是可以買半片嘛”“這辣條加了啥成酸不溜及的了”等。盡管“懷舊鋪子”是以劇情演繹為主,但評論區無論是表達懷舊還是好奇懷舊的,都已成為凝結懷舊圈層的“固化劑”。
“懷舊鋪子”也會有定時直播的行為,以此來擴大銷量。其中,主播的直播話術,一方面緊緊圍繞對過往的懷念去介紹商品,以便拉近與消費者的心理距離;另一方面表示以前是花幾毛錢為了解饞,現在則應當重在體驗上。諸如此類的話語裹挾著公眾去消費,從而獲得群體認證的標識物,會使公眾變為情感資本主義的“人質”。
3.2 情感勞動
按照馬克思的生產理論,通過勞動生產商品是實現資本增值的必要條件。這意味著情感資本主義的命題中少不了相應的情感勞動。生產與消費界限的模糊,也昭示著情感勞動將貫穿于商品售賣的全過程。“懷舊鋪子”中針對公眾的情感勞動與情緒服務類人員的情感勞動相比具有其特殊性,一般來說情感勞動強調勞動過程中的情感管理,以及由此延伸的控制與規訓,這是實現勞動價值交換的重要途徑[6]。目前出現的虛擬空間的陪玩、陪聊,代表著情感勞動已成為標價的商品。
在“懷舊鋪子”的景觀映照下,公眾內生的懷舊情感被持續放大,進而不自覺地影響著景觀下他人的懷舊情緒與情感體驗。在此過程中,懷舊個體成為資本主義的“雇員”,在購買懷舊零食時,除了消費前的情感投入,還會顯露一些個人信息,以此來強化與群體成員的情感關系。而到了資本手里,情感勞動成為維系懷舊消費的介質,所以懷舊的個體既是懷舊情感的消費者,又是懷舊情感的生產者,也就打破了生產者與消費者是相互獨立的慣常。換言之,公眾針對懷舊的情感勞動,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對勞動的異化。
3.3 價值轉移
“懷舊鋪子”是情感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它將懷舊情感商品化,也將鋪子中的零食情感化,所以懷舊零食便是情感商品。有學者認為,情感商品被主體需求并消費,是為了滿足商品承諾帶來的某種情感,而這種情感又是消費主體自己制造出來的。因此,情感與商品共同生成的“循環體”是內爆的表現。
懷舊的感性在消費社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沖刷了公眾對商品真實物質需求的理性,忽視了商品本該具備的品質。比如,部分評測博主便對“懷舊零食”做過測評,在測評過程中發現所謂的“香辣小螃蟹”是蟹殼及“邊角料”組成的;“鎖喉桃”的配料表也是滿滿的“科技與狠活”,失去了桃子的本味,其實不論健康與否,這已然失去了食物本來的價值。
另外,懷舊情感的體驗是資本給予的,但這樣的體驗并非自由的,甚至可說是虛假的,懷舊群體置身于想象的景觀之中,不斷被提示要進行情感消費,這讓懷舊失去了本來的情感價值,公眾將陷入更為嚴重的情感空虛,從而加劇社會的分裂。
4 結語
本文著重分析了消費社會視域下短視頻平臺中的懷舊景觀,從視聽符號入手,分析如何建構景觀想象,也看到了單從“懷舊鋪子”出發,社會的懷舊消費存在著嚴重的倫理問題。雖然世界已經處于情感消費的邏輯之中,但還可從三個方面進行補救:對于個人來說,理性不應被情感完全占據,不能自我混淆,要根據需求進行消費;對于商戶來說,在附加產品的情感特性時,應當切實提高商品的品質,不能將味道與品質混為一談;對于社會來說,應該重視情感與文化的公共價值,加強情感治理,而非任由資本操控,避免陷入麻木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