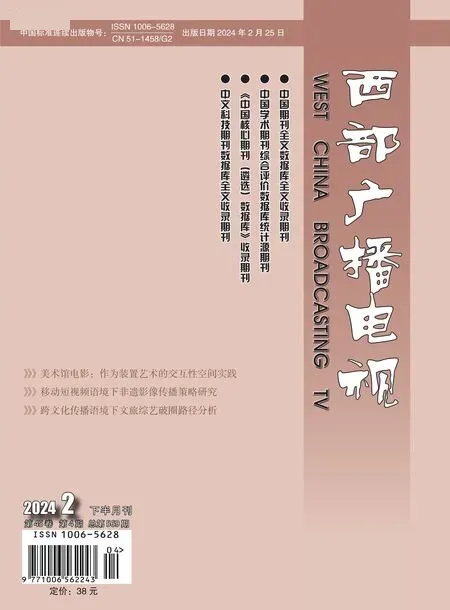鄉村文化振興視角下新農村題材影視作品的主旋律敘事特征
——以《我和我的家鄉》為例
劉宇捷
(作者單位:山西傳媒學院)
《我和我的家鄉》上映于2020年,該電影敘事特征不同于以往主旋律電影集中圍繞軍事、戰爭等內容展開敘事,而是緊扣當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展成果進行敘事,同時匯集多元化的敘事風格,屬于主旋律電影敘事創作的一次較為成功的轉型[1]。該電影之所以引起廣泛好評,除了與優秀導演聯袂執導、優秀演員精湛表演及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有關之外,也與其圍繞鄉村振興主題、轉變陳舊敘事話語的成功嘗試具有密切聯系[2]。《我和我的家鄉》借由不同區域的點狀鄉村構筑成中國鄉村的群像,通過影視巨幕呈現樸實真切的鄉村生活,靈活應用生動精簡的語態完成明朗主題的細膩描繪,將農民生活瑣事作為切入點,從多個維度彰顯鄉村振興主題。
1 敘事結構
《我和我的家鄉》在創作時有機融合文化內涵和當代審美,在幽默詼諧的敘事氛圍中激活鄉村文化的生命力,通過“家鄉+影像”“家鄉+人物”“家鄉+體驗”的敘事邏輯,引導觀眾感知鄉土空間和鄉土溫度,呈現樸素、自然的鄉土氣息。該影片采取集錦式敘事結構,分別拍攝了《北京好人》《天上掉下個UFO》《最后一課》《回鄉之路》《神筆馬亮》5部優質短片,呈現了中國版圖上東、南、西、北、中5個不同地理空間,展現了與農村醫保、支教、扶貧、鄉村建設等相關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果,折射大時代變遷,表達了不同地域的鄉土記憶,并帶領觀眾近距離接觸生活在廣大農村的普通人,感受其在鄉村振興偉大歷史實踐當中作出的具體貢獻以及其中蘊含的人文精神,喚醒觀眾故鄉情結,宣傳鄉村振興戰略價值及需求。
2 敘事風格
2.1 小品化喜劇類型敘事,弱化感傷因子
《我和我的家鄉》運用“幽默+抒情”的敘事風格,賦予電影全新活力,給予觀眾區別于以往主旋律電影的全新觀感體驗,為新主流電影類型實現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全新的、獨特的敘事思路。這5部短片在敘事策略方面基本一致,都靈活應用了喜劇敘事手法。比如:《北京好人》短片敘事過程中通過黑色幽默營造犯罪氛圍,打造獨特的喜劇風格;《天上掉下個UFO》主要采用了浪漫主義奇觀化的視覺呈現和荒誕喜劇的敘事手法;《回鄉之路》《神筆馬亮》與《最后一課》一致采取了經典的“喜頭悲尾”的小品化敘事。該電影整體通過喜劇的外衣來傳遞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弱化描寫主人公的悲慘經歷,并通過插入豐富的喜劇元素,以歡快節奏講述中國故事,為觀眾呈現了一幅幅生動的家鄉畫卷,同時傳遞了正能量。
2.2 聚焦民生問題,滿足觀眾審美需求
《我和我的家鄉》融合了商業性電影和主旋律電影的特點,一改以往主旋律電影“說教式”的刻板印象,具體敘事時將原本較為宏大的國家縮小為家鄉,提高敘事內容與觀眾的適配度,將鏡頭對準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命運,從講述鄉土故事入手賦予影片更鮮明的人文色彩,聚焦社會熱點和民生話題,多視角呈現脫貧攻堅成果。影片敘事時選擇時間長河中的重要事件,通過塑造不同地區獨特的人物形象,讓觀眾了解平民英雄。對于不同人物,影片站在個體敘事層面設計其相應動機,使其擺脫以往必須在國家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作選擇的禁錮。影片還通過塑造人神相融合的新英雄形象,從情感方面轉變了傳統主旋律敘事方式。比如,《神筆馬亮》中,角色“馬亮”選擇下鄉建設新農村,希望通過稻田畫打造文旅融合項目,促進家鄉發展,其對鄉村的付出屬于潛意識的私人情感投射。電影講述的5個故事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均塑造了“以喜為正”的人物形象,主人公都是社會中平凡的勞動者,這種敘事焦點的轉移,展現了小人物的大情懷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可滿足觀眾的不同審美需求。
2.3 融入網絡元素,展示科技成果
新媒體不斷發展,短視頻平臺的出現進一步弱化了傳統媒體的優勢地位,影響了大眾生活習慣、行為方式,改變了大眾心理狀態和審美趣味。新媒體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全新的文化傳播陣地,推動創作人員保持動力,不斷優化作品文化形態、美學樣式等[3]。作為近幾年新主流電影的代表作之一,《我和我的家鄉》將網絡審美特征嵌入形式和內容創作中[4]。比如,在影片內容層面,影片為觀眾呈現了網絡紅人這一新型職業身份,并揭示了這一新型職業身份背后引發的粉絲經濟等現象。相比以往的新主流電影,《我和我的家鄉》的主創團隊不僅在內容上緊跟時代脈搏,還在敘事手法和營銷策略上展現了對網絡流行元素的敏感性和創新性,反映了社會對新媒體文化和經濟模式的關注[5]。
此外,《我和我的家鄉》在展示中國科技發展新成果的同時,也有效展示了不同的鄉村環境,構建了鄉村圖景和科技發展并存的新景觀,重點展示了科學技術對鄉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以及人們從中獲得的福利。影片將鄉村圖景和科技發展成就相結合,不僅不會產生割裂感,還可以通過實際案例有效改變中國農村貧窮的刻板印象,展示中國小康社會建設以及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的成就。
3 敘事策略
3.1 設置較強懸念,奠定敘事基調
《我和我的家鄉》5個單元因受到時間篇幅的限制,不適合采取慢節奏的敘事方式,否則難以引導觀眾快速進入不同故事情境。這一情況下,電影各個單元的敘事保持較快的節奏,且在每個故事開頭都設置懸念,促進觀眾快速投入觀影。以《北京好人》敘事為例,影片開始設計了“兩個光頭”鏡頭,這種敘事方式可以迅速將觀眾拉到本篇故事的荒誕情境中,影片也因此具有較為充足的敘事動力。《天上掉下個UFO》的敘事與《北京好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開頭便呈現出觀眾比較感興趣的“UFO”(不明飛行物)這一神秘的科幻事物,在極短時間內達到制造懸念的目的,使觀眾心理層面快速產生不一樣的感覺,進而吸引其注意力。
3.2 簡化敘事結構,形成敘事框架
受時長限制,《我和我的家鄉》不同單元的故事敘事無法像長篇作品那樣深入挖掘角色背景和情節發展,無法完全展現故事的復雜性和角色的立體性,因此在創作過程中一定要有取舍,以確保各個故事都可以將篇幅控制在合適范圍內。通常情況下,長篇敘事都由數個較為完整的小事件連接而成,事件之間因果相連,一起服務于整個影片的敘事。但《我和我的家鄉》這類電影并不適合此種敘事方式,不同單元故事的發展時間跨幅應當短于正常電影,并且應當簡化敘事結構。以《最后一課》為例,故事整體是線性敘事結構,影片中開始“上課”后采用插敘。當角色“范老師”沿著舊路朝著村內跑去時,影片運用同步的方式有效呈現了回憶和現實完全不同的情境。這種敘事相對簡單,且有利于人物心理的刻畫,還能在一定程度上隱喻鄉村不斷發展的主題[6]。
3.3 借助功能化人物,推動敘事發展
結合該影片設置較強的懸念和簡化敘事結構來看,《我和我的家鄉》在各方面都充分體現了“取舍”特色。以《最后一課》為例,這一單元重點刻畫和塑造了一位盡職盡責的教師形象,其屬于該單元敘事中的主要人物。單元開頭,身體帶病的“范老師”癱倒在地,醒來后,“范老師”的第一個念頭是給學生上課,而不是休息。隨著影片劇情的不斷推進,“范老師”身體變得越來越差,但依舊清晰記得自己與學生的最后一課。與“范老師”相比,影片中其他角色基本是功能化人物,其存在的作用,是更好地凸顯主要人物的形象。比如成年“姜小峰”這一角色的設置,影片借助這一功能化人物形象展現了時間的流逝及其帶來的變化,側面塑造了“范老師”的形象,使其更加立體可感,同時引出“學生反哺教師”這一主題,彰顯了教育的意義和價值。
4 敘事中的鄉村文化
新主旋律電影是傳播文化的良好載體,相關創作人員在融合人文情懷和時代特色等基礎上,努力創作富含中華優秀文化的影片,為講好中國故事打開新的窗口[7]。《我和我的家鄉》的敘事創作在展現新時代中國風貌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并且對思想、主題和人文情懷等都進行了良好表達。
4.1 敘事中的中華傳統文化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其價值不僅僅體現在對大眾生活方式產生影響,更深刻的意義在于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在《我和我的家鄉》的敘事過程中,較多劇情都能發現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例如:《北京好人》單元中,男主角放棄買房買車幫助表舅治病,充分體現了儒家的“性本善”思想;《回鄉之路》單元中,男主角留在家鄉治理沙塵,以報答養母的養育之恩,展現了百善孝為先、落葉歸根等中華傳統思想。
4.2 敘事中的鄉村文化元素
《我和我的家鄉》5個單元的不同創作者在敘事創作過程中都積極挖掘家鄉所具有的獨特地理環境和美食美景等,通過引導觀眾感受濃厚家鄉情,喚醒觀眾內心的鄉愁,引發共情,喚起集體記憶。《我和我的家鄉》用全景式的鏡頭描繪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展現了我國多個地區的鄉村風貌和鄉村文化,所有故事的視角都落在鄉村。觀看電影的過程中,觀眾可以進一步了解鄉村物質文化、鄉村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進而對鄉村文化產生認同感。
4.3 敘事中的鄉村文化振興
首先,民間藝術、手工技藝等文化元素在鄉村振興中都扮演著關鍵角色。《我和我的家鄉》展現了鄉村豐富的傳統文化,旨在通過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提升鄉村凝聚力,進而促進鄉村文化發展。其次,電影中還重點強調了鄉風文明的重要性。開展多元化的文化體育活動,培育文明鄉風和優良家風,不斷加強鄉風文明建設,不僅有助于村民道德素質及文化素養提升,而且有利于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再次,《我和我的家鄉》敘事時,除短片《北京好人》之外,其他4部短片都將鄉村旅游經濟的建設穿插在敘事當中,展現了農家樂、特色農產品等鄉村文化產業的發展。最后,《我和我的家鄉》敘事中,還重點描述了社區參與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性。引導和鼓勵村民積極參與鄉村文化建設,能夠增強村民的歸屬感和責任感,促進鄉村治理提質增效。可見,《我和我的家鄉》講述的5個故事雖有各自的主題,但敘事主線都是“鄉村振興”[8]。
5 結語
鄉村文化振興背景下,影視作品如何通過敘事引發觀眾共情,吸引在外人群返鄉,為鄉村振興建設貢獻力量,是影視制作者應思考的重要問題。《我和我的家鄉》是一部具有獨特敘事風格的主旋律影視作品,其主要采取集錦式的敘事結構,突破了以往主旋律影視作品的敘事風格,采取小品化喜劇類型敘事、聚焦民生問題、融入網絡元素,以此弱化感傷因子、滿足觀眾審美需求并展示科技成果;通過設置較強懸念、簡化敘事結構、設計功能化人物,推動敘事發展;以鄉村振興為敘事主線,為觀眾展現了不同地區感人的家鄉故事,在喚醒觀眾思鄉之情的同時,也為推動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將該類型影片創作推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