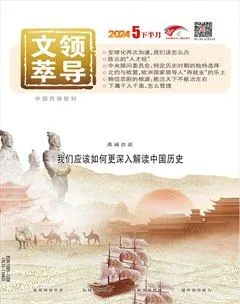“拉美陷阱”真的難以跨越嗎
洪朝偉

“拉美陷阱”(或稱“中等收入陷阱”)是困擾拉美國家和其他一些地區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的長期問題。阿根廷于20世紀60年代就已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60多年過去了,至今沒有邁入發達國家行列。然而,阿根廷總統米萊在參加今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時,卻駁斥了“拉美陷阱”的說法。他認為沒有所謂的“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不尊重私有產權。米萊的這一發言讓人們把目光重新聚焦于“拉美陷阱”。
如何判斷一國是否陷入“拉美陷阱”
20世紀70年代,拉美國家紛紛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此后幾十年里,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卻陷入了困境: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城市化失衡造成環境惡化、失業人口增加、公共服務不足等現象;過度城市化不僅沒有推動經濟持續發展,反而帶來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這種現象被稱為“拉美陷阱”。之后,這一現象也發生在非洲、東南亞、中東等地區。2006年,世界銀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更具普適性的概念。
不論是“拉美陷阱”還是“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都描述了經濟發展的一種困境。當一個經濟體邁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既不能繼續、又難以擺脫以往的增長模式,經濟增長出現大幅波動甚至基本停滯,導致陷入增長的困境難以自拔。長期無法跳出中等收入國家的拉美經濟體,認為自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判斷一個國家陷入了“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一是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屬于中等收入水平。世界銀行目前以人均GNI的閾值來劃分高中低收入國家。目前拉美地區2/3以上的國家屬于中等收入國家。2022年,除安提瓜和巴布達、巴哈馬、巴巴多斯、智利、圭亞那、圣基茨和尼維斯、巴拿馬、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烏拉圭屬于高收入國家外,其余拉美國家均屬于中等收入國家。
二是長期處于中等收入水平,無法跨越到高收入國家行列。多數拉美國家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卻長期無法跨越這一階段。雖然個別國家最后取得了成功,如智利和烏拉圭,但也歷經了40多年的時間,而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等至今仍然處于這一階段。阿根廷常被作為陷入“拉美陷阱”的典型案例。
“拉美陷阱”的主要表現
過去幾十年,拉美地區大多數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整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如下特點:
第一,生產力水平低和經濟脆弱性高形成惡性循環。
一方面,地區國家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級產品部門和采掘業,經濟復雜程度、技術和人力資本投入均較低,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1950年,拉美地區勞動生產率是歐盟的76.05%,到2018年,該數值已經下降到41%。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經濟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初級產品出口模式導致地區經濟脆弱性高,加大了拉美地區經濟增長的波動性,降低了總體增長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61—2022年,去除高收入國家后的拉美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速僅為1.62%。勞動生產率低和經濟脆弱性高相互影響,導致地區難以轉變發展模式,無法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
第二,經濟增長有限與社會不平等疊加。地區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沒有完全轉變成人民的福祉,社會分化較為嚴重。
一是地區財富、收入、受教育機會高度不平等。在財富不平等方面,2021年,拉美地區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77%的家庭財富,而最貧窮的50%人口僅占有總財富的1%。其中,處于頂端1%的人口占據總財富的46%,遠高于歐洲(25%)、東亞(30%)、南亞和東南亞(34%)、北美(35%)的比重。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盡管與2000年相比,目前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拉美地區仍然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區。根據拉美經委會數據,2022年,拉美地區“基尼系數”是0.454,顯著高于經合組織(OECD)國家。在教育不平等方面,盡管近年來拉美地區入學率有所提高,但接受高等教育和高質量中學教育的機會仍然限于特權群體。二是非正規就業占比高,社會脆弱群體比重大。近年來,拉美地區減貧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990—2023年,拉美地區貧困率從51.2%下降到29.1%,但地區非正規就業占比高。2012年至今,地區非正規就業率維持在50%左右的水平。大多數擺脫貧困的人在非正規就業部門工作,由于缺乏保障,失業、疾病等負面沖擊隨時可能導致他們重新陷入貧困。三是社會暴力和犯罪發生率高于其他地區。據統計,全球最危險的50個城市中,有40多個位于拉美地區。
第三,政府公共服務無法滿足新興中產階級的訴求。
減貧擴大了拉美中產階級的比重,新興中產階級不再僅僅滿足于獲得公共服務的機會,而是更關心公共服務的質量。與傳統中產階級相比,新興中產階級消費能力有限,只能訴諸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但政府沒有順應新的社會形勢變化,引發社會抗議事件此起彼伏。此外,腐敗導致民眾對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下降。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來,拉美地區9個國家的20位民選總統因腐敗、失職、被國會解職、民眾抗議等原因提前結束任期。近年來,秘魯的政治動蕩最為極端,在2018年3月至2022年12月間,秘魯共經歷了5位總統。
政治、經濟和社會三重因素
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維度觀察。
第一,政治上“低度民主”的高度脆弱性。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來,拉美地區逐漸建立起民主體制,但地區民主僅僅停留在選舉層面,具有高度脆弱性。首先,拉美地區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有些國家行政權力過大,司法和立法機構獨立性差,導致國家治理能力薄弱,化解政治和社會危機的能力有限。其次,政黨碎片化使得政策推行困難。民主化浪潮提高了大眾參與政治的廣泛性,新興政黨不斷涌現,而政黨碎片化導致總統難以在國會通過重大改革方案。自2001年以來,秘魯歷任總統均無法在國會獲得多數支持。再次,左右勢力輪替執政的鐘擺現象造成政策連續性不足。
第二,經濟上延誤發展轉型時機。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先后經歷了初級產品出口階段、進口替代工業化階段和外向發展模式階段,每個階段的經濟戰略雖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政府沒有伴隨內外環境的改變,適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延誤了轉型時機。從產業結構轉型來看,拉美地區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工業化轉型較為有限:農業占GDP比重從1965年的15.89%下降到1969年的12.2%,工業占比從33.57%上升到35.98%。
第三,社會上過度追求“福利趕超”。與亞洲地區相比,拉美地區社會制度具有明顯“福利趕超”特點,即在經濟發展水平尚未達到既定階段下,過早追求高福利目標,導致社會支出超過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拉美地區在工業化進程中,照搬發達國家福利制度,強化工會作用,對生產部門實行高工資保護等,通過高福利承諾吸引選民,導致地區社會公共支出占GDP比重過高。
如果拉美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擺脫政治因素的干擾,抓住時機,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主動適時調整經濟發展模式,“拉美陷阱”也就不會存在。筆者認為,阿根廷總統米萊否認“拉美陷阱”的存在,意在強調“拉美陷阱”是人為因素所致,不具有客觀必然性。然而,米萊所提倡的全盤自由化就能讓阿根廷擺脫“拉美陷阱”嗎?我們拭目以待。
(摘自《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