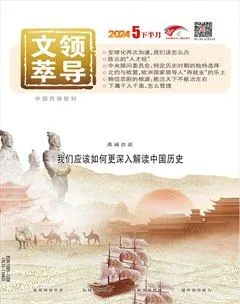黃宗羲的人生選擇
王淼

明清易代之際,有很多文人士大夫自覺地選擇與異族統治者武裝對抗的道路。夏完淳所謂:“長安無限屠刀肆,猶有吹簫擊筑人。”黃宗羲即是一位“吹簫擊筑人”。
黨 人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世稱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天啟年間曾出任御史一職。黃尊素在北京任職兩年,因彈劾魏忠賢被削職歸鄉。天啟六年,黨禍爆發,黃尊素受酷刑而死,彼時的黃宗羲才17歲。
崇禎元年,黃宗羲來到北京,他是為指控將父親陷害致死的直接責任人而來,指控的對象主要是曹欽程、李實、許顯純、崔應元四人。當初這四人分工坐實,將黃尊素迫害致死。
刑部會審許顯純、崔應元之日,許、崔二人甫一出現,早已等候在此的黃宗羲突然躍起,從袖中拔出一柄長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刺向走在前面的許顯純,當場令其“血流被體”。一個月后,會審李實等人,同樣的一幕再次上演。更讓人驚駭的是,當刑部提審兩個曾經對黃尊素等人刑訊逼供的獄卒時,黃宗羲與幾個同難的東林黨人的后人一起沖上去,以棍棒共棰之,將兩人當場打死。
黃宗羲“義勇勃發,自分一死,沖仇人胸”的作為,讓他一時名震天下。當他為父伸冤后返回故里時,四方名士紛紛迎接,并均以做他的朋友感到光榮。崇禎皇帝念及黃宗羲是忠烈之后,并沒有追究他擅殺的責任,自此之后,黃宗羲在士林聲名鵲起。
復社是明末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團體之一。像那些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青年才俊一樣,黃宗羲也加入復社,多次參加復社重大的集體活動并與復社的頭面人物諸如陳貞慧、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等人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復社的歲月雖然很短暫,卻令黃宗羲受益終生。與復社才子們的交往,讓他眼界大開。與冒辟疆、侯方域們的張揚不羈相比,黃宗羲顯得內斂而持重,缺少浪漫的情調,但他從復社才子們的身上看到了一種奮發進取的力量。
游 俠
1644年的甲申之變,對于復社所有的成員都是一個命運轉折點。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中,復社的死敵阮大鋮成為實際的掌權者,黃宗羲也成為阮大鋮重點追捕的對象。幸運的是,黃宗羲在公差前來抓捕之前逃離南京,當他結束流亡,回到家鄉時,弘光朝廷已然傾覆。其后不久,他的老師劉宗周即絕食身亡,黃宗羲自此進入了“天崩地解”的年代,而他也正式承擔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變賣家產,組織義軍,踏上了武裝抗清的道路。
從35歲到50歲,是黃宗羲積極獻身于抗清運動的15年。這15年間,他先是與兄弟一起組建“世忠營”,“世忠營”戰敗瓦解,他又加入魯王的政權,但只是“以布衣參軍事”,與魯王的流亡政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對于抗清的歲月,黃宗羲其實不是不明白,“以一二士子率鄉愚以抗方張之敵,是以羊投虎,螳臂當車”。但對于他來說,“反清”不是為了“復明”,他要以一己的犧牲,讓異族的入侵者看到泱泱中華并非無人。
儒 林
隨著魯王政權的式微,鄭成功攻打南京功虧一簣,尤其是老友兼同志的錢謙益等人先后去世,黃宗羲逐漸陷入四顧茫然的孤絕境地。
漸入老境的黃宗羲變得心似止水,他終于主動放棄武裝抗清,進而一個人躲進山中,離群索居。
離群索居的黃宗羲開始從根本上反思明朝衰亡的原因,并由明朝推及歷朝歷代興亡的規律。正是從這個時期起,對抗者黃宗羲漸行漸遠,思想家黃宗羲呼之欲出。黃宗羲晚年總結平生的作為,將一生劃分為三個階段:
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游俠,終廁之于儒林。其為人也,蓋三變而至今。
所謂“黨人”,是指他加入復社的那一段歲月;所謂“游俠”,是指明朝滅亡后他武裝抗清的那一段歲月;所謂“儒林”,則是指五十歲以后,一個與往昔迥然不同的黃宗羲誕生。這是一個新的思想家黃宗羲,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深度剖析,將批判目標直指王朝體制。
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君為“大害”的具體表現,就是“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就是“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
黃宗羲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所以,應該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因為只有“公治”才能保護“公利”。這種樸素的民主思想,在當時的中國足以振聾發聵。
“國可滅,史不可滅”
正是因為跳出一家一姓的朝代興亡的視域,黃宗羲才不會成為一個愚忠的腐儒,更不會成為一個只愛大明王朝的“愛國者”,他才會對康熙皇帝產生一定程度的好感。
黃宗羲既驚異于康熙朝政治的清明,對康熙皇帝本人的為政寬仁,以及對知識和文化的尊重也深表佩服。與之同時,黃宗羲也對他受到的禮遇心懷感激,康熙皇帝下詔征“博學鴻儒”,首先想到的就是黃宗羲,清朝修《明史》,康熙皇帝命地方官親自出面禮請黃宗羲。
晚年的黃宗羲是在一種寬容、平和的心境中度過的,他積極投身到教育等各項公益事業中去。雖然黃宗羲本人并不出面,但他卻讓兒子參與《明史》的編撰,為的是“國可滅,史不可滅”。康熙二十七年,79歲的黃宗羲立下“裸葬”的遺囑。
公元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逝世。離世前五天,他留下這樣的文字:
年紀到此,可死;自反平生雖無善狀,亦無惡狀,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
對于黃宗羲來說,有了這四個“可死”,死非但不以為苦,反而足以為樂。
(摘自《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