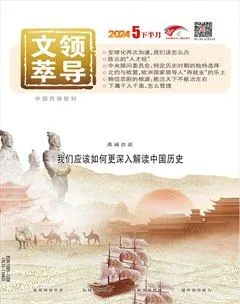楊萬里的“請托信”
王瑞來

在士大夫政治體制下,宋代士大夫為了保證精英治國,并防止官滿為患,精心設(shè)計了官僚選拔制度。士人入仕后,首先成為選人,在選人七階內(nèi)循資、磨勘、考課,在當(dāng)時人所說的“選海”之中翻滾,論資排輩,耗時費日。在此期間,選人必須忍氣吞聲,小心翼翼,接受地位與待遇低下的現(xiàn)實。對于選人來說,做到這些還不困難,此時的命運主要在自己手中把握。但脫離選海,升遷為京官,則猶如鯉魚躍龍門,十分艱難,需要好風(fēng)憑借力。
宋朝制度規(guī)定,選人改升京官需要有五份薦舉信。這五份薦舉信并不是隨便找個官僚就可以寫的,其中的三份必須要由選人直接主管的頂頭上司來提供。有條件的五份薦舉信是政府控制官員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一道重要關(guān)口,也是下層官員通往光明仕途的必經(jīng)瓶頸。這樣的制度設(shè)計無疑是理想的。不過,正如無菌狀態(tài)只呈現(xiàn)于真空一樣,理想的制度設(shè)計,一旦投放到實際政治運作之中,便會變形走樣。
從楊萬里為自己子嗣親戚尋求薦舉、斡旋改官的事實,可窺一斑以見全豹。
楊萬里本人,可以說是在科舉這條狹路上沖殺出的為數(shù)不多的幸運者之一。審視他的狹路奔波,22歲鄉(xiāng)舉失敗,24歲再試,方得取解,但在25歲應(yīng)試禮部,又名落孫山。不屈不撓,27歲再獲鄉(xiāng)解,遂于28歲以并不年輕的年齡終得登第。其間頗歷曲折,備嘗艱辛。是年為紹興二十四年(1154),此時南宋盡管立國未滿三十年,但仕途已顯擁擠。
登第后,楊萬里成為最低一級的選人左迪功郎,授以贛州司戶參軍。不過,由于僧多粥少,他還不能立即赴任,待闕兩年后,方攜父母與家人赴任。32歲時楊萬里在贛州司戶參軍任滿,被授以零陵縣丞,又經(jīng)歷一年多歸鄉(xiāng)待闕后,再次攜父母與家人赴任。
在零陵縣丞任上,楊萬里一直做到37歲。在此期間,楊萬里十分幸運的是,結(jié)識了因貶謫居于永州的名臣張浚和他的兒子理學(xué)家張栻,從而得以師事張浚。此后政治形勢逆轉(zhuǎn),高宗禪讓,孝宗即位,起用主戰(zhàn)派張浚出任宰相。大概張浚動用了其宰相的權(quán)力,以堂除的方式,將零陵縣丞任滿赴調(diào)的門人楊萬里改秩左宣教郎,任命為臨安府府學(xué)教授。從此,楊萬里得以脫出選海,但生活上還一時未能擺脫貧困。
由于有過這種親身經(jīng)歷,楊萬里在官場具有一定的地位之后,便竭力提攜幫助子嗣親屬盡早脫離選海。他為兒子、親屬或者門人請求破白、合尖等薦舉狀的書信,或是請求關(guān)照的書信,以及求得薦舉狀后的感謝信函,就達100多通。
對于并不太熟的人,楊萬里要先去信套近乎,往往等到與對方有過兩三次通信往復(fù)之后,方提出自己的請求。可以說為兒子、親屬或者門人請托,幾乎成了楊萬里晚年家居的主要事情之一。由于是寫給不同的人,所以他為了省事,用的幾乎都是同樣的詞語。晚年的楊萬里,身體并不好,右臂麻痹,不能寫字,就口述讓兒子或女婿代筆。以晚年帶病之身,寫下幾百封請托書信,也著實難為了他。
楊萬里有著詩人的狂放,性格倔強。盡管如此,數(shù)百封書信的事實表明楊萬里的不得已。三個兒子自不待言,其他人也不是與楊萬里毫無關(guān)系。他們之中,有的是楊萬里妻子的親屬,有的是楊萬里兒子的親屬,還有就是利益相牽的鄉(xiāng)黨。
盡管楊萬里已經(jīng)退休家居,但幾十年的為官生涯,特別是他曾經(jīng)在淳熙十二年(1185)擔(dān)任吏部郎中期間,應(yīng)宰相王淮請求寫下過《淳熙薦士錄》,一口氣提名推薦了60人。這些都成為楊萬里退休后推薦子嗣親屬時可資利用的人情資源。
實際上,對于楊萬里來說,在張口求人時,心理也很復(fù)雜。長子的妻兄求他向一位不認識的官員寫信求薦,楊萬里回信說:“陳漕無半面,不曾通書,亦不曾作幼輿托庇之書。彼此無情分,豈可干求,談何容易!不惜取辱,但無益耳。”
根據(jù)制度規(guī)定,在五通舉狀中,頂頭上司州府、監(jiān)司長官的推薦信是必須要有的。在朝廷中,楊萬里熟識的高官并不乏人。然而,年輩較淺的地方官員,楊萬里則并不是都很熟悉。這些書信,表達多有不同。含蓄而間接的,表明楊萬里對其人不甚熟識,或者說交情尚淺。比較直言不諱請求的,表明楊萬里對該人相當(dāng)熟悉,有一定交情,甚至是曾有恩于對方。請求對方,也屬于尋求一種利益的回饋。
在楊萬里的不懈斡旋之下,長子楊長孺終于在幾年內(nèi)連續(xù)升遷,脫離選海,踏上順利的仕途。斡旋成功,還有掃尾工作要做。這就是必須向推薦者致謝。因為這并非一錘子買賣,楊萬里還有其他兒子和親友需要這些在任官僚的推薦。這樣的書信不少,我們僅看其中的一封,《答周丞相賀長男改秩幼子中銓》:
長男難矣,初臨壯縣之萬家;幼子斐然,偶試?yán)舨慷坏谩C裰嘈遥褙仕?埼夜^章破白之恩,及平日口講拾青之誨。率俾先人之門戶,未荒數(shù)畝之蓬蒿。藏之中心,感焉至骨。
這一封是楊萬里寫給周必大的感謝信。關(guān)于這兩個同鄉(xiāng)間的關(guān)系,《宋史·楊萬里傳》提及這樣一件事可以窺見:“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言,由此不大用。”盡管據(jù)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記載,在楊萬里晚年還鄉(xiāng)后二人交往親密,但于往事不可能毫無芥蒂。不過,楊萬里為了自己兒子的前程,不得不硬著頭皮求周必大寫第一份推薦信來“破白”。在兩個兒子分別因此而改官和中銓之后,還寫信用了“感焉至骨”這樣夸張的表達,表示刻骨銘心的感恩。
楊萬里僅僅為長子一人,就寫下了多達20封直接求情的書信。這是一個縮影,不僅僅是一件個案。連地位與名望相當(dāng)高的楊萬里都要低聲下氣地求人,甚至也有達不到目的失敗之時,可見尋求舉主之難。
朱熹在拒絕一個選人求薦的回信中寫道:“朝廷設(shè)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dāng)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dāng)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dāng)自炫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后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yīng)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眾謂當(dāng)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
楊萬里在推薦朱熹時,就說過朱熹“性近于狷介”。然而即使是“性近于狷介”的朱熹,其實同楊萬里一樣,也會礙于人情來推薦一些人。朱熹信中的“其在閑居,非無親舊”便已透露出這一事實。至于被他拒絕的人,大概是還未能進入他的“親舊”圈子。
越走越窄的仕途將選人逼向奔競之路。普通選人的官闕名額為宗室出身的選人所侵占,這便使得“員多闕少”的狀況更為嚴(yán)重。
宋朝皇帝鑒于歷史教訓(xùn),對宗室入官,特別是成為高官加以限制,但這方面在北宋后期已經(jīng)開始松動。到了南宋,為了維系正統(tǒng),興旺趙氏皇族,采取了更多的優(yōu)待宗室的政策。不僅有趙汝愚那樣的手握大權(quán)的高官出現(xiàn),還有更多通過科舉等途徑成為低級官僚選人的宗室子弟。宗室入官,加之歷來就有的恩蔭入官,與進士出身的選人合流,使得選海更為擁擠。勢家出身的選人浮在選海的上層,宗室出身的選人浮在選海的中層,普通無權(quán)無勢無背景的選人則沉淀于選海的底層,難以躍出海面。
(摘自《士人走向民間:宋元變革與社會轉(zhuǎ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