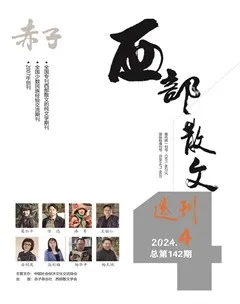高彩梅散文評論小輯
高彩梅
牧歌韻味
我有幸讀了阿古拉泰老師的散文集———《誰是這個世界的富翁》。我被出生于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的阿古拉泰老師那種激情四溢,詩意盎然的筆觸深深感染。他讓我感悟到:草原像大海。草原人的胸懷像海一樣寬闊。草原人有海一樣澎湃的激情,草原人有海一樣愛的深沉。
阿古拉泰曾自謙:他是故鄉胸膛上萌生的小草。是草原溫馨的懷抱,滋養了他綠色的童年和青春的夢想,也給予了倔強和執著的追求。他愿為草原媽媽綠色、繁榮而獻身。他將自己一周歲的小兒子取名“塔拉”。讓這名字時常提醒兒子無論將來翱翔在哪一片天空,都不能忘記,他起飛于一片綠茵茵的草地……阿古拉泰老師那種草原的情懷,彪炳自己的文化人格,展示自己的藝術魅力,令人不得不佩服。讀他的散文入心入肺、心曠神怡。他那種熾熱、噴突 、豪情、 坦誠、 真率顯露在他的散文里,給人一種遐想:那晶瑩剔透的晨露盈動在綠茵茵的草葉上,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清新的綠風,那么溫柔,那么溫馨。潔白的云朵綴在茫茫的草原上,讓人感覺在仙境放牧,靈魂得到陶冶凈化!
一、阿古拉泰散文的語言藝術
美國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認為文學應該這樣∶“作家應該忠實于自己的體驗,正直而誠實,他根據自己的體驗創造出來的作品應該比實際的事物更真實,這樣,人們才可以從中得到寶貴的啟迪。”對于文學語言,汪曾祺老先生也這樣認為: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是浸透了內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如阿古拉泰老師所說:散文是文學中最較勁、最不省油、最要真功夫的一種。哪怕千字短文,對執筆者的思想、才情都是嚴峻的考驗。他那飄灑俊逸,情真意切,閃爍著智慧光芒的句子被賦予更多的個人豐富的情感體驗,蘊涵著震撼人心的心靈情愫。文采斐然。獨特的個性詩話語言,處處引人入勝,感染力極強!將人物刻畫栩栩如生。如《不老艾青》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此次造訪,除了工作,還有一個心愿,求艾老一幅題詞以警策稚嫩的詩情。不敢跟艾老直說,怕就此打住便從此無望,于是竊竊又怯怯地求高瑛老師。哪知高瑛老師揭秘似的沖出書房高喊:“老艾,小蒙古請你題個條幅……”嚇出了我一頭的汗。足有半分鐘,艾老像誦詩般地突出一句:“我的字又不好,有什么用!”我的心一揪:這下完了。又過了半分鐘,“明天來吧!”這一句,像《黎明的通知》一樣蕩氣回腸, 入心入肺。心曠神怡、喜出望外,卻不知該走還是該留。不走吧,怎忍心無端侵占先生寶貴的時間;走吧,又怕這突來的喜氣還未扎下根便急匆匆帶走,瞬息揮發掉了怎么辦?”再如《誰是這個世界的富翁》一文中,描寫烏蘭托嘎的歌像品味一壺剛剛溫過的綿綿的、醇醇的酒,它徐徐沁入你的心肺,又緩緩奔流在你的血脈中。像他的人,不緊不慢,榮辱不驚,舒坦中,永遠讓你心存一絲期待,一番熱切,一陣踏實,一份感動。歌聲嘎然,那情愫,還裊裊地縈繞于心。甘洌,清純,如夢,似霧。讀阿古拉泰老師的這段文字, 我仿佛身臨其境于音樂的現場。音樂的精靈點讀我的心靈,讓我享受這夢幻的天籟之音! 詩性的筆調綻放著別樣的韻味,滲透我每個細胞當中,漸有心靈的回應,靈魂深處的一種耐人尋味的感悟出生。
二、人文情感藝術
阿古拉泰老師有著文人的氣質、氣韻。如古人云:才華外現,形成氣質;才華內斂,形成氣韻。給人一種陽剛、儒雅、博學、有品位而魅力無窮的男性。有道是:腹有詩書氣自華嘛!正因阿古拉泰老師是一個坦誠,真率,視友情如命的詩人,散文家。那份深沉的愛,那份濃濃的親情流露筆端,那些飽蘸深情的肺腑之言,給人一種親切與溫馨,讓我想起明·馮夢龍的一句話: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結者,謂之知心。能與阿古拉泰老師成為知己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阿古拉泰老師《棕櫚常綠憶晨聲》文中,能感受到阿古拉泰老師與漢族詩友晨聲”血脈親人” 情感,親如兄弟最讓人感動的是阿古拉泰老師從內蒙古到廣州親自為逝去的詩友晨聲上墳悼詩“……蒙古包沒擁抱過你的身軀 千里草原頓失十二分詩意 船兒還在浪上泊著 心的桅桿卻已經失去 駿馬在晚風中佇立|斷了弦的馬頭琴默然失語……”低歌痛吟,那種悲痛緬懷是真情啼血的呼喚!再如阿古拉泰老師在《雁北飛》對自己的同室同庚哥們雁北詩人:“驚蟄眼看又到了……舉目遙望,長天廖廓;閉目思忖,十二年了,人雖故去,雁北兄的音容時常浮現在眼前,輕煙燈影,耳鬢廝磨……雁北個性鮮明,是一位超凡脫俗披荊斬棘的詩人;一個有眼光,有責任心和使命感的好編輯;又是一個倜儻,灑脫,標致,美風儀的帥小伙兒,恰在風華正茂之時離開人間。讓人讀了,長痛不已。 阿古拉泰老師在《表嫂》一文中,對新婚的表嫂描寫:“怯生生地站在角落里,人多是有些局促,人少時找著縫隙搭話,小心翼翼地分辨這一個個陌生的親人。”把剛結婚過少婦的嬌羞,賢惠躍然紙上。從他散文里,可以看出 阿古拉泰老師對人,對文學的至愛,對蒼莽的蒙古大地的赤誠熱愛,對叱咤風云,所向披靡,文蹈武略的成吉思汗的敬仰。《以海的目光仰望一座高原》中,寫成吉思汗以他的智勇,以他海一樣的胸懷征服著世界,在歐亞大陸上演了一場令人瞠目的歷史話劇。成吉思汗把東方文明傳遞給西方,讓散亂的文明之火燃燒成太陽,溫暖了世界! 以海的目光仰望,以潮水般的馬蹄聲怒放,為這雄奇的高原?因為草原滋養造就一個詩人,散文家的這種襟懷。
三、阿古拉泰散文的牧歌韻味
蒙古音樂深沉,悠遠,曠達,自信。看阿古拉泰散文,如一首首牧歌,那些優美的音符,清純,溫馨而深情。如同一杯杯馬奶酒,純凈,透明晶瑩散發著濃烈的芬芳和香甜。似微風中,那點綴草原的小花,似雨后懸掛草原的彩虹,似綴落草尖的晨露。《以海的目光仰望一座高原》中寫道:彎刀叢生,像一葉葉牧草,在空中呼呼生風。草葉的露珠,就像牧人那水晶的心靈一樣的透明。在《靜謐與歡樂》中,藝術生命像牧草一樣越來越綠,牧歌韻味使阿古拉泰的散文有了濃郁的草原氣息。讓我對蒙古草原狼有一種著了魔的恐懼、敬畏和癡迷。蒙古狼,對我來說,竟然潛伏著、承載著一種如此巨大的吸引力?這種看不見、摸不著,虛無卻又堅固的東西,可能就是我心靈中的崇拜物或原始圖騰。或許自己阿古拉泰散文的牧歌韻味可能已經闖入草原民族的精神領域。
野性的呼喚回歸于真實的自然
——讀中國首部純動物小說《最著迷野生動物故事》有感
當你徜徉于作家雨街筆下的純動物小說——《最著迷野生動物故事》,你會感到一股清新而又淳樸的風撲面而來,世俗的羈絆,隨之層層剝落。
作家雨街的文字有著獨特的風格,文筆清新雋永,樸素自然,猶如一曲曲清音撥弄心弦,時而激蕩,時而低緩。詩意盎然的句子,娓娓道來,不急不緩。當你手指觸摸著這些方形的文字,流連忘返,不愿離去。
你會驚喜地發現,那么多栩栩如生的動物就行走在你的身邊。比如,小象伊蘭堡、野牛比爾、憨蛇盧彎彎等,它們是集“動物性”與“人性”于一身的,作者巧妙地將動物與人類共存的憐愛、善良、守信、勇敢、合作、尊嚴、貪婪、殘忍、陰險、狡詐、背叛等特點,藝術地移植在一起,得到淋漓盡致地展現。站在一個高度上審視,既合情又合理。而動物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性、捕獵生存,無一不彰顯著生命中最原始的本色,野性的呼喚回歸于真實的自然。
一種真切的生命體驗激蕩著你,動物的原生態引領著你,對于生命的感悟、人生價值觀的取向,深深地觸及著你的靈魂,滌蕩著你的心靈。如《小章魚拉爾》一文中,在海洋生物中,章魚拉爾不是很引人注目的,是很普通的魚類。在這樣一個龐大的海洋生存環境中,為了生存,與勁敵多次交鋒,每次幾乎都是九死一生。章魚拉爾之所以能夠幸存,不單單依靠自己睿智的頭腦和生存的技能,更多的是團結友愛、不計前嫌、善良誠信,豁達大度。也許你要反問,我們生存的意義何在?價值觀的取向呢?
在人們道德行為日益滑坡的現實生活中,比照之下,重新審視我們的生存狀態、生存觀念以及生存價值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是本書的高明之處。
與遠離大自然的人們而言,每走進一種動物抑或一個故事的場景,都是新奇的、興奮的。而作者每一次推到讀者面前的動物形象,不像櫥窗里的模特,呆板、機械、僵硬,而是生機盎然、活潑靈動的。作者用形象、生動、傳神的語言,讓每一個動物形象豐滿,有血有肉。不論是大處著眼,還是小處落筆。總能全方位地、多角度地,讓動物活生生地立于眼前,仿佛你也置身其中。這樣的寫法,在全國也不多見,確實令人叫絕!
作者在描寫“蜜獾”等食肉動物,不僅從正面粗線條的勾勒,給讀者一個大致的輪廓,還從側面用形象化的語言,從細部刻畫。多次運用比喻等修辭手法,這樣的語言極具張力,力透紙背。對于蜜獾等不太熟知的動物,又遠離人們視線,通過詳盡的描述,精確的定位,人們會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過目一次,終生難忘。
再如,狼王辛格與灰熊的決斗,以及其他動物之間展開的角逐。作者先是鋪開筆墨來大勢渲染背景,為營造氛圍而蓄勢,為決斗的主角做好鋪墊。在氣勢恢宏的大草原抑或令人向往的美麗曠野,斗士們依次登場。一場場血腥的廝殺,頃刻間爆發。廝殺中充滿著智慧,血腥中充滿著貪婪……
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無不遵循著這一古老而又現代的自然法則。
除此之外,作者更注重打斗過程的描寫,連續運用極富有動作行為、狀態的動詞來呈現,如躥、躍、撲、摁、縱,隆起、傾斜、壓下、指向等,將廝殺過程連貫得一氣呵成,真切的歷歷在目。如果單獨來欣賞,絕對是一幕令人叫絕的武打動作片。諸如這樣的塑造動物形象和極具傳神的語言,小說中隨處可見。這也是中小學生為之癡迷的原因之一。
當你流連忘返于動物故事的情節中,往往會被一些內容所吸引。你會驚奇地發現作品不僅僅局限于一些故事情節與矛盾沖突講述,更多的是將一些科普知識寓于其中。在解讀故事、揭露矛盾沖突的同時,展現出動物生活的原始習性、生命樣態、文化密碼、感情天地、性格特征、理想追求等。作者將這些知識分條析縷地貫穿其中,對于中小學生的閱讀是非常有益的。
雨街是河北經濟日報記者,曾獲中國年度最佳短篇小說獎,中國年度最佳散文獎,中國當代詩歌獎。出版中長篇小說多部。
《詩度華年》的溫度與韻致
當我手捧這本散發著油墨清香,厚重的,劉建光(九曲黃河)先生的詩集《詩度華年》時,有點迫不及待,想一口氣讀完。這部詩集作品取材詩人身邊的物事,詩人始終抱著一顆赤子之心,用詩作詮釋自己的初心、信仰與情懷,宣泄了超現實的情緒,表現出一種人格的清純、意志的堅忍和思想的豐厚。
縱覽詩壇, 在當代的寫作中,很多人生活于現實的空間,而劉建光先生則存在超現實或者游走于現實和超現實的交叉點上,主要體現于《詩度華年》的溫度與詩韻。在這個時代,有時超現實比現實更真實,更有穿透力、張力,這就是藝術的可貴之處,也是劉建光(九曲黃河)先生的詩的獨特價值所在。
生命鄉土的溫度
細細品讀詩集中的每一首詩,如《疼痛》《母親的一雙手》《悼岳母》《愛》《媽媽在鄉下》等寫給母親詩篇,均顯現了母子深情。這份愛不僅對母親的養育之恩感激,更多的是對母親堅韌、隱忍品質的崇敬。寫母親自然也是寫故土,詩人對母親的愛融于對鄉土深情的愛。如詩篇《老屋》以一種浪漫敘事抒情歌吟的方式,唱出了一個本真而高遠的詩意世界。詩里有濃厚的故土意識和家園情結,有揮之不去的“鄉愁”的沖動,隨性而至,即事即景,但不濫觴于抒情,而再克制地敘寫,把詩意引向某種超現實的境界,詩人也常常將故土作為牧養詩歌的營養地。這種基地遼闊壯美,成為一種格局與視野,從而催生獨特,更能催生一種創作的自信感。如果沒有經歷過刻骨銘心,很難表現出關于烏托邦的虛幻想象。詩人帶著輕輕的感傷和堅韌的希望,同時又充滿生命的活力與質感這樣贊道:“老屋/你在我的生命里/不是過客/而是一首根植血脈的不老情歌。”從前讀最早《詩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小雅,采薇》中的故鄉之詠。而九曲黃河的詩篇《高家堡》也寫出了故鄉所召喚、賜予一個離鄉游子發出的百感交集的嘆息。“剪斷臍帶/一步一步離開家鄉/八百里西口路/八個日日夜夜/奶奶挑著全家/媽媽挑著我/高家堡/從此烙在了記憶深處/黃河幾字灣落成了新的家園。”從心靈暖意的詩句呈現中,盡顯一個詩人的成熟。
深藏詩韻的心魂
劉建光先生是頗有實力、洞察力的詩人。作為一個“捕夢者”營造一個絕世、繽紛的‘幻想世界。在某種意義說,夢境與幻想是劉建光先生詩歌的深淵與動力。如《 風吹綠了夢想》中這樣寫道:“雨水的夢在泥土里/ 翅膀的夢在藍天里 /江河的夢在大海里/ 我的夢/ 在一朵桃花里/ 在一首小詩里/ 在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里”“草尖把夢搖在春風里/ 明月把夢寄托在相思里/母親把夢開在/兩畝玉米地和一頭小肥豬里……”這首詩中,詩人敏感動情于生命、自然、愛和生活淳樸之美,以沉吟低唱或歡歌贊嘆,讓人回想起詩歌來到人間的最初理由。又如《 繆斯之戀》這首詩,詩人始終恪守著內心的詩歌信仰,保持著自己的藝術性和創造力,他的詩意象純凈、筆觸細膩、思致深沉,既對美好事物,也對現實生存,既有神秘內傾的情感關注,也有直擊本相的哲學覺解。《荒度》一詩中,這些外在的意象符號“夕陽”“流水”與主觀的情感抒發,人生才能真正充實完美。
劉建光始終保持對修辭的高度敏感,并用致密的意象與沉郁主題抵達詩歌的本源。讀他的詩每次都會在語言修辭中給人思想的撞擊和提升。又如詩篇《夜路》:“在夜晚走路/我會把每一顆星星/都想象成燈/把每一處燈火/都想象成美好”詩人從生活中掘發詩意,揮灑激情,透過生活表象進行精神探究,他說:“一群人走路/ 走著走著就走出了道路/ 一個人走路 /走著走著就成了坐標”這充滿哲思味道的詩句,是詩人咀人世嚼酸甜苦辣后,豐沛智慧的吐露。如詩《我是一個趕路人》“在季節之末/儲存一抹綠色/在雪花來臨之前/儲存/一點熱量/我是一個趕路的人/我得備足水和干糧/我是一個怕冷的人/ 我得備足溫暖和希望”情感飽滿的詩句,把人引向思致的深處,為讀者展現出詩人另外一種豐饒的靈魂。詩篇《九峰山追夢》,詩中的畫面、場景和細節,在藝術的神奇筆端里,一場夢往往具有幻化的色彩,牽連詩人的情感和想象。酒圣李白“把胸中的鳥氣吐成萬千詩行”大概在一首詩中更能照見詩人的內心處境,能引發某種心理情境,形諸筆墨,自然會帶來某種新異的效果。
多樣獨特的詩美
作為多重身份的劉建光先生,賦予他的詩歌以多樣性。又因詩人有深厚的文學造詣才會詩寫起來更加游刃有余。他創作了一些題圖詩如《黑暗與光明》“詩情豐富畫意,畫景渲染詩境,兩者相得益彰,獲致一種精妙”的藝術效果;一些寫懷鄉、念友與游歷的古體詩詞。語言凝練,意境優美,詩人游走于新舊體式詩之間,得心應手,給我們呈現出色彩繽紛的唯美境界。另,《手機沒電了》這首詩短短的三句話,去掉抒情,用簡單、樸實、日常微觀敘事和近乎“瘦削骨感”的語言直擊生活的事實與本真。
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當今豐盛的物質,劉建光偏偏選擇了詩歌這樣的心靈棲息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不愿放棄對一種有精神風度生活的向往。沒有詩歌,這個世界就會少很多真實的性情、優雅的氣度。當乏力、貧血的文學遍地,我尤為看重詩歌中那種有重量、有來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長的經驗與感受。確實,劉建光不僅要強化自己寫作中的及物能力,還要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情感溫度的人,唯有如此,詩歌才有可能再次感動讀者。他的詩里,總是藏著他對事物的摯愛之心,這就是詩歌的情感,或者說,這就是詩歌的體溫。
高原青楓萬里青
——讀王萬里詩集《高原青楓》有感
作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王萬里,不是一個可以簡單歸類和簡單認知的詩人。從2011年起,他的詩歌接連二三地出現在《人民日報》《詩刊》等國家級報刊上。他的詩歌寫作及其藝術,在“西部詩歌”領域顯示出獨到而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他成為一個具有經典性品質的詩人。近年來在當代詩歌進程中,無論是“先鋒性寫作”,還是“常態性寫作”,幾乎處于停滯狀態。而王萬里這位聳立在中國北高原上的青楓,偉岸、挺拔、擎宇蒼穹,氣宇軒昂。“枝條擂起風云的吶喊/荒山峻嶺展開綠色情懷”“根系把大山捆在一起/雄姿跨越千里世紀”。讀他的詩,你可以感受到一種強大的生命沖擊力。像黃河波濤,風起云涌;像纖纖小草,在風雨磨礪中始終盛開的絢麗的春天。
王萬里是一個頗具男人氣質和男人胸懷的人。讀他這部詩集,能感受到一個強勢的高原人在中國北高原上行走與思考。他的精神與青楓燃成璀璨一片。他對自己身經目擊的一切都有詩意的沉思,有深情的表達。正如著名詩人李小雨所說:“他的詩,既有黃土高原的蒼涼渾厚,又有塞北草原長調的遼闊平靜,更隱含著如大海波浪般起伏的娓娓深情。”中國是詩歌大國,雖然詩歌情懷在很多人心里依然存在,但讀詩的人卻越來越少,原因就是詩歌的情懷空洞,心靈缺席,缺乏最重要的精神命脈。王萬里的詩,卻保持著尖銳的發現,用語言解析生命,用靈魂感知靈魂。
王萬里有著較高的生活與藝術的雙重積累,他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拼打生活幾十年,從事過售貨員等多種基層工作,擔任過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到縣處級領導,打造民營企業團隊,下海經商......多種實踐磨煉了人生,積淀了思想,鑄就了超乎常人的毅力與勤奮。他從2010年8月開始寫詩。短短4年。竟有三部詩集——《松風萬里》《高原青楓》《北方的時光》與讀者見面。成為西部的高產詩人。他的詩歌寫作,獨特地將陜北的高原文化與內蒙古的草原文化和自己的情感融合在一起,以現代意識透視真正意義上的西部精神與西部美學,他的誠實與才情令人感佩。“殘垣斷壁的土窯洞/站著一個守衛家的破門/它為先輩們敞開心扉/年年歲歲目送千里遠行/星移斗轉遙望歸來的游子/閉合回位抵御霜雪寒風/”《陜北故居》。詩人善于捕捉異乎尋常的事物,在“土窯洞的破門”中發現了深刻的內涵。他不是簡單的描摹,而是沉浸在感情與心靈的洞察之中;他從不空洞地抒情,而是扎根那些細微的感受,給人一種深刻的力量。當詩人回到陜北故居,目睹了先輩們當年用過的石碾、石磨以及推碾磨踩下的小路時,寫道:“一代一代的莊稼人/把高山碾成田園/把汗水磨成江河/至今/我的骨髓里有小米的醇香/血液里流淌著五谷雜糧/石頭仍然生長我的力量/”《山村記憶》。王萬里以簡明樸素的文筆寫出了寬闊堅韌,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我”。這些寫故土的詩看似寫物,背后卻分明在寫“自己”。他的詩在生活的現場有感而發,尤其是面對故土、故人時,他的詩性便清晰可見。
細細品讀王萬里的詩,會發現詩人有神來之筆,具有一種把常人覺得抽象的事物變得具體、生動起來的能力。比如“馬蹄擂起激越的鼓點/深深淺淺踩響觀眾的心弦。”又如他寫草原上的蒙古包:“綠草地上扣著數不清的銀碗/不需要用鑰匙打開門窗/東南西北景色一樣/雪白的花朵/村莊連著村莊/瑪尼宏的彩旗獵獵飄揚”。這是多么美妙的草原景致啊!這樣的語言無不飽含鮮活、別致、潔凈、具有打擊心弦的力度。類似這樣神奇的表述在他的詩集里可謂俯拾皆是。如:《放飛夢想》(獻給第二屆國際那達慕大會的贊歌),“火熱的情感跳躍在馬背/雄壯蹄聲飛起草原狂歡/矯健的翅膀向世界騰飛/鮮花舉起最美的笑臉”。不僅寫出了馬背民族的雄健,而且詩化的語言表達了中國經濟騰飛世界。他的詩不是外在描摹而是內在的情感與心靈的洞察。有鮮明的時代感和精神啟示性,其語言表達得透徹確切,頗有動人的魅力。還有《低一點再低一點》《文字里的月光》《春日時光》等作品都獨具詩才,他將思維和想象,變成紛呈意象的文字、至深的生命體驗與強烈的心理感,頓悟浸透了感性和理性,經他心靈的熔煉,引入了對生命的哲學追問,有一種心智放達與高遠,在時下詩壇并不多見。
詩人詩歌敘述的節制和節奏避免了散文的繁冗與拖沓,筆法簡潔,境界空靈,尤其是對祖籍陜北的敘事與那些形而上學思辨、思考的文風對比,形成了特有的風格。“渾厚的心靈/掛著鉛的沉重”《荒野上一個老人》。詩人讓一位離鄉背井獨返荒野的老人的獨特景致呈現出一份生命的沉重,境界舒放,格高思遠,精準傳神地寫出了人間真情。同時詩人對當今龐大卑微群體的生存表現出極大的憂慮與擔當。如《撕碎訴狀的人》“望一眼祖輩留下廢墟的土房/小車上坐著搖旗吶喊的開發商/回頭看一眼陰森森的樓群/撕碎訴狀扔進渾濁的護城河”。這首詩,寫出當今社會一個真實現狀,也顯出無法挽留祖輩遺產的無奈傷感。還有《農貿市場》中的“店鋪”“菜販”“肉攤”“水果”等都滲透著人文關懷與批判精神,沉淀著底層族群的苦難和歡樂,折射著追求真善美,摒棄假丑惡的執著信念和高尚情懷。
文品即是人品,現實生活中的王萬里是一個普通企業的董事長,他積極參與社會生活,與各方面的朋友保持著坦誠與真摯。離開原工作單位鄂爾多斯市煤炭局已10年了,離開內蒙古伊泰集團已20年了,但他和原來的同事、部下始終保持著密切的友好往來,他低調勤勉的人品與豁達大度虛懷若谷的胸懷深深印在人們的心中,備受尊重。他創辦的萬興隆大酒店凡是鄂爾多斯文朋詩友的客人都免費入住,鄂爾多斯作協文聯的活動,皆免費提供場所,免費提供一切服務。他的酒店,可以說是 一個文學沙龍的聚集地。不僅如此,他還資助有困難的員工,過去的下屬和社會朋友。高尚的人格決定了他詩歌的品質。這是王萬里詩歌感動人鼓舞人最基本的源泉。
總之,王萬里詩歌從濃濃的深情中透出堅韌的力量。他曾在本書的后記中說:“從過往的生活中提煉出飽含深情的思想,用詩歌表達我最真實的靈魂之聲”。這就是王萬里:西部的,超越西部;時代的。超越時代。
傷痛的心緒
五月的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小城,時常,沙塵在飛行。這樣的天氣,令人的心情很是壓抑,幸虧陽臺上的令箭荷花在人不留神時,花蕾沖破包裹的葉膜,悄然綻放枝頭,壓抑的心緒,才漸漸像火紅的花一樣,明媚、亮麗起來。望著嬌艷,嫵媚的花,我是多么的驚喜。那一朵的火紅的花,把令箭打扮得像含羞的少女。我的毛孔,浸潤在令箭荷花的幽幽清香里。但僅僅三天的花期,令箭荷花就謝了。我心里的那種疼痛,就像讀劉志成先生的《待葬的姑娘》時,勾起了靈魂深處的戰栗一樣。
《待葬的姑娘》,那是我從不輕易揭開心靈的血痂呀——那是一位年紀僅有21歲“待葬”女孩凄慘的遭遇,憂傷而悲愴:九月的北方,風透著徹骨的寒意,在那廢棄、隨時有倒塌的土窯洞,拴著一個癱瘓、聾啞的奄奄一息的病危少女。她是因家急需錢,被親人賣給十六年前就死去的一個男人“彌婚”的。“在陜北,12歲以上的男性死了,就要埋入祖墳。倘是光棍,親屬會買來未出嫁女子的尸骨,一同安葬。”在她殘存的日子里。孤零零的,只有老鼠為伴、蒼蠅為伍。這是陜北陋俗的寫照之一。上帝就是這樣不公平。可青春只有一次呀!本應該像石榴花一樣,沐浴陽光,雨露滋養。擁有亮麗的青春,美好生活。可她連豬狗不如。那好歹也是條生命啊!我的心在顫栗。正如梅蘭芳所唱:女人花,搖曳在紅塵中,女人花,隨風輕輕擺動。女人如花,未等芬芳,竟然凋零。
我想起了鄂爾多斯市電視臺文友李軍在博客里貼的描寫自己閱讀劉志成文字的一段評語:
《待葬的姑娘》是一種成熟的文字,它冷峻、孤獨,有些離窮索居。我承認,我理想中的文本、文字就應該是這樣子,在這樣的夜晚讀到它,我漸漸地驚栗和慌恐起來。它讓我對自己二十多年的閱讀經歷感到虛無、空虛。甚至缺失意義。我能感覺到的是《待葬的姑娘》這樣的文字叫我頭一回認真地感知和品味語言究竟是具有怎樣的一種屬性。這樣一種文字,它不是為了取悅內容而進行不厭其煩的堆砌,迷失在精心或讀漫不經心的文字堡壘里最終不知所云,而這卻在盡可能的限度之內,充分發揮文字語言作為表述工具的功能。它讓我長期以來對文字形成的敬畏和遲疑心理得到了多半的化解。這樣一種只為如何更好地表述思想而存在的文字,這樣的表述,無疑才能真正直抵文字的本質。讀《待葬的姑娘》,我真的很汗顏從前輕薄文字和對閱讀的漫不經心,以及對文字語言的漠視。也許,《待葬的姑娘》已成為我閱讀體驗和擺弄文字時心理狀態撥亂反正的一個明確拐點。我相信,自己經過思維洗禮的文字會重獲自由,鮮光亮麗,重放異彩。
志成的作品素材來源真實的現實生活。那個待葬的姑娘的確有其人。志成淋漓盡致將苦難的意識推向了極致。這與他自身生存的環境有關。出生在八十里明沙,四十條光棍的封閉、落后、窮苦、荒涼陜北神木的溝岔村。兩岸黃沙漫漫,中間一條小河沖擊沙后,留下干河灘成了種植莊稼的良田。遇天旱,水澇,莊稼顆粒無收。他家坐落西岸的黃沙帶上。家境的貧窮是難以用語言表述的,連條新被子都縫不起。他結婚時,還是岳母為他縫了一條。1995年冬天,妻子嫁給他時,對他的家境一無所知,覺得只要愛他和他的文字就夠了。可是生活,需要鹽、油、醬、醋。妻子一月二百塊錢,難以維持兩人的生活。學校每人伙食一百二呢。連肚皮都填不飽。每天妻子餓得頭昏眼花,可還得撐著虛弱的身體給學生上課。那份貧困留給我們刻骨的辛酸、苦難、蒼涼。
志成的《待葬的姑娘》讓我們真實地看到荒涼、貧窮、落后的陜北黃土地上流的“膿和血”。志成說:從此岸到彼岸,從來外界因素不是因素,心才是因素;路好不好走不是關鍵,心才是關鍵……志成是用心寫作的,他的文字是用心血涂抹而成。在他的文章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寫:⑴當姑母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時,我的心就緊縮得發疼。⑵聽著姑母發狠的聲音,我的心在發冷我幾乎要窒息了,心好似千斤重石壓著。⑶脆弱的女孩是否能挺過即將到來的冬天?我內心擎起的疼痛是否能堅持到明春花開?⑷這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最慘痛的一幕。從此以后,我的心常常如鞭抽過似的疼痛不已。從這些心理描寫我們不難看出志成把自己內心的疼痛升華到人類疼痛的高度。也有人說:痛苦是生命高貴的體現。藝術的圣殿是由痛苦砌成。志成的《待葬的姑娘》應該是一個人性的沉重和傷痛的話題。讀著血淚淋淋的文字,又將我的思緒拉向去年回陜北老家,和姑姑閑聊起閨女和兒媳婦的不同。姑姑說:“女兒出嫁如潑出的水,死了埋不在身邊。兒媳婦自家人,死后能埋在一起。”這句話像狂草,在我心中狂長。我感覺我的鮮血在飛揚。如同那滴血的令箭荷花。重男輕女,現在還根深蒂固在陜北親人的骨髓里啊!痛,在我心中愈來愈深……
是的,讀志成的《待葬的姑娘》,令我像是行走在沙漠多日沒飲水,忽然發現前面有一片梅林似的,激活了一個對生活的瑣碎失去文字感覺的女子死寂、干枯的心湖!
——選自西部散文學會微信公眾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