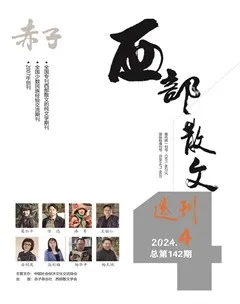我不是一個好女兒(外一篇)
華霖

自從讀了賈平凹的散文《我不是個好兒子》后,我深感自己也不是個好女兒。
母親幼年喪父,在很小的時候就嫁給了父親。父親弟弟妹妹多,家境貧寒,爺爺是國民黨軍官,在抗日戰爭中,子彈穿腿而過,導致殘疾,奶奶一個弱女子撫養眾多兒女,也著實吃力,父親與母親便要分擔撫養弟弟妹妹的責任。文化革命時爺爺挨批斗,妻兒更是要跟著受罪,母親遭受的各種苦難及辛酸是我們無法體會的。
母親如文中的賈母一樣本分老實,勤勞善良,熱情好客。閑時來我們家玩兒的鄰居不少。
記憶中,母親總愛向人訴說她的各種委屈,情到深處,淚眼婆娑。聽者有的搖頭嘆息;有的開導;也有的跟著落淚。母親每次傾訴完畢,擦干眼淚,莞爾一笑,繼續干活。我當時年幼,不諳世事,總覺母親怎么那么善變呢?但我不曾體會她的艱辛,有時甚至覺得她太煩。因為母親總在我淘氣偷懶時,拿起棍子或竹條抽我,無疑,當時我是不喜歡這樣的母親的。
后來,我漸漸長大,似乎懂得了母親的艱辛,便不再那么淘氣,認真做事認真讀書。再后來,我也為人妻為人母,先生常年不在身邊,女兒體弱多病,此刻,才是實實在在體會到了母親的艱辛。但我還是不那么理解母親的,當她再次逢人訴說她的各種心酸時,我便要她少說,甚至不說,畢竟這樣如祥林嫂似的訴說,是不討人歡喜的。
年老后的母親果然是很聽我的話,不再逢人就訴說她的委屈。她很少串門,而長大后的我們個個忙碌,很少陪伴她, 她便經常獨自一人在家。就算幾個婦人來與她道家長里短,她也只是微笑著不言語。她把自己所遭受的各種苦難,就此藏在心底,只字不提。
不久,母親生了大病——頭痛、臉與足發腫、渾身顫抖,講不出話。當地醫生不愿接診,并給母親“宣判了死刑”。父親把母親送到了縣城最好的醫院,進了急診室,總算搶救過來。并住院全面檢查,結果出來,謝天謝地,各個部位均無大礙,一家人總算松了一口氣。
母親生病期間,我因離家遠,加之拖兒帶女,要養家糊口,不曾回去照顧她,只是寄了些錢回去。父親總在親戚朋友面前夸我好,其實我知道,我就如《我不是一個好兒子》的作者賈平凹所說,寄錢只是減輕我心靈的負罪感,我離好女兒實在相差甚遠。
母親住院治療后,癥狀減輕。可一出院,病情又會發作。父親說要把母親送到省城的大醫院。后來,我把母親接到惠州,當然,父親是必須同行的,否則,我們一個個都奔于生計,誰來照顧母親呢?
那天,父親怕我沒錢,把他所有的積蓄都給了我,要我帶母親去醫院。
我帶著母親,來到了惠州第一人民醫院心腦血管科。醫生很細心地看了母親從縣醫院帶來的病歷及各種體檢結果,又耐心地聽母親訴說著身體上的各種不適。我原以為又得住院,不曾想,醫生聽母親訴說完后,輕輕地拍了拍母親的肩膀,嘴角上揚,親切地說:“阿姨,您沒事的,我開點藥給您,您按時吃藥,早起多運動就會好起來的”。我喜出望外,又松了一口氣。
我拿了藥,帶著母親回了家。把母親看醫生的過程告訴了父親,并叮囑父親多帶母親出去走一走,又叮囑母親按時服藥,便繼續投入工作中。
很快,一段時間過去了,母親的病果然大有改善。我想:這醫生簡直就是華佗轉世啊!母親的疑難雜癥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他治好了。我連忙買了茶葉去感謝醫生,并詢問母親到底是什么病。醫生給我看了診斷書及藥物說明書,該藥是治療神經官能,抑郁癥,神經衰弱,更年期抑郁……啊!我的母親,患的居然是精神類疾病。我們作為兒女的卻是不曾察覺,又怎么能稱得上一個好女兒呢?
是的,母親年幼喪父,外婆無力獨自撫養一群孩子,只能讓母親早嫁。一個女孩兒在失去父親的同時,還要離開親人到一個陌生環境生活,真不知母親當時是如何克服內心的恐懼及悲傷的。早嫁給父親也遭受了各種磨難,最初還夭折了兩個孩子。生產我時,也是經歷了九死一生。據說生產我時,母親大出血,因為當時狂風大作,下著瓢潑大雨,加之當時交通不便,不能前往醫院。母親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生下我時,已是奄奄一息。可苦難還沒結束,因我是早產兒,自小體弱多病,常常把父親的血汗錢送給了醫院。母親是如何地把我拉扯大,個中的辛酸,簡直無法想象。
母親遭受的各種磨難,真是說不完道不盡。她需要有個傾聽者,可作為女兒的我,不但沒有用心傾聽,加以開導,卻還限制她向他人訴說,這樣母親又怎么能不生病呢?所幸遇到了好醫生,使母親的病好了起來,否則,我這個做女兒的又該如何面對母親呢?
父親的肩膀
我與父親已多年不相見,不知他那瘦小的肩膀是否還是那么堅硬?
這次母親身體抱恙,我決定讓她來我處養病,當然,父親是一定要陪同的。
那天凌晨五點,我便起床開車前往火車站等二老。初春的凌晨仍有些寒意,我雖穿得多,但仍忍不住打寒顫。
六點鐘,天還未亮,隨著“嗚——”的汽笛聲,載著多年未見的雙親的火車到站。
許久,在晨霧中,三個模糊而熟悉的身影映入眼簾,妹妹挽著病懨懨的母親在前,身形瘦小的父親肩上扛著一個巨大的箱子,緊隨在妹妹與母親的身后,手里還拎著一個小箱子,顯得有些吃力。
我三步并作兩步,趕上前去,要父親把肩上的箱子放下,與我一起抬著走。父親連連搖頭,表示不肯。我只好接過他手中的小箱子,走在前面帶他們上車。
來到車前,我把車尾箱打開,伸手準備幫父親把肩上的大箱子放好,可父親執意不肯讓我幫忙。他還是與當年一樣,什么事都要自己一個人扛著。
我說:“爸,我已不是當年那個小孩了,我能幫您!”“箱子臟,別弄臟了你的手。”父親說著,已將箱子放入車尾箱。
微弱的光線下,父親縱然穿著厚厚的棉衣,看起來卻依然那樣瘦小,我不禁一陣心酸,眼淚便奪眶而出。“爸,那么遠,說好不要帶那么多行李,怎么還是帶了。”我一面嗔怪,一面偷偷抹淚,打開車門請二老上車。
“你不知道,上車前幾天,他就給你到處張羅,一下子給你準備臘肉——你不是最喜歡吃的?一下子又在村里給你挨家挨戶買家雞蛋,這種雞蛋城里可沒有哩!一下子這個特產那個特產,弄個那么一大箱,上車下車都扛著,碰一下都不行……”母親咳嗽著,斷斷續續地說著,我一言不發,只是默默地聽著,眼淚卻再度涌了出來。淚光里,一個熟悉的剪影隱隱走來,那是青年時期的父親。

年輕的父親,肩膀也是那樣瘦弱。可為了一大家子的生活,便是千斤重的擔子也不惜任其壓在那原本難堪負荷的雙肩上。雖然如此,那肩膀卻從未垮過——我的父親,從未退縮。
那時的父親,本應是學校里的驕傲;本應在某所高校深造;本應擁有神采飛揚的年華,卻因國民黨軍官后代的身份,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爺爺在抗日時被鬼子的槍打傷,落下了瘸腿的后遺癥,因著這病根兒,并不能勞作。奶奶一介女子,也實在難以獨自扛起這一大家子的生計。于是,養家糊口的重擔結結實實地壓在了作為家中長子的父親的肩膀上。那樣瘦瘦小小的雙肩,一邊扛起了柴火,一邊扛起了父母的晚年;一邊扛起了鋤頭,一邊扛起了弟弟妹妹的前程。
肉體上的重壓,已令人難以接受。而在文革時,作為國民黨的后代,別人無情的嘲笑,惡意的捉弄,更是父親心中如家常便飯般的苦楚……
可我的父親,他的肩膀雖然瘦小,卻實實在在地堅硬。面對著艱難困苦的境遇,父親并未就此向命運低頭。生活的棘刺里,他依然昂首挺胸,硬是用瘦弱的肩膀為家撐起一片天,再苦,再艱辛,也是那樣扛著……
后來,父親娶了母親,有了我,有了妹妹,弟弟。成了家的他肩上的擔子更重了。為了生活,勞作至深夜是常有的事。可他卻說,為了我們,再重的擔子也能承受。
說起來,這個家最讓他操心的,卻莫過于我了。因為是早產兒,小時候的我總是體弱多病,總把父親好不容易掙來的錢送到了醫院里。稍大了,看著自己不爭氣的身體一次又一次地耗光父親的血汗錢,我總是禁不住地懊惱不已。每當此時,父親仿佛總能看穿我的心思,繼而用那瘦小的肩膀扛起我,帶我去看更高的地方。那一次次扛著我奔向醫院的肩膀,似乎一直倔強地相信著,總有一天,我會飛得很高……
晨寒帶來的寒顫停止了,已至七點鐘的早晨。許是晨光?或是別的什么?在回憶的旅程中暖了我的身軀。
眼淚在曙光帶來的晨風中風干,回憶漸漸淡去,眼前老父親的形象清晰起來。我細細看著,與當年的那個他相比,這個在風吹雨打中老去的身子已是大不如從前了,原本黑而稠密的頭發,如今已斑白稀疏,歲月在他的臉上無情地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皺紋。然而,惟有他那瘦小的肩膀還不肯放下撐起天空的倔強,依舊那么堅固頑強。此刻,朝陽中的他,肩上扛著的是沉甸甸的大箱子,沉甸甸的土特產,如山,如海,幻化成深沉而堅實的父愛。
——選自西部散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