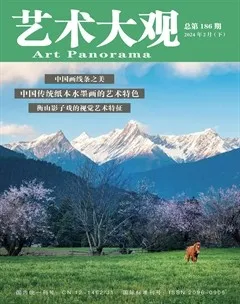20世紀初錄音與現代音樂家演奏實踐的風格比較
趙淑嫻


摘 要:“演奏實踐”這一術語如今越來越受現代學者們的關注,從字面對其進行闡釋,在中國古代文學《宋史·理宗紀》中記載:“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圣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1]這里“實踐”是指實行;履行,用行動使成為事實。那么“演奏實踐”則指演奏家將文本的音樂符號轉化為音樂實體的過程。而在西方《新格羅夫音樂詞典》(1901)中,闡述該詞來自德文“Aufführungspraxis”,而與之相關聯的是“詮釋”一詞,《里曼音樂詞典》(Riemnns Musik-Lexikon)中闡釋“詮釋”一詞源自拉丁語“Interpretazione”,具有解釋之意,是指演出者將樂譜上的音樂呈現出來。
關鍵詞:錄音;演奏實踐;風格比較
中圖分類號:J6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4)06-00-03
如上文所述,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演奏實踐都需要從音樂文本入手進而轉化。而若要追溯音樂樂譜文本則要從古希臘字母符號譜,到中世紀的紐姆譜,再到現代作曲家“精益求精”的樂譜。幾個世紀以來,樂譜的標記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錄音技術的問世,使得演奏實踐研究產生了新的方向。錄音技術一勞永逸地將作品歸于一個確定的音樂形式上。對于演奏者來說,“二次創作”時所呈現的主觀“解釋”原則也受到了一些挑戰。
本文將對20世紀初至今不同演奏家對于同一作品音樂詮釋的不同風格進行探究,進而對20世紀初錄音版本和當下現代音樂錄音版本的差異作淺顯之談。
一、20世紀初的錄音技術發展環境
愛迪生的錫紙留聲機(1877)開啟了聲音復制的時代,為表演實踐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新型資料。在20世紀初的聲學錄音(acoustic recording)技術發展下,錄音室的環境非常簡陋,其與音樂家曾經所熟悉的,寬敞明亮的音樂廳相差甚遠。并且聲學錄音需要藝術家或演奏者在固定的錄音設備前表演,限制了他們的移動和表演的自由度,從而導致演奏者無法完全展現音樂作品的表現力和舞臺魅力。與此同時,由于當時聲學錄音技術限制,聲學錄音無法準確地捕捉音樂的細節和動態范圍,導致錄音總體質量相對較差。這使得當時的音樂錄音師無法客觀地完全還原演奏者及藝術家的音樂表現和真實感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樂的傳達和欣賞效果。在時間方面,由于當時聲學錄音設備使用脆弱的介質,無法實現長時間的連續錄制。錄音需要頻繁更換介質,增加了錄制過程的復雜性和成本,這限制了音樂錄音的持續性和連貫性。以上種種問題都反映了20世紀初聲學錄音技術下客觀存在的限制性,使得聽眾從錄下的聲音中根本無法得知錄音室里音樂作品中的任何聲學特點。因此,在錄音技術還不成熟的20世紀初,大多數音樂家對錄音表現出一定的不適應性。例如,拉赫瑪尼諾夫曾發表過“憎惡麥克風”或者“恐懼紅色信號燈”之類的言論。[2]但于此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初的聲學錄音技術仍然具有歷史意義,為當時的音樂記錄和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并為后來的錄音技術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二、音樂作品介紹
《Scherzo NO.1 in B minor,Op.20》這首作品是肖邦得知華沙爆發反沙俄武裝起義之后而作的,因此在音樂中涌現與迸發了從未有過的震撼人心的悲劇力量。舒曼曾評價此作品:“既然連玩笑都披上了黑紗,那么莊嚴又該穿什么服裝呢?”[3]的確,盡管這是一首諧謔曲,但在整首作品中充斥的是絕望與悲憤。接下來筆者將對利奧波德·戈多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弗拉基米爾·霍洛維茨(Vladimir Horowitz)、郎朗三者的錄音版本進行比較。
三、《Scherzo No.1 in B minor,Op.20》三個錄音版本的分析
三個錄音版本的具體信息見表1所示。
(一)演奏家個性特征
由于個性氣質、生活經驗、社會環境、審美理念等差異,不同的演奏家形成了獨特而賦有個性化的音樂風格。他們的音樂表演通過音樂獨有的形式——音響,展現出獨特的表現力。作為藝術表現的主體,他們對旋律、節奏、速度、和聲等音樂表現要素的處理方式各異。同時,又融入了個人的審美經驗與藝術觀念,從而使其音樂蘊含了更深層的個人意義。本文在分析不同演奏家的錄音時,發現不同演奏家的個性特征對音樂詮釋的風格有著巨大影響。
在錄音技術剛剛興起的時代,大多數的音樂家對錄音抱有“厭煩”情緒。比如,斯特拉文斯基在寫給朋友的信件中,他抱怨錄音過程沒完沒了地重復帶來折磨神經的體驗,而同時代的很多演奏家也深有同感。但對于戈多夫斯基這位追求完美而易于緊張的人來說,即便是在音樂廳演奏,也會有著某種程度的拘束。靦腆和拘謹的性格特征影響了他的演奏效果,同時,在彈奏的力度上他也不會用力過猛,始終保持著一種文雅的風度。
霍洛維茨的音樂演奏極富個人色彩,以至于任何聽過他演奏的人都能輕易地將他的音樂創作與其他演奏家的演奏區分開來。他十分善于使用斷奏,短促而扎實的音樂表現手法,也是霍洛維茨演奏作品時的一大特點。他的琴音靈動剔透,其左手運用了特殊擊鍵方式使其音樂充滿一定沖擊力與獨特性。
中國演奏家郎朗的演奏風格以極具個性化的表現力而被大家熟知,他性格的自信、樂觀、灑脫,導致其音樂風格的豪放張揚,也因此而受到廣大音樂愛好者的喜愛。
(二)版本時長及特點
從宏觀速度布局來看,最引人注目的是戈多夫斯基版本(總用時716”),他的演奏整體偏快,特別是他對于尾聲的處理,聽感上略顯倉促。相對而言,郎朗的演奏(總用時947”)更加具有音樂的方向性。他將情感處理得更加細膩、抒情,并且演奏速度較為緩慢。通過豐富的表情語言和身體動作完美地展現了音樂作為一種可觀賞藝術的視覺盛宴。他的演奏時長較長,作品中呈現出的個性化元素也最為豐富。此外,霍洛維茨(總用時828”)在第一樂段的a部分的演奏用時最多,用時47秒。在這版錄音中,他用了一種反常的慢速來演奏,聽感上極具個人色彩。
(三)演奏手法的對比
本曲的引子部分是兩個完全不協調的和弦,宛如兩個巨大的驚嘆號,為整個曲子創造出了一絲緊張不安的氛圍。戈多夫斯基演奏引子時,較為中規中矩,且有急促與“草率”之意;霍洛維茨演奏引子時,將音樂從強音(ff)過渡到更強的音(sf),力度對比鮮明,使得音響連貫而又緊湊。郎朗演奏的節奏最為自由,兩個和弦的“驚嘆號”變成了一問一答。樂句的銜接間帶有部分的漸慢或突強,同時通過節奏的加緊或收放,增強了音樂的動態性特征。在呈示部,郎朗演奏速度很快,旋律不斷攀升,爆發力極強。戈多夫斯基發展同樣激烈。然而霍洛維茨演奏呈示部時呈現出格外嚴謹的結構模式,引子部分的顆粒性較強,力度對比富有戲劇性。戈多夫斯基和霍洛維茨均強調了左手和弦的進行,并且重音的處理十分精巧。而郎朗自由熱情的演奏風格賦予了這首諧謔曲新的生命。
從74小節開始,整體的音樂變得惶恐不安,戈多夫斯基的演奏貫徹了其一開始的急促風格,好似要將情緒推向最高點。高低聲部、三個八分音符所組成的旋律線形成了一種對峙的效果,而主旋律則隱藏在高音部的最高音中,使其音樂力不斷凝聚上升,后又慢慢回落。而霍洛維茨的演奏并沒有一度地追求音樂的速度,而是在音與音之間設計一些意料之外的休止與停頓。音符的演奏變得靈動純粹,少了些緊湊感,突出左手的重音演奏,與戈多夫斯基的版本形成了鮮明對比。而郎朗則以他華麗的演奏方式和超高技藝,將半踏板以及顫音踏板(Flutter Pedal)靈活地混合應用。
肖邦在展開部旋律的寫作時模仿了對巴赫復音音樂的不同聲部間的模仿,使一個聲部產生了兩種不同的音響。右手高音部看似只有一個聲部,但事實上大指為旋律,小指為伴奏,演奏者必須把音色區分出來,讓右手表現出兩個聲部的效果。[4]這一部分,演奏最為突出的是霍洛維茨,中聲部的持續音自始至終都存在。
尾聲部分的情緒迸發將音樂推向頂峰,不斷出現的fff力度符號將一個個強烈而尖銳的和弦奏響連續重復了九次。在“con brio”的指引下,音樂以活力積極的方式下行,然后以半音階的上行作為終結,宛如狂風一般,以輝煌的姿態結束了整個曲子。然而在本曲最后八小節的六個和弦的演奏,戈多夫斯基彈奏得相當急促,頻繁運用緩急重音的手法,給人們的聽覺帶來了明顯的伸縮變化。相比之下,霍洛維茨和郎朗演繹的音符節奏與時值則比較嚴謹,更偏于標準化。
(四)彈性速度的分析
“彈性速度”(Tempo Rubato),原文的意思為“被奪去的時間”(Stolen Time)。《牛津簡明音樂詞典》解釋為:“一種演奏方面的現象,在一個短時間內不顧及嚴格的拍子,在某個音符或某些音符中奪取的時間在后面給以補償[5]。”根據音樂的進行適當增減速度,從而使得音樂更加自由,具有歌唱性。也就是這種彈性速度,讓演奏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酌情處理樂句之間的緊密聯系。戈多夫斯基的rubato處理在樂句演奏的劃分上,似乎并未按照譜面的演奏標記,將兩個樂句的劃分變為一個長句。在裝飾音部分,似乎更傾向于古典風格的演奏風格。而霍洛斯茨的處理相較于其他兩位較為快速,中聲部的旋律的演奏最為突出,旋律不斷地高揚,直至最高音?G,隨即突然漸慢。裝飾音的處理的延遲演奏,突出了情感的表達。而郎朗總體偏于抒情緩慢,有一種漸入云層之感,與前段的搖籃曲形成呼應。這一部分裝飾音的彈奏,郎朗處理得較為自由,出現了一些左右手的錯置對位。
不同作曲家對于rubato的處理有所不同,慢—漸快—推向高點,使音響效果富有張力。而有些演奏家“傾囊訴說”,緩緩道來。由此說明,音樂是感性的產物,每個人有自己的認知處理方式。
(五)音色處理的分析
由于戈多夫斯基版本錄音為20世紀初,當時錄音技術不夠成熟,同時錄音師要求演奏家需要極度克制音響的強弱對比,從而導致戈多夫斯基錄音版本的音色層次感和強弱對比不夠鮮明。而在霍洛維茨和郎朗的錄音中,對比明顯,高音音色較為清脆,而低音音色則更為厚實和深沉。在三位演奏家的表演中,霍洛維茨在音色的特殊處理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處理最弱音時,他甚至能使其弱到你幾乎無法聽清,但又在微弱中顯現出來。這需要出色的鍵盤控制力。可以說在音色的控制程度上,霍洛維茨是無人能超越的。
四、結束語
本文通過對肖邦《Scherzo No.1 in B minor,Op.20》作品不同錄音版本的聆聽,分析從20世紀初至今,三位具有跨時代代表性意義作曲家的音樂詮釋,進而對20世紀初錄音版本和當下音樂錄音版本的差異作淺顯之談。在戈多夫斯基的錄音中能夠聽見較多的匆忙的短音符和過多點綴的節奏,從而在聽覺感知上總會產生一些認為演奏處理缺乏控制的“錯覺”。而這些在其后霍洛維茨和郎朗的版本中都得到了明顯的克制。在旋律方面,如裝飾音的彈奏,會以輕巧快速的方式彈奏。而當代的演奏家則更加偏向于彈性速度的演繹。楊健老師總結20世紀初的音樂時說:“在20世紀初,那些被稱為緩急重音或不均衡的節奏等傳統演奏,似乎更像是一種古老的敘述方式,當代的聽眾習慣漸漸無法十分清楚地解讀其中的表現含義。”[6]對于20世紀初錄音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當代演奏風格中的精確性、規范性傾向特征進行反思,從而也為未來的演奏實踐領域產生了全新的視野。
參考文獻:
[1]劉緒義.周敦頤的為官之道[J].刊授黨校,2016(04):66.
[2]楊健.錄音技術對20世紀西方音樂表演風格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10(04):48-54.
[3]李琦.“披著黑紗的玩笑”——肖邦《b小調諧謔曲》Op.20研究[J].音樂時空,2016(07):63-64.
[4]謝承峯.漫游黑白鍵:西方鋼琴作品解析與詮釋[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8.
[5]謝承峯.論彈性速度的廣義概念與應用[J].藝術評論,2015(08):94-96.
[6]楊健.20世紀西方器樂演奏風格的結構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基于計算機可視化音響參數分析的研究結果概述[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08(03):1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