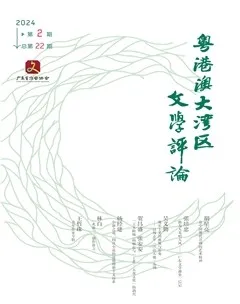抒情性敘事的探索及文學(xué)遠(yuǎn)景
陳銀清 陳培浩
摘要:青年作家王哲珠的小說作品多與潮汕鄉(xiāng)土關(guān)聯(lián),也有對城市的呈現(xiàn),體現(xiàn)了濃厚的鄉(xiāng)愁與對熱烈的新鄉(xiāng)土生活的展望。她的小說多采用抒情化的語言,形成一種詩化的敘事風(fēng)格。王哲珠以女性特有的細(xì)膩將小說寫得波瀾婉轉(zhuǎn),飽含深情地述說時代與人、鄉(xiāng)村與城市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表現(xiàn)了人在時代變遷中的變化,別具獨特的審美意味。王哲珠的寫作,自覺地賡續(xù)和轉(zhuǎn)化中國文學(xué)的抒情傳統(tǒng),其詩性敘事頗具特色。然而,有效的抒情化敘事不是敘事的懸置,而是情動對敘事的激活;抒情化敘事也需要與更寬廣的文學(xué)觀相連接,與敘事性與虛構(gòu)性相統(tǒng)一,以打開更廣闊的文學(xué)遠(yuǎn)景。這構(gòu)成了當(dāng)代小說待解的難題。
關(guān)鍵詞:詩性敘事;抒情傳統(tǒng);敘事性;虛構(gòu)性;王哲珠
潮汕作家王哲珠的又一部長篇小說《玉色》,于2023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是作者繼《老寨》《長河》《琉璃夏》《塵埃閃爍》《我的月亮》《姐姐的流年》之后的又一部長篇小說。作為“80后”青年作家,王哲珠雖不如雙雪濤、蔡東、王威廉、陳崇正、鄭小驢、孫頻等人受關(guān)注,但憑著勤奮和高產(chǎn),王哲珠也收獲了不少文學(xué)成果和榮譽。新近更是憑長篇小說《姐姐的流年》獲得第十一屆廣東省魯迅文學(xué)藝術(shù)獎。值得追問的是,寫作已有十多年,王哲珠的創(chuàng)作顯示了怎樣的階段性和內(nèi)在衍變?濃烈的抒情語言是王哲珠小說的重要特征,抒情性成了王哲珠小說的語言氣質(zhì)與風(fēng)格類型。但小說的抒情性如何獲得更高的文學(xué)遠(yuǎn)景?如何與敘事性、虛構(gòu)性相統(tǒng)一,這同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本文嘗試通過王哲珠的小說對此有所回答。
一、王哲珠小說創(chuàng)作嬗變
王哲珠的寫作是從書寫鄉(xiāng)土起步的。鄉(xiāng)村是王哲珠最熟悉和依戀的地方,也是她持久回眸的對象。在鄉(xiāng)村觀察鄉(xiāng)土,于城市回望鄉(xiāng)村,斯土斯民成為王哲珠寫作的重要題材。但王哲珠小說也不局限于鄉(xiāng)土題材,也有多樣的題材和多變的風(fēng)格,曾引起社會和文學(xué)評論界的廣泛關(guān)注。
王哲珠的創(chuàng)作初期,鄉(xiāng)土題材占據(jù)了較大的比重。此間,不但有出版于2013年的長篇小說《老寨》和出版于2015年的長篇小說《長河》,還有很多中短篇小說面世。這個時期的王哲珠,縈繞于懷的是中國農(nóng)村為何逐漸失去新鮮血液,日漸衰微與空蕩,那原本附著于鄉(xiāng)村的生活方式、樸實無華的價值觀、專屬于鄉(xiāng)村的味道都隨時代的變化而漸漸消弭。鄉(xiāng)村對于王哲珠來說,是小時候的家園,是純真無邪的地方,是充滿著童趣與故事的地方。在鄉(xiāng)村所積累起來的童年經(jīng)驗,影響了王哲珠對生活的感知方式、情感態(tài)度、想象能力、審美傾向與藝術(shù)追求。但時代的高速發(fā)展,漸漸將鄉(xiāng)村拋在現(xiàn)代生活的外面,鄉(xiāng)土樸素可親的面目也逐漸模糊了。于是,王哲珠想用飽滿的細(xì)節(jié)再現(xiàn)一個寨子變遷中的點滴,以敘事復(fù)活鄉(xiāng)土曾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人倫關(guān)系,這便有了《老寨》。《老寨》以豐富的細(xì)節(jié)展現(xiàn)過去鄉(xiāng)村生活的緩慢與柔美,以溫暖細(xì)膩的筆觸思考老寨的歷史與未來,寄托著對傳統(tǒng)鄉(xiāng)村的凋零和沒落的無限追憶與感傷。王哲珠創(chuàng)作的多部(篇)鄉(xiāng)土題材小說,并非一成不變地描寫鄉(xiāng)村的凋零,也有別樣的呈現(xiàn),如長篇小說《長河》。《長河》通過馮家?guī)状说纳睿瑫鴮懥私鹣c金溪河的命運,展現(xiàn)了人心在膨脹的欲望中的背叛與堅守。王哲珠感慨于:鄉(xiāng)村想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卻被時代越甩越遠(yuǎn),直到失去它原有的生命力。與《老寨》不同,《長河》有鄉(xiāng)村子民面對時代變遷的迷茫與掙扎,也有嘗試跟上時代步伐的努力,體現(xiàn)了更強的主體性自覺。
王哲珠創(chuàng)作的第二階段大約是在2016年至2019年。隨著閱歷的增加和視野的打開,王哲珠的小說不再局限于寫鄉(xiāng)村的盛衰興替,而開始有了視角的切換,由此帶來對生命“真實”的不同理解。此間,她更多從城市回眸鄉(xiāng)村,嘗試以豐滿的日常細(xì)節(jié)挖掘生活更深的內(nèi)里,寫出生活的背面,表象世界底下的另一面。此階段代表作有《琉璃夏》《紙上人生》《塵埃閃爍》《琴聲落地》等。《琴聲落地》,描寫了鄉(xiāng)村揚琴手老獨與花旦映嬋在潮劇興盛時期結(jié)下的深厚感情,也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生活觀念如何逐漸滲透并深深影響、改變了農(nóng)村。年輕人不喜歡潮劇,傳統(tǒng)鄉(xiāng)土的文化生活方式已無人呼應(yīng),作者流露出一種懷舊的感傷和憂思。王哲珠意在描寫現(xiàn)代城市文明對鄉(xiāng)土文化的入侵,鄉(xiāng)土文化逐漸失去堅守者,這讓農(nóng)村的現(xiàn)代化進程行進艱難。《紙上人生》思考的則是“真實”與“虛構(gòu)”的關(guān)系,寫的是一個離奇故事,小說中的人物高宇、楊木木、閻讓東,自以為掌握了自己的生活,最后發(fā)現(xiàn)自己被生活掌控,這種“失控”的隱喻,讓小說呈現(xiàn)出思想的厚度與深度。再如《塵埃閃爍》,主角是都市里的邊緣人物,小說寫出了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相互吸引與融合。來自鄉(xiāng)村心靈純凈、珍視生命本真的丁丑原本與女朋友姚婉凈一起擺燒烤攤謀生,但這無法滿足姚婉凈對物質(zhì)享受的追求,最終她追隨有錢人而去。在城里長大的高書意家境優(yōu)越,但她的生活卻很單調(diào)空虛,她被丁丑那豐富的內(nèi)心與純凈的心靈所打動,最終與丁丑走在了一起。這篇小說寫出了兩種錯位人生,鄉(xiāng)村與城市有了交集與融合。這個時期王哲珠對鄉(xiāng)土的描寫更加扎實與厚重,有了更多層次。
王哲珠第三階段的創(chuàng)作有了更大的推進,也更加注重對人物的刻畫與表現(xiàn)。2020年至2023年的三年間,她發(fā)表了《我的月亮》《姐姐的流年》《玉色》等多部小說。與之前不同的是,此時期王哲珠筆下人物更加立體,有對人性更深入的探討,敘述形式也更加豐富多樣。如《我的月亮》,小說展現(xiàn)了生與死的糾纏,愛與人性的交匯。得了絕癥的青年女歌手高靈音面對命運的戲弄意圖自殺了結(jié),但老天讓她遇見了富二代肖一滿,他阻止了高靈音的自殺。高靈音之后去了山村小學(xué)教孩子們唱歌,獲得了一種心靈的圓滿。又如《姐姐的流年》對“姐姐”的多視角描寫,讓“姐姐”的形象更加飽滿。小說六個章節(jié)書寫?yīng)毩⒌墓适拢圆煌囊暯敲鑼憽敖憬恪保€以諸如劇本體、日記體來結(jié)構(gòu)全篇,且形式與內(nèi)容形成內(nèi)在的嵌合和呼應(yīng)。“姐姐”也隨著不同的視角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象側(cè)面,展示出“姐姐”的成長軌跡,以及多側(cè)面的、多層次的形象。
最新長篇小說《玉色》則以鄉(xiāng)村振興為主題,這是王哲珠以更加建設(shè)性的方式回望鄉(xiāng)村。但她的書寫比之以往有諸多不同。《玉色》中延續(xù)了《老寨》《長河》的鄉(xiāng)土抒情敘事,但在精氣神上與《老寨》《長河》不同,書寫的是充滿希望與奔頭的鄉(xiāng)村,是追求文化高度的鄉(xiāng)村,是不甘于落寞的鄉(xiāng)村。小說主要寫: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以夏文達、歐陽立與林墨白等人為代表的喬陽人不懈努力,讓喬陽成為全國重要的翡翠聚集地之一。小說既寫村干部的精神成長與思想的進步,也寫喬陽人創(chuàng)業(yè)過程中的矛盾沖突和團結(jié)協(xié)作。圍繞玉石交易和人性糾纏展開了頗具可讀性的新時代鄉(xiāng)建敘事。玉在中國的文化中,不僅意味著財富,也代表著美德。《玉色》在鄉(xiāng)建敘事的背后,也內(nèi)蘊了以“玉”為核心的德性呼吁。小說在語言上更加的克制與隱忍,也間以魔幻的元素,如“粉翠精靈”,以一種魔幻式的表達豐富了喬陽村的翡翠文化。這是王哲珠在長篇小說的又一次發(fā)力,也是她對鄉(xiāng)土題材的再次呈現(xiàn),但無論在寫作手法、敘事技巧,還是抒情方式上,《玉色》都體現(xiàn)了一種新的氣質(zhì)。王哲珠正是在對生活的不倦挖掘與對日常細(xì)節(jié)的細(xì)膩展示中,呈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和時代新的詮釋。
二、抒情化敘事:以情感為中心
抒情與敘事是中國文學(xué)的兩大傳統(tǒng)。但就如陳世驤所說:“中國文學(xué)的傳統(tǒng)一言以蔽之,是一個抒情的傳統(tǒng)。”1“抒情精神在中國傳統(tǒng)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正如史詩和戲劇興致之于西方。”2那么,作為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小說的抒情與敘事該如何結(jié)合?然而,這里的抒情不局限于作為表達方式的抒情,更是指一種精神與韻味。王哲珠曾多次提到自己喜歡《紅樓夢》,并在創(chuàng)作中受其影響。《紅樓夢》是中國現(xiàn)代抒情小說的鼻祖,也是中國抒情傳統(tǒng)的集大成者。受古典文學(xué)的教育與熏陶,王哲珠小說中有豐厚的感傷氣質(zhì)與濃郁的抒情性。王哲珠對第三人稱內(nèi)聚焦限制敘事頗有心得,能精微捕捉主人公意識流動;又以很強的語言駕馭能力,使意識流敘事呈現(xiàn)出抒情化格調(diào)。謝有順曾說:“抒情傳統(tǒng)不僅是一種文學(xué)實踐,也是一種生命實踐。抒情傳統(tǒng)中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不把抒情、情感視為小道或僅僅局限于文本,而是表現(xiàn)為對一種生命意識、生活態(tài)度、情感結(jié)構(gòu)的體認(rèn)。”3王哲珠的小說也體現(xiàn)了這樣的追求,其第一部長篇《老寨》,在開篇就奠定了一種抒情基調(diào):
作為一個寨子,我的年歲不算大,但我老了。我這樣說時,心平氣和,無悲無喜。我很清楚,如今不比從前,人世間的一切都鼓了說不清道不明的風(fēng),嘩嘩啦啦地飄。風(fēng)呼呼呼地喊,快,快,快。人世間的腳步便啪啪啪地快了,往前趕,雖然不清楚那么快做什么,也不清楚這聲音從何而來。4
《老寨》的語言很有黏性與表現(xiàn)力。讀小說開篇的這段文字,我們感覺語言被拉長。重復(fù)的字詞、深情的語調(diào)讓語言節(jié)奏舒緩悠揚,又不乏靈動的變調(diào),如從二字的“嘩嘩”“啦啦”到三字的“呼呼呼”“快,快,快”“啪啪啪”的轉(zhuǎn)換。這里將老寨擬人化,以老寨為第一人稱,以老寨之“眼”觀乎世情,既蘊含對鄉(xiāng)村的充沛情感,又帶點傷感的氣息。小說開篇的這種抒情性寫法,并不合于一般的小說寫法,那它沒有小說敘事性嗎?又不是的。小說接著便進入人的故事。《老寨》全篇分為三個部分,圍繞著鄉(xiāng)村的典型事件——喪事與喜事展開敘述,最后以“心事”來深入老寨的血肉記憶與滄桑歲月。《老寨》擅于抒情化敘述及在敘述中抒情,在敘事與抒情中呈現(xiàn)鄉(xiāng)村的精神內(nèi)核。如第一部分《喪事》中,進城務(wù)工的樹春因工傷亡,而樹春妻子此后卻背叛樹春,最后又感到愧疚。這一部分描寫的多是鄉(xiāng)村生活的瑣細(xì)點滴,描寫鄉(xiāng)村人物如樹春、秋柳、喜月、阿爸之間的關(guān)系纏繞,少有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設(shè)置,也沒有驚心動魄的高潮與矛盾。小說用抒情的語言,濃墨重彩地書寫人物內(nèi)心的情感波瀾。如樹春因工受傷卻得不到說法的無奈:
“所有的聲音,都落進樹春的那些黏稠的靜里了。以后的歲月中,樹春要不就在這團黏稠的靜里沉默,要不就全身烘出一團火氣,炙烤那團黏稠的靜,烤得噼噼啪啪地響,那層靜便一片一片地掉落,甚至飛濺,濺到身邊某一雙眼里,或某一張臉上,周圍那雙眼或那張臉就疼痛起來。” 1
樹春因工受傷,卻得不到老板相應(yīng)的賠償,將老板告上法庭也無濟于事。樹春陷入求告無門的痛苦中。這一段以第三人稱內(nèi)聚焦限制敘事的方式,呈現(xiàn)了樹春受傷后身體的疼痛與精神的困苦。人物描寫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部分,這里,王哲珠不用曲折的情節(jié)去凸顯人物,而是通過表現(xiàn)人物情感與精神來表現(xiàn)人物。她的小說敘事結(jié)構(gòu)單純,文字直指人的苦難與疼痛。《老寨》的樹春、《長河》的馮家人、《我的月亮》中的高靈音、《姐姐的流年》的姐姐等人物的人生在王哲珠筆下徐徐展開,小說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jié)與嚴(yán)密的故事性,她只是細(xì)致入微地觀察、平靜如水地敘述。王哲珠小說的抒情性,即體現(xiàn)為將人物情感作為小說的內(nèi)核。抒情的文字之下,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是層層深入的人物情感。人物情感成為了敘事的中心。另一方面,盡管情節(jié)并不曲折,但故事也在抒情性的語言中得到鋪呈和展開。因此,這并非一種靜態(tài)的抒情,而是一種抒情化的敘事。
又如王哲珠的另一部長篇小說《長河》里的抒情語言:
馮流夏在河邊遇到葉子,準(zhǔn)確地說,應(yīng)當(dāng)是先遇到葉子的歌聲。當(dāng)時,馮流夏坐在河邊,手里扭著細(xì)長的草莖,他聽到歌聲,煙一樣,渺渺而來,又極脆亮,像魚翻起的水花聲,因隔得遠(yuǎn),聲弱了,但仍感覺得到丁當(dāng)?shù)馁|(zhì)感。2
這里對人物的感覺有多層的表現(xiàn):馮流夏聽到葉子的歌聲,而葉子的“歌聲”又如“煙一樣”,又如“魚翻起的水花聲”,聲弱后又有“丁當(dāng)質(zhì)感”。小說由單純的葉子的歌聲,串聯(lián)起“煙”“水花”“丁當(dāng)”幾種事物,讓一個事物的聲音聯(lián)系起多種聲象,語言曼妙而生動。同時,人物自身的情思與心緒,也由語言的組合匯聚成一種抒情的氛圍與情調(diào)。這樣具有抒情意味與情調(diào)的語言,讓我們不由想起廢名、沈從文與汪曾祺等小說家的抒情化敘事。廢名將自然美景和田園趣味引入小說,他寫小說不重講故事而重創(chuàng)造意境,并在此過程中寫出對人生的理解;沈從文擅長在小說中鋪展湘西邊地的風(fēng)土人情,創(chuàng)造氛圍與意境在沈從文是與小說情節(jié)同樣重要的事;汪曾祺常將風(fēng)俗描寫作為人物的背景與敘事契機,借以呈現(xiàn)人性之美。不難發(fā)現(xiàn),王哲珠受到現(xiàn)代文學(xué)抒情化敘事的影響甚深。她眷戀和書寫故鄉(xiāng)的風(fēng)景與人物,人物的行為在不同氛圍的籠罩下不斷發(fā)展,心理思緒也因之不斷起伏變化。在小說中,作為作者的王哲珠也是潛在的抒情主體,其情思投射在小說人物的言行上,現(xiàn)實認(rèn)知和省思遐想蘊于其中。
不能說王哲珠在抒情化敘事的方向上超越了前人。事實上,超越可能不是用來描述文學(xué)代際賡續(xù)的有效概念。對于科技而言,一代之興必是上一代之廢;但對藝術(shù)而言,承續(xù)不是在上一代的路上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而是獨辟蹊徑和別開新境。幾千年過去,《詩經(jīng)》和荷馬史詩依然是吸引后人的中外經(jīng)典。這樣說,不是說王哲珠已經(jīng)可以和前面那些抒情小說家相提并論,而是說作為后輩小說家她同樣擁有吸納前人又另辟蹊徑的可能。抒情化敘事,不重故事、淡化情節(jié)、深挖內(nèi)心、重視氛圍和意境的營造,這些都是共性。然則,什么決定了抒情化敘事的藝術(shù)高下?情感的獨特性、技巧的創(chuàng)造性以及藝術(shù)上擊中人心的效果,都是考量的要素。抒情化小說,歸根到底必須有情。不僅是人物有情,更是寫作者有情。寫作者有情,其筆下人物才可能有情。文學(xué)的有情不是一般地指有感情、有良知,而是指其內(nèi)心被某種情思所纏繞,甚至有所郁結(jié),不吐不快。文學(xué)的有情也不僅是作者情感的宣泄,它必須是一種更豐富、更微妙、更高級,包含著更高價值內(nèi)涵的情感。文學(xué)的有情,是指某種情思穿透了寫作者的心靈結(jié)構(gòu),使其悸動,不可抑止;隨后又把這種心靈波瀾藝術(shù)化,投射到人物和敘事中去。所以,抒情化敘事的真正核心是情動,而不是敘事的缺位或隱匿。敘事隱匿并不會自動帶來情感的凸顯;沒有情動而強行抒情,同樣無法讓人感動,反而容易令人反感。不管具體的展開方式如何,王哲珠的抒情化敘事,絕大部分把握住了由情動而生發(fā)敘事這一核心。
三、抒情化敘事與文學(xué)語言的更高追求
必須說,王哲珠的抒情性小說語言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王哲珠的小說語言清麗婉轉(zhuǎn),具有輕音樂般的和緩柔美,筆觸細(xì)膩,情境沖淡平和,作者也力圖將文學(xué)之美和哲理之思有所融合。如她在《塵埃閃爍》與《琴聲落地》中的描寫:
這兩個多鐘頭里,周雪雅把城市一層一層掀起來,讓姚婉凈細(xì)細(xì)看,她一層一層,一個角落一個角落地抖摟開,經(jīng)經(jīng)脈脈理給姚婉凈聽。真正的城市其實是看不到摸不著的,你得融進去,整個化進它獨有的生活和方式、觀念和意識。1
掂起琴竹,老獨整個人變了,蛻皮般褪去層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琴架前的他成了月下的煙,邈遠(yuǎn)、神秘,目光蒸騰,表情游離。琴竹敲出第一個音,余音裊裊。第二個音響起,曲子就起了,他蒸騰的目光收聚成點,閃爍在曲子深處,渙散的表情一掃而光,面皮浮起光彩,隨曲子起落而明暗。2
以上兩個文段,情與景交融互滲,運用具有靈動性的詞語,如用“掀”“抖摟”“蒸騰”“游離”等詞語自然地鋪展敘述。無論是對鄉(xiāng)村還是城市的描寫,王哲珠常常挖掘出易被人忽視的情感體驗。《塵埃閃爍》中的姚婉凈向往城市的繁榮,卻不通曉城市的經(jīng)經(jīng)脈脈。王哲珠于此處道出了城市的復(fù)雜及其生存方式,具有哲理性;《琴聲落地》則寫出了主人公老獨只有面對著揚琴時,生命才煥發(fā)出了光亮。王哲珠用“月下的煙”來形容老獨彈琴時的狀態(tài),營造了一種縹緲神秘的氛圍。同時,也從側(cè)面表達了以生命狀態(tài)呈現(xiàn)的藝術(shù)之美。可見,王哲珠的小說具有語言的美與哲理之思。
但也要看到,這種比較理想的語言狀態(tài),是王哲珠不斷追求和實踐的結(jié)果。王哲珠創(chuàng)作初期的小說,抒情味較濃,在思想性與哲理性上還有發(fā)展空間。但到了后期,她的小說漸漸將抒情性與敘事性、思想性更好地結(jié)合了,如2020年發(fā)表的《姐姐的流年》:
母親說姐姐背著我洗衣時,我偏偏愛撒尿,又偏偏總在冬天。多年以后,我回憶起來,才意識到母親語氣里充滿疼痛,而姐姐總是笑,手指在臉上劃著羞我,我因為害羞,母親說起這些時總想避開。
云淡風(fēng)輕的語言背后,是人生的疼痛與無奈,是生存的艱難與困苦。王哲珠在這里寫出了“姐姐”的形象,同時也寫出了姐姐生活之苦。這里交雜著命運與人性的主題,具有思想性,同時又沒有消磨小說的故事性。從《老寨》到《玉色》,王哲珠擅長以日常的書寫與充盈的細(xì)節(jié),描寫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記錄對時代的感受與思考。她不斷摸索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由此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抒情特色。如今,王哲珠在語言上有了更多的突破,她的最新長篇小說《玉色》就融入了對人物意識流的描寫:
他感受到極端的亮,亮到無法睜開眼睛,但每一寸肌膚都打開了眼睛。他看見了光,光飽滿濃稠到難以承受,灼熱是在靈魂里的,熱到極點,失去了灼熱感。轉(zhuǎn)瞬間,他從極亮跌入極暗,暗像水像空氣,滲進林墨白的身體,他被融化,成為黑暗的一部分,刺骨的冷,不,是冷到感覺不到骨頭,感覺不到自身,只有冷,巨石一樣在壓在身上,壓得人無處可逃。1
這是小說里的人物林墨白見到粉翠精靈時的心理描寫,同時也是一種感覺化的描寫。從光、熱、融化,到冷、刺骨,王哲珠熟稔地運用著感覺化的語言來描寫人物的心理變化。以具有陌生感的語言打破以往司空見慣的日常語言,讓小說具有新的形態(tài),帶給讀者獨特的閱讀體驗。總的來說,王哲珠的小說語言在不斷進步,也在不斷挖掘自身的可能性,其抒情性小說也獲得了文體意義上的合法性。
某種意義上,王哲珠的抒情性小說賡續(xù)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抒情傳統(tǒng)。學(xué)者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中認(rèn)為:“引‘詩騷入小說的藝術(shù)嘗試,不單為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貢獻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抒情小說,而且促成了中國小說敘事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2他將現(xiàn)代抒情小說的出現(xiàn)視為一種小說敘事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我們由此可以找到這條關(guān)于抒情性小說的“史的線索”,即從魯迅《社戲》《故鄉(xiāng)》開始的抒情鄉(xiāng)土小說,到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沈從文的《邊城》《蕭蕭》、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再到汪曾祺的《受戒》、遲子建的多部鄉(xiāng)土抒情小說與魏微的創(chuàng)傷書寫等。蕭紅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重要作家,她的《生死場》《呼蘭河傳》,將對悲涼生命的迷惘與掙扎化作抒情性的文字,訴說孤獨者的生命感受。遲子建以兒童般純凈的赤子之心,以不被世俗侵?jǐn)_的眼光和觀察力,記錄鄉(xiāng)村與城市的生靈日常,文字澄澈而空靈。“70后”作家魏微的《鄉(xiāng)村、窮親戚和愛情》(《花城》2001年第5期),寫的是一個城市女孩與農(nóng)村男人之間的微妙感情,這篇小說同樣不以情節(jié)取勝,而是將感情作為中心,推動敘事的行進,主導(dǎo)了小說的敘事方向。王哲珠小說中充溢的抒情性,讓她的小說產(chǎn)生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她的抒情性小說創(chuàng)作,自覺轉(zhuǎn)化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抒情傳統(tǒng),無疑是當(dāng)代抒情小說的一朵浪花。
事實上,重語言、擅于抒情化敘事,這是大多數(shù)女作家的特點。女作家出色的感受力和細(xì)膩的表達力,往往使她們與抒情傳統(tǒng)締結(jié)了更親密的關(guān)系。但是,抒情化敘事能否、又如何上升為上述那種語言與思想、內(nèi)容與形式化合為一的更高的語言?這是一個待解的問題,又是一個對王哲珠這樣的青年作家尤其重要的問題。抒情化敘事以及抒情傳統(tǒng),常是可以方便地加諸其身上的論述。這種論述固然敞開了作者的某種寫作特質(zhì),卻也擱置了更高的追問:即抒情化敘事內(nèi)在有沒有高下?抒情化敘事如何朝向更高的方向邁進?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語言的寓所中。”1汪曾祺也有一句名言:“寫小說,就是寫語言。”2他們都說明了語言的重要性。表面上看,這是指任何文學(xué)作品都以語言作為載體,文學(xué)效果的達成也有賴于語言的恰當(dāng)運用。深層次看,則是指文學(xué)語言與敘事內(nèi)容以及精神價值之間,不是簡單的杯子與水的關(guān)系。有什么樣的語言,就有什么樣的文學(xué)創(chuàng)造和文學(xué)價值。將語言提升至文學(xué)本體的位置來討論,并非否定其他諸如經(jīng)驗、內(nèi)容、思想等文學(xué)要素的作用,而是說真正好的文學(xué)語言,必然蘊含著內(nèi)容、思想和價值觀等內(nèi)容;而文學(xué)的思想和價值,也必形諸于語言之中。語言的內(nèi)容和形式,都化合為一。所以,抒情化敘事,并非懸置敘事就夠了。既必須以真正的情動使抒情化敘事獲得有效性,又必須置身于更高的語言追求中,使抒情性獲得更大的文學(xué)前景。此外,小說的抒情性還必須處理好與敘事性的共生關(guān)系。詩性或散文化的小說雖以抒情性為主導(dǎo),但并非對敘事因素的全面拒絕和放棄。抒情也需要語言載體、故事模型的依傍。然而這需要作家以高超的功力去調(diào)節(jié)抒情與敘事的矛盾,達到抒情與敘事的平衡。從文體角度來看,小說主要還是一種敘事的藝術(shù)。雖然每個時期抒情性的小說的出現(xiàn),都是一種超越主流敘事范式的努力,但它們往往都處于邊緣的地位。靜態(tài)的抒情過盛,很可能傷害小說的故事性與虛構(gòu)性。導(dǎo)致抒情性的失效。這些,都值得以抒情性為敘事追求的作家注意。
結(jié)語
小說由語言造就,某種意義上,有什么樣的語言就有什么樣的小說。抒情性敘事是中國現(xiàn)代小說中非常重要的一脈,這一脈的小說更強調(diào),“人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存在,而且還是一種心理的存在,一種情感的存在。”3因此,重要的不是故事和敘事,而是通過小說對人的情感內(nèi)在性進行不懈的勘探。王哲珠的寫作有多個面向,但她顯然更擅長抒情性小說,抒情性敘事隨著她的寫作探索、對世界認(rèn)識的深化而發(fā)展和完善。她不斷耕耘,也在不斷收獲。她的語言與思想經(jīng)過時間的錘煉獲得了發(fā)展,她小說中純凈婉轉(zhuǎn)的抒情語言與頗有哲思的詩性敘事,吸納了中國文學(xué)抒情傳統(tǒng)的養(yǎng)分。王哲珠的寫作,關(guān)聯(lián)著抒情性敘事的探索和如何獲得更大文學(xué)遠(yuǎn)景的理論難題,值得持續(xù)關(guān)注和探討。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1 陳世驤:《論中國抒情傳統(tǒng)》,《抒情之現(xiàn)代性——“抒情傳統(tǒng)”論述與中國文學(xué)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版,第26頁。
2 [美]陳世驤著,張暉編:《中國文學(xué)的抒情傳統(tǒng):陳世驤古典文學(xué)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8頁。
3 謝有順:《“70后”寫作與抒情傳統(tǒng)的再造》,《文學(xué)評論》,2013年第5期。
4 王哲珠:《老寨》,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
1 王哲珠:《老寨》,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頁。
2 王哲珠:《長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頁。
1 王哲珠:《塵埃閃爍》,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頁。
2 王哲珠:《琴聲落地》,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頁。
1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49頁。
2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2頁。
1 [德]海德格爾:《關(guān)于人道主義的書信》,見《路標(biāo)》,孫周興譯,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版,第366頁。
2 汪曾祺:《林斤瀾的矮凳橋》,見《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頁。
3 劉再復(fù)、林崗:《傳統(tǒng)與中國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