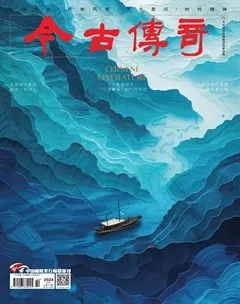永遠有多遠 文學有多遠
早在1997年,美國批評家希利斯·米勒就提出了“文學終結”論,他認為互聯網、新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將使文學失去崇高地位,“文學就要終結了”。時隔二十多年,今天AI寫作所引發的效應,不亞于一次新的“文學終結”危機。當人工智能寫出的文本可以“以假亂真”時,文學創作究竟面臨著怎樣的深刻考驗?
于是有人把文學比成美人,認為“眾芳蕪穢”“美人遲暮”是一種宿命,就像王國維詞中所寫——“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離別或者零落是一種命定的結局。這個比喻多少有些悲哀和無可奈何,但我卻愿意從另一個角度去解讀。文學在表述方式、內容與內在精神的構成方面,更多地呈現出一種生命器質,這種器質主要體現為一種藝術型創造性靈智。它融和充盈完整的生命體驗,展示出一種超越邏輯和知識的靈性。人如何生存是亙古不變的話題,并不隨時代、環境的轉移而消逝。也許文學與生命在本體論上具有一種同構共生性,并關涉生命超越的價值反思。
文學是關乎審美體驗的。而審美體驗中那些豐富、生鮮的思想不能完全在比較、分析、綜合、抽象與概括中得到。文學所衍生的美,絕不會成為任何意義上的現成對象。美并非凝固不變、可觸可感的實體,而只是一種形而上層面上的存在。這種存在是無論如何不會被概念化的,只能在體驗中被揭示出來。在審美的存在空間里,概念化、觀念化只能將我們囿于狹小的一隅,讓我們喪失掉體驗終極實在的原發視野。文學需要秉持的始終是詩性思維,而非知性思維。詩性思維可以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從概念化、凝固性、本質主義的理論范疇中解放出來。從這個角度而言,文學是永恒的,她有如一脈意識的泉水,有如一抹思想的流云,有如一處心靈的夢境。
所以,永遠有多遠,文學就有多遠。我們把遠方交給彼岸。彼岸是實在的,也是虛幻的,出發了,你就莫要停留。彼岸在召喚,隱約但是堅定,那將是我們生活的方向——心的方向。
(畢曼,著名學者,博士,湖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
- 今古傳奇·當代文學的其它文章
- 魚雁杳 水云重
- 清明帖(組詩)
- 影響力人物——高曉暉
- 憶秋滋味
- 契約
- 引譬連類之法,沉郁頓挫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