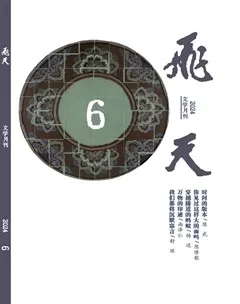小城敘事與現代性追求(評論)
白曉霞
作家楊逍出生、工作、寫作于甘肅天水,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甘肅天水有著“羲皇故里”之稱,是文學創作的寶地和福地。但是,已頗具人生閱歷的作家卻沒有讓筆致過多停留在歷史深處,而是更愿意讓小說直面當下復雜紛紜的人和事,現實和理想的矛盾被一點點撕開。于是,一種特殊的文本面貌出現:在歷史文化背景與現代性語境的碰撞、對接之中,擁有理工科教育背景與多年職場復雜體驗的作家楊逍的創作選擇了“向內求索”的路徑,形成了某種“心理小說”的類型:比較關注人物的心理困境并試圖理性分析困境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可能得到救贖的現實路徑。這樣的基本創作理路,無疑使得楊逍的小說超越了我們循著慣性所能想象的西部鄉土語境帶來的文本面貌,小說確實因之而帶上了某些現代性的色彩,在甘肅作家的小說創作中有著較強的辨識度。早在楊逍的小說集《天黑請回家》的一些篇什中,就體現出了上述心理小說的色彩,而小說中大多數故事發生的空間似乎仍有著西部村鎮色彩,也許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即作家試圖在西部文化的特定語境中破解現代性的文化命題,2013年《天黑請回家》在《創作與評論》(現《湘江文藝》)發表后,即被《中篇小說選刊》轉載,引起了文壇的一定關注,隨后出版的小說集《天黑請回家》也獲得了第五屆黃河文學獎。
很明顯,楊逍的小說新作《鏡身》與《穿越隧道的螞蟻》依然在延續著前述“心理小說”的某些特點。但是,經過了三年疫情、下鄉扶貧、人到中年、人事更替等各種主客觀環節洗禮的作家,自然而然會為文本注入一些新的元素,開始更聚焦關注在無情的小城時間之河中無奈漂流的小人物的心理生活,他們平凡渺小,面對生活的重壓時常陷入無力無奈感和虛無絕望感。作家以先鋒筆觸和現代性意識聚焦關注了“小城小人物”的“暗淡心理”,乍看文本表面灰色沉重,而在結尾處卻往往有一道雖然微弱但從沒有熄滅的光亮加持著即將完全崩潰的主人公走向了另一種重生。獨特的“暗淡心理”敘事使得文本帶上了現代性意味,結尾刻意閃爍而出的光亮一筆又提醒我們文本的根還是在溫情敦厚的西部鄉土文化之中。于是,楊逍小說文本的內涵展演路徑便在城與鄉、絕望與希望、現代性與傳統性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異的悖論式的對接,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作家主體性意識的矛盾與掙扎、放棄與堅守、沉淪與升華。文本敘事總體上比較成功,人物、情節、主題指向都在敘事中不斷分裂,形成了某種出人意料的戲劇效果,從而使文本擁有了一定的閱讀張力,較強的可讀性承載著較深的思辨性。
《鏡身》是一則關于小人物命運的黑色預言,前半部分凝重悲觀,可貴的是,在結尾處作家主體會同人物形象客體一起做了不甘沉淪的掙扎與突破,讓讀者心生暖意,體會到的仍是“人間值得”的欣慰。小說中的“我”是一個一事無成的小公務員,在工作借調中奉獻青春,蹉跎歲月,漸漸失去了晉升的機會,平庸而消極的“我”在家庭和社會中都被邊緣化:“我越是安靜的時候,我就越是深陷于這種自我懷疑中……我就像是砧板上一小塊瘦肉,再也不能與整個牛身融為一體,面對挑剔的顧客發出的‘這一小塊是不是這頭牛的一部分的質疑。”作品的前半部分盡管彌漫著消極壓抑的氛圍,但依然是現實主義基調,“我”行尸走肉一般提前脫離了社會,受到出身優越的妻子的嘲笑與嫌棄。后半部分卻用一個西方心理學上的陌生語匯“鏡身”讓作品陷入了神秘主義的敘事氛圍,所謂“鏡身”就是另一個“我”,可能是前世也可能是來生。那個尋蹤而至的陌生的年輕人自稱是“我”的“鏡身”,人生的上半場與“我”一模一樣,要從“我”身上尋找他人生下半場的正確答案。然而,“我”卻是一個愛情上的負心漢,是一個事業上的失敗者,是一個連自己都覺得厭惡的“兩面人”:“我成了一個完全兩面的人,及至現在,我已經無法將我的分裂合二為一,可我又多么想合二為一啊。”“我”早已習慣了自己丑陋消極的面目,然而,在面對執著尋找“鏡身”的對生活充滿希望的下一代年輕人時,“我”突然醒悟,羞愧無比,年輕人的執著單純及對美好生活的無限憧憬終于激勵“我”決心重新振作起來。于是,在小說的結尾處有溫暖的“陽光”照在百草山。陽光終將沖破烏云,這是宅心仁厚的作家在人物最后的精神死亡關口為讀者打開了真善美的大門,新鮮空氣如潮水一樣涌了進來,“我本渺小”的平凡生命終于如火中鳳凰一樣涅槃重生。
《穿越隧道的螞蟻》中表達的依然是小人物的黑色生活,想象生動而鮮活:“我”的“生理的病”與“心理的病”扭結在一起,如令人窒息的蟻群撲面而來,好在結尾處這些消極絕望的情緒終于被世間最為可貴的親情做了溫柔阻攔,依然有著幾分好人終得好報的隱喻意味。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消極頹廢的中年人,在作家筆下,這個生活在小城鎮的普通人常年的“暗淡心理”情有可原:夫妻不睦、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事業平淡無奇。小說的開篇部分筆調散淡甚至帶著幾分慵懶的意味,頗有90年代新寫實小說中“小人物小事情”的痕跡:“在我們分開的最初一年里,我一直認為我們的那次分歧是一次意外,不就是我抽煙的時候不小心把她放在沙發上的一條新裙子燒了個洞嘛,大不了再買一條好了。我一點兒都不覺得那條裙子有多好看。”平淡到無聊的煩惱生活讓主人公壓抑到近乎崩潰,被現實生活深度異化的他竟然擁有了神奇的感覺能力,為了確切表達這份神奇的感覺,作家漸漸從新寫實的手法過渡到了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讓人物從現實走向了虛擬,又在虛擬中努力追求著現實,“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視聽幻覺:穿越隧道的螞蟻。這種在醫學上被稱之為“顳葉癲癇”的疾病帶來的幻覺死死控制著“我”,“我”卻相信“穿越隧道的螞蟻”是真實存在的,“我”的肉體常常因之而昏厥甚至可能會死亡:“我從另外一個反方向,在隧道里飛奔,而隧道越來越窄,越來越細,直到成了一個針眼大小,而我執意要從這個針眼里穿過去,去解救那只即將面臨危險的螞蟻。我想變成一只螞蟻,那樣我就能從那個針眼里鉆過去了。但我鉆不過去,我憋足了勁,屏住呼吸,我真的渴望我的呼吸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終于,在無比沉重又非常孤單的庸常生活中,“我”的“病”日重一日,幻覺完全控制了我:“后來,我成了螞蟻中的一員,而不是螞蟻的拯救者。”而唯一能讓“我”保持最后一點清醒的人,是父親和女兒,或許,作家想說,在亦真亦幻、亦實亦虛的小人物的平凡單調的生活軌跡中,似乎只有親情的力量才能讓主人公保持著最后一點理性與尊嚴。而那個中年喪妻、女兒又不學無術的可憐的瘸腿鞋匠巴赫則是作家筆下另一只“渺小的螞蟻”,也正是因為把全部的愛都無條件的給了女兒,巴赫這只“渺小的螞蟻”才被渡化成為一個偉大的父親。
顯然,楊逍的兩篇小說都有著心理小說的味道:重視探索人物的精神困境以及救贖之路,文本的某些部分帶有明顯的意識流痕跡。然而,與絕大部分同大都市文化臍血相連的心理小說不同,這兩篇小說有著比較明顯的小城敘事意味:“小城里的小人物”被沉重的現實生活異化,消極悲苦,找不到靈魂救贖的出口。于是,在停頓與前行之間,在墮落與飛翔之間,他們滿載著痛苦與分裂,又充滿了掙扎與不甘,這或許是后疫情時代文學創作的某種必然選擇。好在,天性善良的作家最終都讓主人公有愛可以憑借,有力量可以前行,終于為讀者撥開了滿天烏云,帶來了一道陽光。客觀地看,在甘肅的小說作家中,楊逍所創作的這種聚焦關注人物被現代生活所異化之后的特殊心理的小說類型還是比較獨特的,其上充溢的思想上的現代性意味與藝術上的先鋒性探索確實還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綜上所述,楊逍的小說《鏡身》《穿越隧道的螞蟻》從心理學的角度入手,書寫了一種“小城小人物”身上所承載的現代性困境,寫作意識先鋒、筆觸精致冷峻、情感體驗細膩。“作為一個心理學范疇,現代性不僅是再現了一個客觀的歷史巨變,而且也是無數‘必須絕對地現代的男男女女對這一巨變的特定體驗。這是一種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可能性與危難的體驗。恰如伯曼所言:成為現代的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這樣的境況中,它允諾我們自己和世界去經歷冒險、強大、歡樂、成長和變化,但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們卷入這樣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那兒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為現代就是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馬克思所說,在那里,‘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①確實如此,楊逍的小說為我們展現了這種共性的“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和痛楚”,與此同時,小說也形成了值得稱道的個性化特色:一方面,作家對人物在“小城之中”產生的由壓抑而至分裂的心理體驗的理性冷靜的描寫讓我們容易聯想到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施蟄存的小說《梅雨之夕》,現代性敘事追求明顯。另一方面,善良的作家卻又不忍心真的讓人物墮落、變形、粉碎、毀滅到萬劫不復,所以,結尾處總有陽光閃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或被青春的明凈所打動,或被永恒的親情所擁抱,現代性敘事終于止步在人物精神分裂的邊緣,最終化成了盡管微弱卻依舊溫暖的一束光,這束光回護著人物形象身上最后的精神的整體性,使其在危險的懸崖邊完成了救贖,如過河之舟,渡化人心走向真善美。基于此,我們似乎有理由做出這樣的判斷:這束“護人性于周全處”的文化之光來自底蘊深厚的“羲皇故里”天水,來自廣袤敦厚的西部大地。一般認為,現代化所取得的科技與物質方面的成就與帶來的某些弊病(如因空氣惡化、資源減少、生態變差、物質至上帶來的精神困境)都與工業文明有著密切聯系,如前所述的“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和痛楚”的現代性困境也由此產生,毫無疑問,以“人學”為內核的文學對破解人類的現代性困境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而農耕文化長期以來的穩定性以及所推重的天人合一等“大自然中心”理念,有可能會為破解因“人類中心主義”理念而產生的現代性困境提供啟發。甘肅天水有著深厚的農耕文化積淀,理應得到本土作家更多的重視,在理性研究農耕文化的過程中思考解決西部當代文化現代性困境問題,或許是甘肅作家的重要使命,從某種角度看,甘肅作家在面對上述問題時,似乎也具有某種潛在優勢。目前看來,楊逍的小說創作似乎進入了長篇發力期:2023年11月,長篇小說《從來惜》獲得天水市委宣傳部文藝扶持項目立項;2023年3月,長篇小說《柳生芽》與重慶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將于2023年內正式出版。我們無從得知他新作品的具體內容,但“心理小說”也許依然會是他前行的重要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寫作中確實不必刻意回避在西部語境中探索人的現代性的問題。前已述及,農耕文化在中華大地歷史悠久、根脈深厚,其中的優秀因子對破解現代性困境有益,對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有益,對中華民族文化復興有益:“文明史編撰,要有中國視野和中國特色。中國視野就是用中國人的眼光看世界;中國特色,則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運用中國史學編纂的傳統和方法,對世界各國的文明史進行研究和闡釋。”②甘肅天水有著深厚的農耕文化底蘊,是傳說中中華民族人文始祖伏羲誕生的地方,傳說母親華胥氏“歷十二年而生伏羲”于成紀,伏羲“一畫開天,肇啟文明”。文學是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看,甘肅作家對于現代性問題的成功書寫或許會超越文本本身,產生更為重要的文明史意義。前述的小說文本也正顯示出了楊逍在這一方面的探索以及相應的功力,這樣的文學面向,是值得繼續開掘的一座富礦。當然,道阻且長,上述的文化使命必然也會對甘肅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作家在理論學習、經典文本閱讀、文史哲融通等方面進一步下功夫,以便為真正優秀的經典文學文本的產生提供根性營養。
①周憲、許鈞主編,卡林內斯庫著,顧愛彬、李瑞華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總序,商務印書館,2010年。
②朱孝遠《文明史研究的中國視野》,《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1期。
責任編輯 郭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