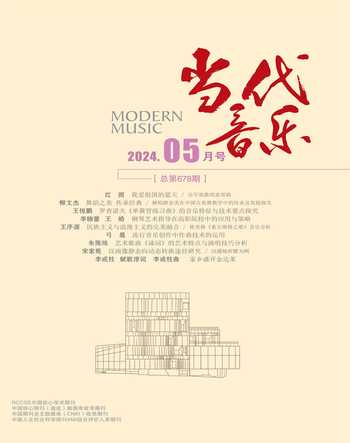我國地方志中音樂史料的價值與開發(fā)
張沐
[摘 要] 地方志又稱為地志、地記等,主要記錄了我國各個地區(qū)的文化習俗、自然風貌以及社會發(fā)展現(xiàn)狀。地方志為歷史學者研究音樂史料創(chuàng)造了便捷條件。鑒于此,本文以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方音樂、清朝時期廣西地區(qū)地方音樂以及漢唐時期的瀟湘音樂作為研究對象,對其中記載的音樂史料展開分析和研究,并對史料中蘊藏的價值進行深入挖掘,以供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 中國地方志;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料
[中圖分類號] J609?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24)05-0192-03
我國地方志記載經(jīng)元、明、清三代,發(fā)展較為穩(wěn)定。地方志中的內(nèi)容繁多,為后世研究我國不同區(qū)域的風俗民情提供了史料依據(jù),同時地方志中記載的社會風俗和文化風俗也對現(xiàn)有的文化價值開發(fā)提供了參考和借鑒。
一、地方志中音樂史料的區(qū)域性溯源
地方志是我國古籍著述中較為重要的一個分支,在我國歷朝歷代的文化古籍中占有較高比重。作為能夠管窺各地文化、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的區(qū)域性古籍類別,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保存下載的地方志大約有8000多種,共計10000多卷,時間跨度自宋元至今均有著述。如此大體量的著述,在我國歷史上除正史著述外,成為具有系統(tǒng)性、功能性、區(qū)域性的代表性古籍之一。其中豐富的史料內(nèi)容,為研究各時期區(qū)域文化發(fā)展提供了大量史料。史料是研究歷史的基礎,以音樂史研究為例,針對音樂史料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需要參考各類歷史資料。我國發(fā)展歷程較長,擁有的史料典籍眾多,正所謂史料均收,記載完全。然而從歷史層面分析,一些史書在記載歷史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xiàn)記載斷層的現(xiàn)象,部分史料內(nèi)容還會出現(xiàn)缺失和記載不完全等現(xiàn)象。
我國大多數(shù)史料以正史為主,其記載的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而偏遠地區(qū)往往被忽略,同時音樂類史料也以宮廷雅樂為主,未能全方位展現(xiàn)我國古代區(qū)域音樂文化。地方志以記載地方歷史為核心,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又被稱為“博物之書”,其地域性非常顯著。主要記錄了特定時期、特定年份以及特定地區(qū)的社會、文化、經(jīng)濟等各方面內(nèi)容。地方志只記載本地區(qū)的事情,由于各地的自然環(huán)境、人文政治、地區(qū)風俗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且編纂人員對于區(qū)域性特征的重點論述,使得地方志記述時主觀性較強。也就是說,從正史能夠了解史料的詳細面貌,而從地方志則能感受到強烈的區(qū)域風格。對于那些涉及全國的事件,地方志只詳記和本地區(qū)有關的部分,其地區(qū)性特點,成為研究區(qū)域音樂史料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方志以外的地方文獻,大多各自有一個側(cè)重面:有的記歷史,有的記現(xiàn)狀,有的記地理,有的記人物,有的記政治經(jīng)濟,有的記文化藝術,有的只記一時一事。只有地方志,它的記述以最近一段時期(一般是幾十年)的現(xiàn)實狀況為主,同時要兼敘歷史沿革,無論天文地理、名勝古跡、資源物產(chǎn)、民族、宗教、風俗以及政治措施、軍政機構、典章制度、經(jīng)濟狀況、文化科學、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以至方言俗語、金石碑刻、天災人禍、故事傳說等,只要和這個地區(qū)有關,統(tǒng)統(tǒng)屬于它的記述范圍。也就是說,任何地區(qū)自古以來均有音樂形式和內(nèi)容的存在情況,而針對地方志中音樂史料的研究,則會對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區(qū)域的音樂記述情況有詳盡且真實的紀錄,如《(光緒)山東通志》卷一一○至一一三為“典禮志”,其中詳細記錄歷次典禮的經(jīng)過和儀式,包括舉行儀式用什么器具,用什么樂器等等,同時也記載其他各種官方的和民間的禮儀。這些記載不僅能夠窺探地區(qū)音樂文化發(fā)展歷程,還能從其他方面思考音樂文化流變的緣由。
其中地方志音樂史料中又包含了當?shù)氐亩Y俗祭祀、婚喪嫁娶、樂器樂譜等內(nèi)容。自從地方志有所記載以來,對地方志進行撰修編撰,成了相關史料記載人員的重要工作內(nèi)容之一。民族音樂集成具有的“音樂的地方志”性質(zhì),其所包含和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題材方面是十分豐富的。[1]因此通過對地方志史料的有效研究和深入調(diào)研分析,不僅可以挖掘其中蘊藏的優(yōu)秀文化,同時還可以更好地研究地方發(fā)展歷史。
地方志史料的資料搜集、編撰以及推廣應用多由官方完成,因此很多地方志又被稱為官書,這也從側(cè)面體現(xiàn)了地方志的重要性。記載地方志的過程中,必須真實地反映當時的史實,還原事物的原貌。[2]在本文中,筆者以區(qū)域地方志中音樂史為核心,對其中蘊藏的各類樂器、樂譜、音樂現(xiàn)象展開深入研究,同時也對完善我國地方志音樂史料記載提供對應的借鑒依據(jù)。
二、地方志中有關少數(shù)民族
音樂史料的分布情況
在我國傳統(tǒng)地方志中,主要針對一些較為官方的音樂進行記載,而針對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的記載內(nèi)容較少,導致該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核心原因有二:一是我國古代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二是傳統(tǒng)漢族文化中心論因素影響。同時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在地方志記載的過程中,可能會對部分地區(qū)的史料進行零星記載,而這些記載內(nèi)容也主要以祭祀風俗和藝文志有關。
綜合來看,在我國地方志中比較典型的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料包含以下幾類。
(一)清朝《西域圖志》中的音樂志
《西域圖志》中所載的音樂志,記錄了我國邊疆地區(qū)——新疆的主要日常活動。著述過程中,對于古時西域地區(qū)的風貌和知識,除記錄清朝時期特征外,還將官方正史與考證材料融入其中,可以更好地幫助大眾了解古時西域的相關知識,同時也對一些訛傳和野史進行了更正,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在《西域圖志》中曾記載:“回部”和“準噶爾部”專設音樂子目,又將音樂子目分設為樂器、樂譜等各個分項條目。其中的“準格爾部”中,對樂譜和樂器進行細分,還記述了圓布什爾、伊奇爾呼爾、雅托噶、特木爾呼爾等傳統(tǒng)樂器的演奏方法;“回部”則記錄了哈爾扎克、喇巴卜、巴拉曼等少數(shù)民族運用傳統(tǒng)樂器演奏的方法與行為,同時還兼述樂舞表演形式。這些對于邊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樂器、樂舞、樂歌的記載,可以更好地幫助現(xiàn)代人了解到我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民族音樂的整體發(fā)展歷程,將其完整、真實、形象地呈現(xiàn)在大眾眼前。為音樂史研究學者研究我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音樂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
(二)《云南志蠻夷風俗》中的音樂記述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少數(shù)民族眾多,尤其是在我國的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數(shù)量人口眾多,通過對我國邊疆地區(qū)地方志的深入研究,可知古代不少學者對我國西南邊陲地區(qū)的蠻夷風俗進行了分析。以《云南志蠻夷風俗》為例,該地方志中就記載了我國西南邊陲地區(qū)的民族風貌,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和有機性。《云南志蠻夷風俗》共計10卷,涉及的內(nèi)容主要介紹了云南地區(qū)的風俗地貌、婚喪嫁娶、音樂、舞蹈等。通過深入研究《云南志蠻夷風俗》中的相關內(nèi)容可知,雖然其介紹的篇幅集中在蠻夷風俗這一方面,針對音樂內(nèi)容記載較少,但是仍能直觀地了解到我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音樂活動。
(三)《廣西通志》中的音樂記載
雍正時期的《廣西通志》中共分為128卷,主要內(nèi)容有政治、經(jīng)濟、歷史、蠻夷文化、藝文、音樂等。蠻夷地區(qū)主要介紹安南以及諸蠻部落。在《廣西通志》中主要的介紹區(qū)域集中在廣西區(qū)域,同時還對廣西周圍的少數(shù)民族歷史風俗進行了記錄,對廣西當?shù)馗鱾€民族的分布情況進行了詳細記載,具有極高的地方志研究價值。在《廣西通志》的風俗篇中,和音樂相關的介紹內(nèi)容共有6段,可以真實地向讀者反映我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對音樂的喜愛程度。少數(shù)民族音樂類型多以婚喪嫁娶為主,不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受經(jīng)濟繁榮程度影響,其風俗和禮儀存在一定的差異。[3]在《廣西通志》的諸蠻篇中,對我國廣西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資料進行了著重闡述,其中有關音樂的研究內(nèi)容共計有117段,該地方志中詳細描述了瑤族男女對歌的場面。瑤族男女通過對歌來互相抒發(fā)愛慕之情,是一項非常熱鬧的民俗活動,該對歌風俗一直沿襲至今,被很好地傳承下來,是廣西當?shù)胤浅>哂写硇缘拿耖g音樂活動。同時《廣西通志》中還對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日常生活內(nèi)容進行了記載,而唱歌內(nèi)容始終穿插于其中。縱觀苗族、瑤族、侗族這類少數(shù)民族的發(fā)展歷程,可知音樂文化史在其歷史發(fā)展中占有較大比例。音樂多用于祭祀、生產(chǎn)等日常活動,不僅可以滿足精神需求,同時還滲透于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日常生活領域。《廣西通志》在雍正初年時期曾被刪改,其中包含一些少數(shù)民族音樂相關內(nèi)容,對研究我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音樂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男女對歌活動自古已有。少數(shù)民族的音樂往往和民俗活動相互融合,其中最為常見的是以唱歌的形式來表達和傳遞情感。在地方志中記載了大量苗族男女唱歌習慣的內(nèi)容。通過研究地方志內(nèi)容,可以深入了解廣西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群眾當時的生活軌跡和風俗,男女通過這類民俗活動可以盡情放歌,享受唱歌的樂趣。
三、地方志中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料
的研究價值分析
張舜徽先生曾這樣說過:“宋代學者氣象博大,學術途徑至廣,治學方法至密,舉凡清代樸學家所矜為條理縝密、義據(jù)湛深的整理舊學的方式與方法,悉不能超越宋代學者治學的范圍,并且每門學問的講求,都已由宋代學者創(chuàng)辟了途徑,準備了條件。宋代學者這種功績,應該在中國學術史上大書特書,而不容忽視或湮沒的。” 宋元祐年間的鄭興裔在《廣陵志序》中就明確提出:“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察民風,驗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鑒,甚重典也。余奉簡書,自廬移守茲土,表章先哲,利賴兆民,日求康治,而文獻無征,心竅悼焉。”宋代方志的作者,開始注重方志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強調(diào)要有補于風教,有益于政事。也就是說,宋人對方志的新認識,并逐漸賦予它新的使命,提出新的要求。自此,地方志發(fā)展與正史著作發(fā)展并駕齊驅(qū),且成為正史著作中部分內(nèi)容地域特色的補充部分。
于音樂來說,地方志中所留存下的民歌民謠,歲時風俗,乃是廣大人民在共同生活和與自然界做斗爭的經(jīng)驗總結。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的《烏青鎮(zhèn)志》中《風俗》篇有關歲時風俗的記載中,所載“簽大桔于柏枝上,著之謂百事大吉。昆弟交戚過從飲椒酒,子弟鳴鉦擊鼓以相娛樂,三日為小年朝。”便是對于節(jié)日用樂的考證。又如《淳祐臨安志》卷六《學校》篇所附郡守陳襄的《勸學文》載:“必將風之以德行道藝之術,使人陶成君子之器,而以興治美俗也”。對當時文化藝術培訓的理論體系建設具有時代性的價值。
近代著名學者俞樾(1821—1907)所修之《鎮(zhèn)海縣志》,《學校》一門所載不僅對于學宮歷次興廢重建的過程都有詳盡的記載,各個書院、社學、義學建立原委、規(guī)模都作記述外,對學宮的“祭器”“樂器”“舞器”“齋戒”“執(zhí)事”等,以及祭儀、行禮、奏樂、唱舞的各個節(jié)奏動作都詳細羅列。事實都說明,各種方志的學校門類,是研究我國教育史的很好的園地。還應當指出,方志記載學校,甚至還影響到史學的發(fā)展。眾所周知,正史中從未立過學校志,唐代杜佑所作《通典》,雖然是專講典章制度,但也僅在《選舉典》中講到學校。到了宋末元初,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在方志記載學校的啟示下,搜集了大量資料,在《文獻通考》中專立了《學校考》這個新的門類。這充分證明學科之間相互滲透,互相影響的作用,且能夠通過對于學校門類的記述,了解學校對于音樂人才培養(yǎng)的政策和措施,此乃一舉多得之功。
通過對中國地方志中有關音樂史料的研究,為我國音樂史發(fā)展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史實材料。史書以記載國家大事和重要人物為主,而地方志者則主要記載地方發(fā)展歷程、地方民俗、音樂、文化等重點內(nèi)容,對完善我國的音樂文獻記錄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為學者研究我國音樂史提供途徑。“社會的形態(tài)所提供的社會環(huán)境對音樂的發(fā)生、發(fā)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由于它的影響,一定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規(guī)則都反映在不同形式和規(guī)模的音樂行為里”[4]。因此,深入研究地方志中的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獻,可發(fā)現(xiàn)很多文獻中涉及的內(nèi)容,以風俗節(jié)日、典禮、祭祀生產(chǎn)活動為主,包括人文、自然、地理等諸多內(nèi)容。通過深入分析地方志編撰情況可知,其編纂工作具有詳略得當?shù)奶攸c,主要由史學者進行記載,同時多數(shù)內(nèi)容來自民間,是對當時地方風貌和生活的真實記錄。不僅可以更好地幫助現(xiàn)代人了解古人生活,同時也具有較強的可信度和真實性。
結? ?語
綜上所述,地方志是對我國古代地方歷史風俗文化進行記載編撰的主要史實文獻,也是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不僅涉及前朝后世的歷史發(fā)展情況,同時也包含了各式各類的古人生活風貌,為后代學者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史料的查找與發(fā)現(xiàn)十分不易,是一項十分重要而艱巨的工作。對大量的歷史信息進行梳理、提煉也是耗費學者精力的繁重工作。[5]地方志具有內(nèi)容翔實記載,名目繁多等優(yōu)勢,同時也可以為后人研究地方的發(fā)展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針對地方音樂進行研究,筆者上文中所寫的內(nèi)容僅僅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對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并非一件簡單的事情。在收集地方志史料的過程中,因地方志史料并非為專業(yè)史官所編撰,容易受客觀因素的限制和影響。同時在研究方面,受筆者自身研究能力的限制,可能會對史料的整體應用性產(chǎn)生負面影響。如果僅僅是借助史料來研究歷史,則難以從宏觀層面對音樂文化進行統(tǒng)一系統(tǒng)性的呈現(xiàn),但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只有不斷地積累,才能更好地為研究中國音樂史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1] 馮光鈺,王民基.音樂的地方志地方的音樂志——試論編輯五種民族音樂集成的意義和方法[J].中國音樂,1985(03):5.
[2] 劉莎,顏家碧.地方志與區(qū)域音樂史研究——以清代廣西地方志中的音樂史料研究為例[J].黃河之聲,2022(12):62-64.
[3] 翟書藝.中國地方志中少數(shù)民族音樂史料的價值分析[J].當代音樂,2020(10):72-74.
[4] 洛秦.音樂的構成:音樂在科學、歷史和文化中的解讀[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24.
[5] 秦雪峰.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史著述中的史料探究——評《曾澤霖志忞考》的史料學貢獻[J].音樂生活, 2023(02):4.
(責任編輯:韓瑩瑩)
[收稿日期] 2024-01-05
[作者簡介] 張? 沐(1992—? ),男,博士,江蘇第二師范學院音樂學院講師。(南京? 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