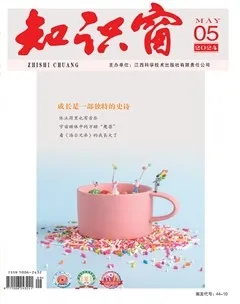海風知意
楊馨悠
親愛的何攸:
我在海島已經一個月有余,俱安排妥當。見你頻頻來信,三五天信便塞滿書店前的小箱子,就連上了年紀的郵遞員都啞然失笑,說我們在通信發達的今天,仍用這種最耗費時力的、最笨拙的方式交換訊息。他說出這話的時候,攤開掌心給我看一個小小的吊墜,里面是他妻子年輕時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大海,海浪拍打著石岸,激起身后一排海浪。那個女士優雅地站在鏡頭前,向自己的愛人微笑。
這使我想起上一封信里隨信寄去的那片樹葉,它與吊墜差不多大。信到時,它大概已經泛黃,但你應能想象出葉脈中蓬勃的生機。你睡眠不好時,可將這片樹葉枕在腦后,它雖無安神效果,但你可做個好夢,不知成效如何。我還未拆開你最新寄來的幾封信,愿你能提到有關這片樹葉的只言片語,以慰我心。
我剛看到你的信,郵票果然是你喜歡的風格。至于文字,依然如此洶涌,如潮水般襲來的情感最終匯聚成這一張泛黃的信紙。親愛的朋友,我們明明已經分開一個月有余,我卻感覺你就像是昨天才來過似的,趴在我的懷里哭泣,濕了我心口的一片衣料。我常常想,大概被文字選中的女生總是如你一般纖細,又同你一樣情緒起伏不斷,就像一葉扁舟行于海浪之間,任憑上下。我偶爾會感到慌亂,仿佛突然踏進迅疾冰涼的小溪,不知該向上還是向下。但友誼就是如此突然出現——如你所說的,當我撫摸那樣渾身炸毛的小獸時,我的心也如同被柔軟的皮毛包裹般平和、寧靜。
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正坐在海島的書店一隅,面前是一扇半開的竹窗,越過窗便是礁石與海,海浪翻滾著拍打礁石,連帶咸濕的海氣涌進窗戶。我的書桌是曾與你提到的那個——父親留給我的,殘缺了一角的實木桌子,不高,我得伏下腰才方便書寫。寫到這里時便知道,你要羨慕我一段時間了,于是隨信再附幾塊小小的碎石,是我心煩的時候常把玩的,朋友小可說將它們捏在手里就像撫摸柔軟的海。若信到時,你病還沒好,愿它能消解一些你病中的沉悶。
何攸,遠方的春要到了。海島也開起花來,不知北方的樹是否生了綠意?
在書店的時候,我曾倚著花和不少來買書或賣書的人聊天。其中不乏穿著藍白校服,如你一般的青春學生,但他們比起你來相差甚遠,讀書匆匆,往往是翻上兩三頁再看看封面就決定買不買。對書店來說自然是好事,只不過在此時我總是想起你,恍惚間,窗口下好像出現了你低頭看書的場景。何攸,我記憶中的你就坐在此時離我不過五米的沙發上,金色的陽光灑過蓬松的發絲間,你的眼像我面前的海一樣深邃蔚藍。
海風迫不及待地吹起我的信紙,吹向你的方向。郵遞員是個喜愛懷舊的理想主義者,他常為我們頻繁的書信往來感到開心。他愿文字不死,在此也算給你我的褒獎。
太陽逐沒,海浪不休。
愿思念與礁石永存。
遠方的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