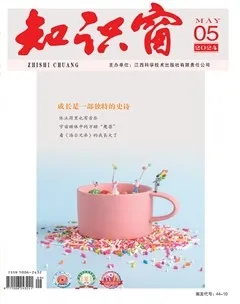春風十里,香粥一碗
陳柏清
陽春四月,北方是春寒料峭,南方是乍暖還寒。民以食為天,在不但要吃得飽,而且要吃得好、吃得健康的時代,何以解腸胃之憂?恐怕是香粥一碗。
我幼時不喜食粥。每日母親做飯,我像條小尾巴跟在她身后,暗暗觀察她舀在鍋里的米,半瓢是煮粥,一瓢是煮飯。如果見母親舀了半瓢,我便會嘟起嘴巴坐在門檻上,悶悶不樂。那時的我哪里知道大人的苦,只知米飯容易飽腹。
成年后,我得了一次腸胃炎,常在半夜疼痛難耐。同寢室的一個大姐連續三天喂我小米粥,幫我調理好腸胃,從此我對粥徹底改變了看法。
粥在平常飲食中可以充饑,在病時可以作為藥療調理。喝粥在中國可謂歷史悠久。從出土的文物和相關歷史記載來看,農耕時代的人就已經知道喝粥這種飲食方式。到宋朝時,已經有各種各樣的粥。宋朝大詩人陸游有詩云“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他形容食粥就如做神仙。《本草綱目》中記載:“食粥補虛益氣,與腸胃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做飯千篇一律,不過是食材改變,粥卻可以花樣百出。在宋朝,由著名醫學家王懷隱撰寫的、官方編撰的《太平圣惠方》里就已經有129種粥的做法,最著名的就是枸杞粥、酸棗仁粥、葛根粉粥。在枸杞粥一方中,王懷隱還特意注明枸杞粥為鮮枸杞與粳米煮粥。粥成后,以咸豆豉佐餐。每日兩次,經常食用可以滋補肝腎,清熱除煩,宣泄郁熱而不傷陰。因為枸杞甘平入肝腎,久食能治虛勞低熱、體虛盜汗,無所禁忌。酸棗仁粥可以滋養心脾,補益肝膽,是治療虛煩、驚悸不眠的良藥,對神經衰弱、失眠多夢的療效甚佳。
宋朝大文豪蘇軾曾經寫過一首《豆粥》,詩中寫道:“君不見滹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這里提到豆粥,說明粥在宋朝早已實現多樣化了。到了清朝,黃云鵠編的《粥譜》共記載了8大類237種粥,品種非常豐富。粥好,連粥米湯也是好的,清朝名醫王士雄說:“貧人患虛癥,以濃米湯代參湯,每收奇跡。”張學良活過百歲,據傳他曾對人說:“我們張家承襲下來的養生之寶還有米湯,我就相信這個米湯的功效。”
在古代,貧苦人家之粥與鐘鳴鼎食之家的粥不可同日而語。陸游日常喜靜不喜動,卻能享年86歲,想來也有食粥養生之功。名著《紅樓夢》更是有許多食粥的描寫。賈府每日飲食多有山珍海味,酒菜、果品、點心源源不斷,當然不會有興致經常吃干飯,粥就成了最好的選擇。譬如有一回,賈母與家人中秋賞月,對于兒孫送上來的菜,只嘗了一兩口,便要拿稀飯來吃。尤氏端上紅稻米粥,賈母只吃了半碗,命將剩下的給鳳姐吃。可見那時,紅稻米做食材熬的粥,是富貴人家才有的。
不僅僅是《紅樓夢》,《浮生六記》中也有多個場景寫到各種食粥。最著名的就是蕓娘為沈復準備的私房粥,由此還衍生出那句愛情名句“立黃昏,粥可溫”。
北方人做粥常用的俚語動詞是熬,南方人用的是煲。一熬一煲,便透出粥絕不是簡單得來。家常日子,小火慢燉,熬一碗香甜的米粥,煲一鍋熱乎乎的香粥,一家人燈火圍坐,慢慢享用,慰帖脾胃肺腑間,每一匙都是時光的贈與,每一刻都是歲月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