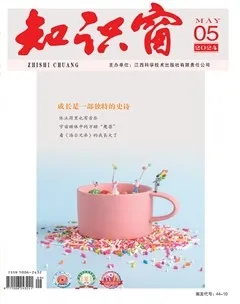聽它鳴聲蕩漾
許冬林
在古詩文里,表示鳴蟲的詞有許多。例如,今人稱為蟈蟈的小蟲,在《詩經》里叫螽斯。當然這也有爭論,有人認為就叫“螽”,“斯”是助詞。如果真是這樣以單字為名,那也是極動聽的名字。還有深秋的蟋蟀,在古人的詩句里寫成“寒蛩”,仿佛有了人生苦短、人世涼薄的嘆息在字里。
關于螽斯,在不同版本的《詩經》注釋里,解釋也不盡相同,有的釋為蟈蟈,有的釋為蝗蟲。我比較了一下蟈蟈和蝗蟲的形貌之異。蟈蟈通體綠色,觸角細長,甚至長過身體,很像戲曲演員頭頂上插的兩根翎子,委實俊逸颯然。清晨,它在露水里沐浴小小的身體,在瓜果藤葉之上跳躍、覓食、游戲,霧散日升時開始鳴唱,音色明亮。而蝗蟲之于蟈蟈,就顯得有武夫的魯莽之相,它觸角短,兩個前翅不像蟈蟈那樣能摩擦生出悅耳的聲音。
如此看來,蟈蟈有文藝氣質,蝗蟲形象庸俗,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繁殖力強,屬于子孫興旺的物種。因此,在社會生產全靠人力的農耕時代,《詩經》里的那首《螽斯》被作為祝賀新婚的民歌。
人類生活于這個星球,與浩瀚宇宙相比,人類實在渺小,所以繁衍生育從來都是一件大事。在遙遠的《詩經》年代,人們通過傳唱民歌的方式描述勞動,吟詠思念,感傷戰爭,還祝福人丁生育。這些都是大地上的宏大敘事。
只是在這些宏大敘事的縫隙里,我常常會流連于那些清秋之夜的蟲聲。
在星月交輝的涼夜,在老屋的墻根下,在沐著夜氣散步經過的林子里,那些昆蟲摩拳擦掌,用翅膀摩擦,一扇一扇地震動空氣。那小小的聲浪像暗夜的海潮,在我的耳膜上潮起潮退,卷起銀色水花。在古詩文里,它們叫螽斯,叫寒蛩。在孩子的捕捉游戲里,它們叫蟈蟈,叫油葫蘆……
在那些素樸的歲月里,我們的生活或許有過這樣一個動人的片刻:在清寂之夜,聽蟲聲鳴唱。
有一年夏秋之際采風,我夜宿一座落在半山腰的賓館,房間前后皆是竹木。我洗過就寢,熄了燈躺下,卻不能入眠。風起時,我聽見窗外仿佛有一片海,那是松濤竹喧之聲。風息時,卻是密室匝匝浮到窗口的蟲聲,似斷又連,似連又斷!我仿佛看見海潮退去,在明月朗照下,小螃蟹、小銀魚、小蝦米在沙灘上翻騰著小身體——那么多小生命在月光下閃耀著光澤!是啊,在悠長的蟲聲里,我仿佛看到這些山野小蟲身上的光澤,那是生命稚嫩生長又蓬勃繁華的光澤。
聽著這樣的蟲聲,真讓人想家。
真讓人想念童年,想念少時,想念曾經的鄉居歲月。
唐人張籍有詩《冬夕》:“寒蛩獨罷織,湘雁猶能鳴。月色當窗入,鄉心半夜生。”
中國文人的思鄉之心無處不可寄托,夜來對月會思鄉,白日里看春風吹綠大江兩岸會思鄉,日暮時分行舟煙波之上會思鄉……可是,最深情的一定是在蟲聲里思鄉吧。
在濕漉漉的他鄉清夜,我聽著“吱吱吱”“唧唧唧”……像聽著方言,聽著鄉音。這方言和鄉音是外婆在月下的籬笆邊給童年的我講古老的故事。
我讀著《螽斯》,耳邊仿佛又響起繁密的蟲聲。蟲聲蕩漾,夜夜在織誰人的故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