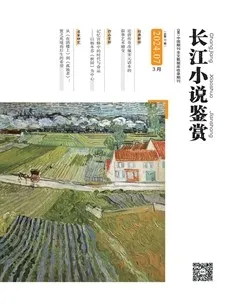從《在酒樓上》到《孤獨者》:置之死境而后生的希望
張捷
[摘要]《在酒樓上》和《孤獨者》是橫跨魯迅“第二次絕望”時期的重要作品,也是魯迅自我色彩最重的兩篇小說,它們之間有一種“延續性”。本文將從兩篇小說在人物塑造與情節設計上的遞進與“延續”著手,結合魯迅切實的人生經歷與情感體驗,分析魯迅隱含在兩部作品背后的人生心態轉變。
[關鍵詞]魯迅? 《在酒樓上》? 《孤獨者》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07-0086-04
自1923年遭遇第二次絕望后,魯迅以小說集《彷徨》打破了長達一年的沉默。他曾在《吶喊》的自序中寫道:“希望是在于將來的,絕不能是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1]如果說《吶喊》的寫作是為了點燃鐵屋毀壞的希望,那么《彷徨》則是魯迅在那份希望破滅后,努力從絕望的灰燼中涅槃新生的嘗試。《在酒樓上》和《孤獨者》是《彷徨》中魯迅自我色彩最濃重的兩篇小說,創作時間相隔一年零八個月,雖說兩篇文章的人物、故事情節并不相同,但其中蘊含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甚至存在某種“延續性”。這種“延續性”是魯迅個體意識的探索,或許可以從中窺見“彷徨”的本質,因此需要將兩篇小說對照解讀,才能真正理解魯迅的創作心態。
一、現代知識分子形象的進階
呂緯甫和魏連殳都是經歷五四思潮由高轉低的新派知識分子,他們不再認同傳統文化中保守迂腐的思想,對現代文明有著先進、獨到的見解。但當那個狂飆突進的時代陡然落幕,他們真正走向民眾時,慘痛的現實才擺在了他們面前。這種個別覺醒者與未開化群眾的對峙,實際上是文化個體與文化群體之間的沖突,這無異于以卵擊石,任重而道遠。不同于單一文化的擁護者,新派知識分子是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群體,一方面他們所接收的現代思想崇尚打破舊有桎梏,建立自由、民主、科學的新時代主張。另一方面,在與民眾認知博弈的過程中,他們也意識到雙方力量的懸殊,為了基本的生存,絕大部分的新派知識分子選擇在表面上向舊有傳統妥協,但心中仍懷有反叛與“立人”的希望,這種分裂的痛苦讓他們成為時代的“孤獨者”。在魯迅的人物刻畫中,呂緯甫和魏連殳雖同為失意的新派知識分子,但在五四退潮后的心態轉變上卻有些不同。
當希望落空,呂緯甫展現出頹唐消沉、麻木嗜酒、隨遇而安的一面。為了謀生,他在同鄉的家里教著過去堅決反對的“子曰詩云”,用“他們的老子要他們讀這些;我是別人,無乎不可的”[2] 來解答“我”的疑惑,也借以寬慰自己。在與“我”交談的過程中,呂緯甫反復強調自己以前所行皆為“無聊的事”,可無論是給小兄弟遷墳還是為阿順買花,他都沒有一絲敷衍。在為弟弟遷墳時他感到高興:“愿意掘一回墳,愿意一見我那曾經和我很親睦的小兄弟的骨殖。”[2]面對母親要求給阿順買剪絨花,即便輾轉多地,他也是“并不以為煩厭,反而很喜歡”[2],由此可見呂緯甫做這兩件事并非完全是奉母之命。既然如此,為何仍覺無聊呢?細讀文本,不難發現呂緯甫對這兩件事“無聊”的評價,以及對自己當前“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狀態形容皆出現在故事敘述的尾聲,這兩個事件的共性在于:呂緯甫都曾對此懷抱過希望,但事實是小兄弟的墳蹤影全無,順姑還沒等到屬于她的剪絨花就早已離世。如此“希望落空”的感覺是否一如五四思潮的由高轉低呢?因而我們不妨猜測呂緯甫所說的“無聊”,或許是因為他曾努力付諸行動的每一件事,最終都徒勞無功,結果總是像他同“我”所說的“等于什么也沒有做”一般,于是也就如此渾渾噩噩地生活著。
比起呂緯甫逐漸接受在無聊中消磨的頹唐心態,魏連殳的心理斗爭則更加矛盾、激烈。祖母去世后,他為了謀生一而再地遷就,先是拜托“我”為他留心生計,即使是為知識分子所不齒的、工資低廉的“鈔寫”也愿意去做,最終多次無果后妥協做了杜師長的顧問。在給“我”的回信中,魏連殳難掩憤激之情,他稱愿意自己活下去的人已經不在,自己卻要為不愿自己活著的人而活,他決心為生存“躬行先前所憎惡”,最為荒誕的是,他的徹底絕望竟然換來之前以真心渴求的一切尊重,昔日冷清的客廳在他繳械投降后變得富麗熱鬧,“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但也有“新的鉆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3]他一邊自我唾棄,一邊萌生了“復仇”的快感,如此激烈的矛盾一直撕扯著他,致使他到死都冷笑著看待這個荒誕的世界,他永遠無法同呂緯甫一般,在無聊中慢慢自我說服。
呂緯甫代表著一類無奈向現實妥協,但勉強能在人群中立身的新派知識分子。從他“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自嘲中尚可以窺得一絲不甘,但這絲不甘很容易就會在一樁樁“無聊”的事中,被現實與未來的無能為力所擊潰。在魯迅為他所作的結局里,呂緯甫是仍在掙扎的,他雖然極大可能會被磨平心性,但總歸還是“隨隨便便”地活著,或許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他所選擇的是一條委曲求全的自我壓抑之路。然而魏連殳則是選擇了自我毀滅式的復仇之路,魯迅描述他是一匹“受傷的狼”,曾經卓爾不群的異類在被現實多次無情驅逐后,帶著對族人親情的蔑視以及對孩子的絕望一同選擇了自我戕害,他決心徹底拋棄過去苦苦堅守的信仰,絕望地走向自己所憎惡的,這是他獨特的復仇方式。故事的最后,“我”對他告別時,看見魏連殳的遺體似乎在冷笑,這不由得讓人深思,這個躺在棺材里,穿著不合適衣服的人,究竟是曾經孤憤的魏連殳,還是那個“魏大人”?呂緯甫與魏連殳的一生既可以看作是兩種不同類型現代知識分子的人生,也可以視為同一個知識分子經歷的兩次心態轉變,如果說呂緯甫身上尚存有一些失望后零星希望的掙扎,那么魏連殳則是展現出一位現代知識分子徹底絕望后的崩潰。
二、小說情節設計的遞進
《在酒樓上》和《孤獨者》不僅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繼承性,在小說的情節設計方面也有著濃烈的遞進色彩。換言之,“《在酒樓上》提出的問題,在一年零八個月之后的《孤獨者》中有了答案”[4]。
首先是在親人角色的設置上。呂緯甫之所以能夠在“無聊”的日子中掙扎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仍保留著與他人的聯結,尚未被群體所驅逐,這些聯結中最為重要就是“母親”,無論是給小兄弟遷墳,還是為阿順送剪絨花都是緣于母親的命令。作為一代先覺者,呂緯甫本該是同“我”一樣覺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2],他們與家鄉之間有著鮮明的割裂感,逃離家鄉應該是許多新派知識分子共同的人生期望,呂緯甫原本也不想做飛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蠅子,可現實倒逼他們回到原點,支撐他們留在原地的唯一緣由便只能是親情,親人的意志成了他們最后的寄托,可倘若沒有這份羈絆呢?魯迅在1925年的《孤獨者》中給出了答案,故事一開頭,魯迅直接從魏連殳祖母的葬禮寫起,魏連殳的境遇比起呂緯甫而言顯得更為寂寥,祖母還在時,他便已經作為異類,被家族與鄰里所不容,祖母的去世讓他徹底淪為世間的“孤獨者”。于是,他在孩子身上寄托啟蒙的希望,對房東家的孩子關愛有加,真是“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寶貴”。他以為孩子們的天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但當孩子連他的花生米都不要時,他開始嘲弄自己以往的希望,繼而瀕臨絕望。由此可以猜測,興許沒有母親意志驅使的呂緯甫也會像魏連殳一樣,喪失生存的動力,在“無聊”中走向“孤獨”,最終自我毀滅。
情節的遞進還體現在小說敘述者“我”與呂緯甫、魏連殳的距離上。“我”與呂緯甫算得上是故友,曾一同學習現代思想、反抗封建腐朽的傳統文化、議論國家的改革方法。小說一開始故友相逢的情節就給整個故事蒙上了一層回憶的色彩,在與呂緯甫的交談過程中,“我”更多充當著一言不發的聽眾,被呂緯甫的講述帶回過去。這里的“我”是隱藏在暗處的,“我”雖同情故友的現狀,驚訝于他巨大的性格轉變,但交談全程,“我”都不曾與他有過除去推動情節發展外的互動,“我”的情緒是藏在暗處的,以至于讀者很難辨別“我”對呂緯甫的態度,直到小說最后“我們一同走出店門,他所住的旅館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門口分別了”[2],才就此點明:“我”和呂緯甫終究還是分道揚鑣了。由此可見,《在酒樓上》“我”與呂緯甫雖然曾經關系稍近,但相逢后的靈魂距離卻已經飄遠,那么作為小說敘述者的“我”又究竟是否有些認同故友的觀點呢?這是相當朦朧的,也是魯迅為讀者留下的思考空間。《孤獨者》則是完整介紹了“我”與魏連殳相識的始末,“我”與魏連殳本無交集,恰巧因為他祖母的喪事得以在人群中遠遠一窺這個傳聞中的“異類”,也是因為好奇心驅使“我”順路吊慰,這才有了第一次正式見面。縱觀整篇小說,“我”一直與魏連殳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某段時間常常拜訪他,一是因為“無聊賴”,二是因為“他倒很親近失意的人”,可失意人不會永遠失意,當“我”尋到合適的生計后便沒工夫再訪問他,在小心忙碌中“自然也就無暇記得連殳。總之:我其實已經將他忘卻了”[3]。雖然“我”與魏連殳之間的關系并不親密,但與《在酒樓上》不同,《孤獨者》中的“我”與魏連殳產生了真正的對話,又或是說“辯論”,魏連殳認為孩子們性本善,“我”卻以為“惡花果”是由“惡根苗”導致的,辯論最終以“連殳氣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開口”告終。此后小說還多次描述了類似的辯論場景,有時是以“我”和魏連殳的討論對話進行有聲的互辯,有時是以兩人的沉默進行暗辯,但無論何種,在《孤獨者》里,讀者可以聽到“我”和魏連殳兩個獨立的聲音,至此,小說敘述者“我”與魏連殳徹底拉開距離。
三、置之死境而后生的希望
無論是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的進階,還是情節設計上的遞進,又或是“我”與主人公距離上的逐漸拉遠,歸根究底反映的都是魯迅個體意識的探索過程。
呂緯甫做的兩件“無聊的事”在魯迅的生平中都有跡可循,緯甫的小兄弟對應的是魯迅的四弟椿壽,他在六歲時不幸夭亡,魯迅曾回鄉為他遷葬,一如小說中的遷墳;阿順的原型則是周家一個很能干的少女,她的病亡與未婚夫的哭悼,皆實有其事[5]。至于《孤獨者》中的魏連殳,魯迅曾對胡風說“那是寫我自己的”[6],因而無論是小說的敘事者“我”、呂緯甫還是魏連殳身上都或多或少投射了魯迅的人生經歷和情感體驗,但對于同為自己“影子”的兩人,魯迅卻為他們設計了截然不同的結局,這兩個結局之間或許隱含著魯迅創作期間人生心態的轉變。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依靠母親的意志,得以敷敷衍衍地掙扎著活下去。魯迅的一生,作為長子、長孫、長兄,維系著整個大家庭的經濟與情感聯系,母親同樣是魯迅生命中至關重要的親人,正如他所刻畫的魏連殳,一邊說著家庭應該破壞,一邊領完薪水當即寄給祖母,魯迅也是處在傳統家庭倫理與現代思想啟蒙之間的知識分子,母親的愛是他生存的動力,卻也是他前進的羈絆。既然呂緯甫是魯迅投射自身的人物,那么呂緯甫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親人,應當也是支撐魯迅渡過第二次絕望的重要力量。而在《孤獨者》中,魯迅直接掐滅了這個精神支柱,讓魏連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魏連殳最后的死局也就是魯迅為自己預設的最壞結果。從《在酒樓上》到《孤獨者》,從呂緯甫的痛苦掙扎到魏連殳的悲壯自戕,實際上是魯迅從絕望到絕望后的徹底崩潰,魯迅在1924年寫給李秉中的信中說道:“我也常常想到自殺,也常想殺人,然而都不實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7] 這就印證了他在《彷徨》的創作階段遭遇了嚴重的生命意義危機,但就是在這樣完全被絕望籠罩的創作氛圍中,又仿佛有希望在“涅槃重生”。
《在酒樓上》的結尾寫道:“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見天色已是黃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織在密雪的純白而不定的羅網里。”[2]這里的“我”和呂緯甫是魯迅的一體兩面,雖然他們終究不是同路人,但呂緯甫的經歷還是刺痛了“我”,讓“我”產生了反思,也在失望之余更為迷茫,所以才會有眼前的世界都被籠罩在一張危險未知的網里的感觸。而在《孤獨者》中描寫“我”與魏連殳最終告別的情景時,卻是以一種輕松的筆調:“我快步走著,仿佛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沖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么掙扎著,久之,久之,終于掙扎出來了……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3]與魏連殳告別的那個夜晚,風雪消散,圓月當空,魯迅已經徹底將“我”與魏連殳拉遠,“我”不再沉湎于過去沉重的絕望和崩潰中,而是決心迎著月光大步前行。
如果說《在酒樓上》是一部老友重逢的懷舊之作,魯迅借呂緯甫的故事,寄托自己對未來的虛空和彷徨不安,那么在一年后的《孤獨者》中,這種虛空的絕望感被完全擊碎,魯迅以更為決絕的自我毀滅展現出“將要從舊我掙脫出去的瞬間姿態”[8],這是一種置之死境而后生的希望。至此我們可以看到,“戰士”魯迅依然堅定地走在前行的路上。
參考文獻
[1] 魯迅.吶喊·自序[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2] 魯迅.在酒樓上[M]//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3] 魯迅.孤獨者[M]//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4] 汪衛東.“夢魘”中的姊妹篇:《在酒樓上》與《孤獨者》[J].魯迅研究月刊,2012(6).
[5] 周遐壽.魯迅小說里的人物[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
[6] 胡風.魯迅先生[J].新文學史料,1993(1).
[7] 魯迅.書信·240924 致李秉中[M]//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8]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責任編輯? 余? ?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