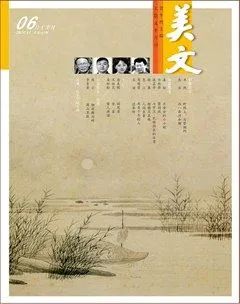我是個年輕人
周靖萱
我工作的地方只和王府井步行街隔了一條馬路,很近,但是我不常過去。最近的三年我們都發生了許多轉變,我不去是為了逃避一個在心里轉了幾萬遍的念頭——我是個年輕人,不過也沒什么意義。
第一次把眼前的景色對應上“天地”這個詞的時候,我十六歲。學校放暑假,住在川藏的某座山上,頭上是天,腳下是云,我想那時我是曾短暫擁有過天地的。能夠想象到的最綠的綠、最藍的藍、最黑的黑、最白的白……所有最純粹的顏色都是我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那是草、是蒼穹、是夜、是太陽……成群的牦牛瘋跑,有時我撫摸它們,有時我騎它們,有時我怕它們,有時我也享用它們,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你愛一樣生物與你殺掉它們仿佛沒什么沖突。我不謹記自己作為人的高尚。
我采花,將螢火蟲捉起來,在高海拔的地方我度過了冷冽的夏天,雪也會下,我帶著小喇嘛們邊躲雪邊講故事,喝用泥水煮出來的面湯,拿刺骨的雪水給他們洗衣服,跑到山腰上的小賣部買零食給他們吃。他們終日地纏著我,像普通的孩子們一樣,會趁著鏟雪的時候打雪仗,把泥巴偷偷藏進我的鞋子里。我有時候也被氣得拿鏟子揍他們,用不講新故事威脅他們,但是也有很溫馨的時刻。他們從樹下撿到了小鳥給我,我們一起拿煮不熟的米飯喂它。三四歲的小喇嘛長得漂亮極了,眼睛大大的,紅彤彤的小臉和嘴巴,很遠地看到我就跑著撲上來。我抱著他們,一個個吻便落到我臉上,我也不拿他們當佛,總是覺得承擔太多的膜拜對年幼的他們來說,還過于辛苦。
十八歲的時候身邊有了一群朋友,我不敬畏任何東西,勇氣和混賬在我心里同時滋長。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年少的人畏首畏尾,我們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人,只有青春在我們的眼睛里蕩漾。我可以去電影院看十幾次同樣的電影,徹夜不眠再睡過整個白天,凌晨三點我們到處找吃的,在便利店肆意掃蕩,在四點的大街上我們騎車,大聲地唱歌,撞見打群架的小團伙,邊吹口哨邊溜得飛快。柳樹的葉子掃過我的頭頂,我感到風在我臉上滑過,快樂像洪水一樣涌向我,我被它一下子沖走,大腦里空白一片,只記得一個詞,那是——自由……
我聽很多古怪的音樂,買一些用不上的小玩意兒,敷著深褐色的面膜去上課。什么理論我通通聽不進去,我只想到詩歌、舞蹈,想到話劇和夜場。我總在寫作,肚子里有說不完的話。女生宿舍成天吵架,但是也馬上和好,明明剛才還面紅耳赤的兩撥人,轉頭又可以坐在一個屋子里,吐槽渣男、嗑瓜子、哭哭、哄哄,找一個空教室放映《回家的誘惑》,跟著主題曲一起大唱特唱。那幾年我還常常喝多,清醒的時候很少,做很多丟臉的事兒。聽說我酒品差得很,還坐到同學家的健身單車上,聲稱要騎走。他們跑過來扶我,我又折騰,手里的煙一歪,燙了我一個疤,在胸口。事實上我不吸煙的,那種味道讓我聞著頭疼。
再回到家的時候,我將要二十歲了,在王府井的胡同里一家廣告公司做文案助理,寫的東西統統都不過。在某一次下雨的時候我坐在滿是白熾燈的格子間里,看著電腦發愣。我突然在想自己是否真的擁有才華?我對寫作產生了困惑,對于已經認知到的一切也同時不確定了起來。偶爾閑下來我總是埋進廚房,做飯、烘焙、腌泡菜、熬果醬……我急需一個結果來證明自己,來證明過去。我愛過的,怎么會沒有愛過我呢?與寫作一同拋棄我的,還有愛情。
即便我的臉青春猶在,性格也還算熱鬧有趣,可是我那時喜歡的人是不中意我的。我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人性本賤,總是對得不到的東西格外偏愛,所以才會喜歡上不喜歡我的人。只是慢慢的我才明白,我只是還不能接受,人生不能事事如意的真相。浪漫是我生命的主旋律,對于下班時偶爾會碰到的乞丐大叔,我心里都充滿了愉快,甚至會期待每天的見面,期待那一瞬間的微笑和點頭。我看不見他的狼狽,誤以為我們是在分享這個美好的未來。我下意識地不愿理解——我不理解他的卑微、他的無奈。我不愿去明白,我們之所以相遇是因為他必須乞求生存。
我還不到二十二歲,不過也快了,我仍想停留在原地。可是我一定要走。那么我就不走到那條街上去,一定會有源源不斷的年輕人是嗎?他們也會走到那些山上去嗎?會在楊柳依依的春天盛放?我還要繼續長大嗎?或者要走向老去了?是不是每一個問題的后面都會配有答案?我把剩余的,那些鮮活的心跳都換成了問號,希望有一天……希望有一天……
(責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