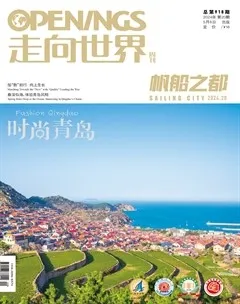青島:五四運動的緣起之地
陸安
五四因青島而起,青島因五四而榮。相比較于“帆船之都”和“影視之城”的專業化和局部性,“青春之島”以其廣博化和整體性,更能折射出青島的深刻內涵和獨特韻味。正是這4個形同珠璣的大字,托舉起了這座城市的根脈與魂魄。
五四運動激活了青春之島的根脈
站在2024年,回望歷史,不難發現,對于青島這座城市來說,最為重要的發展節點,既不是1891年6月14日那個建置的日子,也不是1897年11月14日那個淪陷的日子,更不是1922年12月10日那個回歸的日子,而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卻與青島休戚相關的日子。“五四”為中國賦能亦為青島賦能,一下子激活了這座年輕城市的根脈,從而導致了一個嶄新時代的大幕徐徐拉開了。
甲午戰爭之后,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瓜分第一幕,就是1897年11月14日清晨那永遠定格在了歷史上的場景:坐著德國遠東艦隊的3艘鐵甲戰艦,從上海吳淞口出發,由海軍中將棣德利指揮的720余名德軍官兵,在青島搶灘登陸,終結了1891年6月14日光緒皇帝一道圣諭所開啟的清王朝對這里的短暫而正規的統治,作為青島建置象征的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的總兵衙門易幟了!德國五色旗在凜冽寒風中肆意地升了起來,大清朝的黃龍旗降下,很快就在這片土地上失去了蹤影。但凡對中國近代史略有所知者,一定會記得謝纘泰所畫的那張充斥著“禽獸”的時事漫畫《時局圖》,青島作為德國殖民地,在上面有著恥辱的印記。
德國對青島長達17年的殖民統治,到1914年戛然而止了。通過日德青島之戰,日本一舉擊碎了德國“模范殖民地”的迷夢,從此,悲苦交加的青島,前門驅虎后門進狼,又落到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日本在青島設立守備軍司令部,取代了原來德國的膠澳總督府,成為這片土地的新主人。得寸進尺的日本,1915年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軟弱無能的北洋政府不斷妥協退讓,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先進知識分子走在了斗爭的前列,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標志著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方針,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由《青年雜志》演進而來的《新青年》也隨之遷到了北京,北大一躍而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搖籃。此時此刻,蔡元培在北大的眾多學生中,有兩位不起眼的山東人,這就是后來到青島大顯身手的楊振聲和趙太侔,為北大學風、五四精神傳承到青島埋下了伏筆。
在一個新舊更替的時代,共和取代了帝制,民國初年的政治舞臺上涌現出了一批思想新銳、遠見卓識的年輕精英,如力倡“以工代兵”、力主參加一戰的梁士詒,在巴黎和會上據理力爭捍衛國權的顧維鈞,無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前者,以14萬華工支援協約國的高昂代價,為中國贏得了戰后參加巴黎和會處置德國等同盟國的極其寶貴的“一張門票”,也為在華工之后赴法勤工儉學的周恩來、鄧小平、李慰農、郭隆真等接受馬克思主義、最終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鋪平了道路;后者,在“弱國無外交”的不利局面中為中國贏得了解決青島問題的機會,彰顯了“弱國有外交官”的豪邁氣質。值得一提的是,青島曾是一戰華工的出發地和歸來港,也曾經是赴法勤工儉學的李慰農和郭隆真開展革命活動、最后不幸被捕的地方,見證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使得已經在地下集聚、奔涌著的如巖漿一般熾烈的中國人民的怒火,終于破土而出!5月4日天門廣場上“還我青島”的時代吶喊,喚醒了眾多沉睡的國民,也喚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風暴眼中的青島,卻是另一番景象。表面的寧靜之下,涌動著反抗的怒火。此時的青島,處在日本占領軍的刺刀淫威之下。“五四”風雷,波及到了這里。據上海的《申報》報道,青島明德中學的校園內出現了反日標語,令日本守備軍大為光火,查封了這所學校,驅逐了校長王守清。
五四運動熔鑄了光耀百年的魂魄
正是在風起云涌的反抗怒潮之下,北洋政府最終沒敢在巴黎和會的不平等的和約上簽字,這就為1922年華盛頓會議期間青島問題的解決創造了條件。1922年12月10日,青島回歸,一掃25年德日殖民統治之恥。此前一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此后一年,中共青島誕生。歷史將永遠銘記,1923年8月,那個炎熱的夏天,中共青島組在海岸路18號成立了,鄧恩銘任書記。青島,遂成為最早建立中共地方黨組織的城市之一。出席過中共一大的鄧恩銘和王盡美,為青島黨組織的成立和早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25年8月19日,留下了遺囑,“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27歲的王盡美在青島病院與世長辭;1931年4月5日,留下了詩篇,“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30歲的鄧恩銘在濟南緯八路侯家大院刑場英勇就義。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中,無數革命先烈在這里拋灑青春、熱血乃至生命,第一個在青島犧牲的共產黨員就是曾經赴法勤工儉學的李慰農。1925年7月29日,在團島刑場,李慰農犧牲在反動軍閥的屠刀之下,時任中共四方支部書記,時年30歲。他犧牲的噩耗傳到上海時,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執委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提議暫停會議,為烈士致哀。時光流轉,多年之后,1992年青島出版紀念烈士的專輯,鄧小平同志親自題寫了“李慰農烈士專集”7個遒勁的大字。與周恩來、鄧穎超等一道參加過五四運動、覺悟社的重要成員、赴法勤工儉學的女中豪杰郭隆真,在青島領導工人運動,不幸被捕,留下了八字遺言,“寧可犧牲,絕不屈節”,最后與鄧恩銘等共產黨員同時就義,時年37歲。那是一個年紀人可以干大事業、做大貢獻的時代,也是一個年紀輕輕的人可以拋灑熱血、犧牲生命的時代。熱血奔涌,激情燃燒,為國為民,前赴后繼,正是那一代先賢群英的生動寫照。“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據統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青島有14位市級黨組織主要負責人英勇犧牲,有名可考的烈士約1.37萬名。
在弦歌不輟的新文化運動中,青島的街頭,留下過多少“五四”先輩的足跡,傳誦過多少蕩氣回腸的佳話。楊振聲1930年出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趙太侔1932年出任國立山東大學校長。大學路上,大師的身影絡繹不絕。《避暑錄話》,誕生在1935年的青島,凝聚了一批文人墨客。一所大學,一份報刊,大師成群結隊地來,行走在這座城市彎彎曲曲的石徑小路上,也行走在了人們永不消失的記憶之中,令人們不禁遙想到“五四”新文化啟蒙和傳播的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一向被不明就里的人們藐視為“文化荒漠”的這座城市,從此有了厚重多元且綿延不絕的文化傳承。
在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核心的偉大“五四”精神感召之下,在跌宕起伏的中國百年革命征程中,青島始終沒有缺席,是參與者、見證者、實踐者,作為“五四”的緣起之地,作出了自己獨有的貢獻,書寫了輝煌的華章。
1949年,青島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催生出了這座城市更加亮麗的容顏。作為五四運動的緣起之地,青島始終沐浴在“五四”的榮光之下。正是薪火相傳的“五四”精神,讓這片沃土熠熠生輝,躍動著永不衰竭的生機與活力,從而無愧于“青春之島”的美譽。
Qingdao: The Birthpla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s a significant under tak ing in Qingdaos urban developmen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symphony of the“Easter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the “May Wind” sculpture and the May Four th Square have been among the citys proudest landmarks since their official completion in 1997. With the fiery color, soaring style, and progressive spirit, they epitomize the essence of this “Island of Youth”. A sculpture, a square, a city, and a historical period converge remarkably, representing a precious amalga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