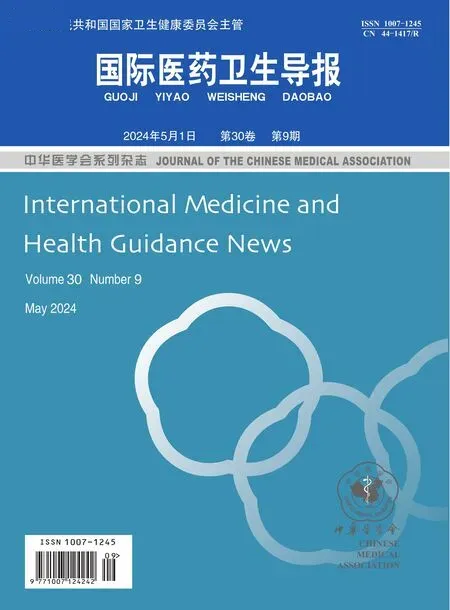首發表現為肝衰竭的Wilson病1例并文獻復習
鄭亞楠 丁國鋒 劉賢賢
1濱州醫學院第一臨床醫學院,濱州 256600;2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感染性疾病科,濱州 256600
Wilson病(Wilson’s disease,WD)又稱肝豆狀核變性,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本病在世界范圍內不同人群的患病率為1/30 000~1/2 600,但我國尚缺乏相關統計數據。WD可以在任何年齡起病,但多發生于5~35歲,也有80歲才出現癥狀的患者[1]。WD患者臨床表現多種多樣,缺乏特異性,同時基層醫生對該病缺乏認識,導致漏診和誤診率高。肝臟是其最常累及的器官之一,以肝衰竭為首發表現的患者少見,早期診斷困難,病死率高。WD為目前少數可治療的遺傳疾病之一,患者如能在發病早期或癥狀前期即被確診并得到及時治療,大多預后良好[2]。維持治療過程中醫生要密切關注患者用藥依從性及藥物不良反應。現報道以肝衰竭為首發癥狀且對青霉胺不耐受的WD患者1例并進行文獻復習。
病例資料
患者,女,15歲,學生,因“發現皮膚鞏膜黃染2 d,發熱1 d”于2019年5月14日入住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感染科。患者入院前2 d無明顯誘因下出現皮膚黏膜及鞏膜黃染,次日出現發熱,最高體溫37.8 ℃,伴頭暈、腹脹,自行服用“布洛芬”后體溫可降至正常,數小時后再次出現體溫升高。檢查血常規示: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絕對值升高,輕度貧血,肝功能及凝血功能異常。既往有“雙黃連”藥物過敏史,個人、家族史無特殊。
入院后查體:體溫38.2 ℃,脈搏90次/min,呼吸22次/min,血壓142/65 mmHg(1 mmHg=0.133 kPa);急性發熱面容,貧血貌,皮膚及鞏膜重度黃染,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心肺查體無異常;腹軟,劍突下壓痛,無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觸及。血常規+網織紅細胞:白細胞計數11.0×109/L(4.0×109/L~10.0×109/L)(括號中均為正常值參考范圍),紅細胞計數2.7×1012/L(3.5×1012/L~5.5×1012/L),血紅蛋白81 g/L(110~160 g/L),血小板計數178×109/L(100×109/L~300×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81.5%(50.0%~70.0%),中性粒細胞絕對值8.9×109/L(4.0×109/L~10.0×109/L),網織紅細胞百分比6.8%(0.5%~1.5%)。凝血指標:凝血酶原時間22.6 s(9.0~14.0 s),國際標準化比值2.05(0.80~1.20),凝血酶原活動度36%(70%~140%),活化部分促凝血酶原激酶時間37.9 s(26.0~42.0 s),纖維蛋白原含量1.5 g/L(2.0~4.0 g/L)。血生化:丙氨酸氨基轉移酶160.2 U/L(7.0~40.0 U/L),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276.7 U/L(13.0~35.0 U/L),白蛋白32.8 g/L(40.0~55.0 g/L),總膽紅素165.6 μmol/L(5.0~23.0 μmol/L),直接膽紅素80.3 μmol/L(0~4.0 μmol/L),間接膽紅素85.3 μmol/L(0~13.0 μmol/L)。C反應蛋白9.8 mg/L(0~6.0 mg/L),降鈣素原1.16 μg/L(0~0.25 μg/L)。入院診斷:急性肝衰竭、感染性發熱。給予抗感染、改善凝血功能、保肝退黃等對癥治療。3 d后患者病情加重,膽紅素進行性升高,血紅蛋白及凝血酶原活動度急劇下降,轉重癥醫學科給予血漿置換等治療。查找肝衰竭原因,完善Coombs試驗,結果為陰性,EB病毒抗體、巨細胞病毒抗體(CMV-IgM)、EBV-DNA定量、抗核抗體、自身免疫性肝炎抗體譜、免疫球蛋白(Ig)G4、布氏桿菌抗體均陰性,但血清銅藍蛋白0.067 g/L(0.200~0.600 g/L)明顯降低,上腹部MRI增強掃描結果提示肝硬化(肝內彌漫性再生結節形成);眼科會診檢查眼底示:雙眼角膜上方及下方角膜緣可見K-F環。綜上考慮患者為WD,進一步行ATP7B基因突變檢測,結果:13號染色體外顯子區域1個雜合子突變c.4114C>T(p.Gln1372),同時檢測其父母,均為雜合攜帶。立即給予低銅飲食,靜脈輸注二巰丙磺酸鈉及保肝退黃等對癥治療。治療15 d后復查肝功及凝血指標較前明顯好轉,于2021年5月31日出院。出院診斷:慢加急性肝衰竭、感染性發熱、肝豆狀核變性、急性溶血性貧血。囑長期口服青霉胺治療。
患者院外堅持口服青霉胺治療。隨訪4個月,患者肝功能及凝血指標逐步好轉,但血小板計數進行性下降,最低至26×109/L,遂于2021年9月14日再次住院。完善檢查排除原發疾病的進展,考慮青霉胺可導致骨髓抑制,明確血小板下降的原因是青霉胺的不良反應,將青霉胺減量至250 mg tid,3 d后復查血小板計數下降至13×109/L,停用青霉胺,藥物調整為二巰丁二酸0.25 g bid。門診隨訪2個月后患者血小板計數升至124×109/L,恢復正常。目前,患者堅持口服二巰丁二酸,定期門診復查,肝腎功能及血常規正常。
討論
WD是由于位于常染色體13q14.3的腺嘌呤核苷三磷酸7b(ATP7b)基因突變導致的銅代謝障礙性疾[3],過量銅沉積于肝細胞中造成肝細胞壞死和纖維組織增生,肝細胞大量壞死釋放出銅會誘發溶血,游離銅也會逐漸在腦、腎、角膜等沉積[4],出現以錐體外系癥狀、肝臟損害、腎功能損害、角膜K-F環等為特征的臨床表現。成人WD患者大多以神經系統損害為首發癥狀[5]。本病呈緩慢進展性,兒童及青少年期發病多見。5~10歲時,肝蓄積銅的能力逐漸飽和,游離銅釋放入血,對紅細胞產生毒性作用,表現為急性溶血性貧血,少數WD患者雖肝內銅蓄積已達飽和,但銅向血液轉移困難,從而進入肝細胞內溶酶體,造成肝細胞大量壞死,臨床表現為急、慢性肝衰竭[2],且常不典型、進展快、預后差。
本例患者的臨床特點:⑴既往無臨床癥狀,父母體健,無肝病家族史;⑵起病相對較晚,因感染誘發急性肝衰竭入院,查體可見角膜K-F環;⑶血清銅藍蛋白水平下降,結合基因學檢測結果,根據《中國肝豆狀核變性的診治指南2021》診斷標準,該患者WD診斷明確。該病在國內誤診率50%左右[6]。造成誤診的原因如下。⑴WD為罕見遺傳代謝性疾病[7],在全球范圍內患病率為1/30 000~1/2 600[1]。⑵臨床表現多樣:10%~25%的患者出現精神癥狀,30%~40%的患者出現神經癥狀,40%~50%的患者出現肝臟癥狀,尤其是神經精神癥狀患者首診科室常為神經內科[8-9]。⑶青年醫師查體不細致:入院查體時未發現該患者有特征性角膜K-F環,導致延誤診斷。⑷多數醫師對該病認識不足:臨床發現輕度肝功能異常患者后未對其進一步明確病因。⑸多數醫院尤其是基層醫院未開展血清銅藍蛋白檢測。對于不明原因肝功能異常或急性肝衰竭的年輕患者,臨床醫生應認真詢問病史,詳細查體,排除常見病因后及時檢測血清銅藍蛋白水平,必要時行基因檢測,避免誤診。
WD的治療是通過驅銅及阻止銅吸收來糾正銅失衡。堅持終身維持治療是預防癥狀復發或疾病進展的必要條件[1]。高達25%的患者不能堅持藥物治療。中斷藥物治療可能會導致癥狀復發,導致不可逆的肝損傷,最終需要肝移植治療[10]。WD藥物根據藥理作用可分為兩類:一是促進銅排出的藥,如D-青霉胺、二巰丁二酸等;二是降低銅離子吸收的藥,如鋅制劑等[1]。D-青霉胺為最常用的驅銅藥物。研究顯示,D-青霉胺治療肝臟損害WD患者效果顯著,患者肝功能在治療2~6個月后會有不同程度改善[11]。青霉素皮試陰性才可服用D-青霉胺。一般用24 h尿酮作為減量或間歇用藥的指標。D-青霉胺早期不良反應包括發燒、中性粒細胞減少和皮膚出疹,晚期反應包括腎毒性和骨髓毒性[1]。據統計,高達30%的D-青霉胺治療患者因不耐受而停藥[12-13]。如果患者對D-青霉胺過敏或不耐受,可與二巰丁二酸膠囊交替服用,或用二巰丁二酸膠囊代替D-青霉胺長期口服維持治療,從而減輕D-青霉胺的不良反應及長期用藥后藥效衰減作用[1]。鋅制劑通過誘導腸細胞金屬硫蛋白的產生來干擾腸道對銅的吸收。金屬硫蛋白是一種內源性螯合劑,優先結合腸細胞中的銅并阻止其吸收[14]。
本例患者經青霉胺治療后好轉出院,在肝功能、凝血功能穩定狀態下,復查結果血小板計數進行性下降,考慮不除外青霉胺不良反應,給予停藥并調整為二巰丁二酸膠囊后,患者血小板計數恢復正常,病情穩定[15]。終生堅持使用螯合劑或鋅劑進行維持治療對預防復發至關重要。
WD具有異質性表現,早期診斷并及時治療以恢復銅平衡是關鍵[16]。同時,基層醫師應提高對該病的認知水平。如果患者在發病后未及時治療,一般病程不超過5年,其中以急性肝衰竭起病的WD患者發病至死亡病程在1~3個月[2]。筆者查閱文獻發現,目前,對于螯合劑治療WD患者的最佳選擇尚無專家共識。對于青霉素皮試陰性的患者,仍需密切監測青霉胺的不良反應,定期監測患者血常規及生化指標,確保用藥依從性及長期隨訪。通過早期診斷和維持治療,部分患者也可以擁有正常預期壽命和生活質量[17]。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鄭亞楠:文獻檢索,論文撰寫;丁國鋒:文章的構思與設計;劉賢賢:病例資料收集與整理,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