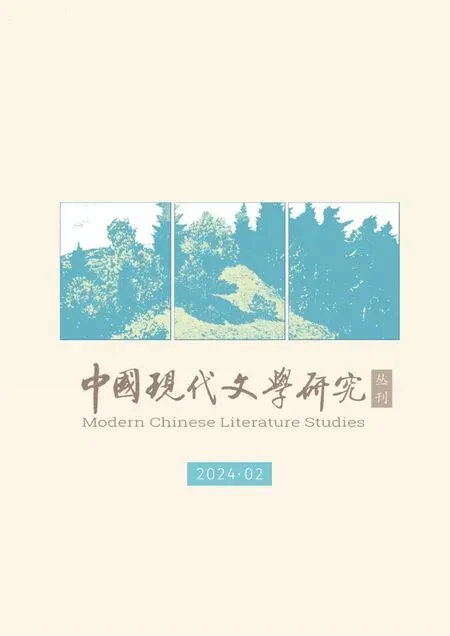“雜文的畫框”
——《雜文的自覺》與魯迅的文學本體論問題
王 欽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關于魯迅雜文的研究從來都是一個誘人而艱難,同時又不可忽視的工作:由于雜文之“雜”,使得它幾乎很難在形式和內容上得到清晰穩定的概念規定,以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研究者即便有意識地從審美自律性的角度接近雜文,最終也往往會從一個名為“政治性”的出口徘徊而出。本文通過考察張旭東在《雜文的自覺》中對于魯迅雜文作出的文學本體論層面的分析,探討了雜文在魯迅的寫作實踐中同時具有的內部和外部的推動力,以及“雜文的自覺”對于其他文類和風格的影響力;與此同時,通過聚焦“雜文的畫框”的概念,本文也探討了張旭東的這種嘗試所透露的一個棘手的困境。
眾所周知,在國內外迄今為止汗牛充棟的魯迅研究中,關于魯迅雜文的研究從來都是一個誘人而艱難,同時又不可忽視的部分:一方面,相比于魯迅留給世人的所謂“純文學”創作(小說、詩歌、散文、散文詩等),雜文無論是數量上還是其在魯迅本人的文學實踐中占據的重要性,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首要性;另一方面,恰恰由于雜文之“雜”,使得它幾乎很難在形式和內容上得到清晰穩定的概念規定,以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研究者們即便有意識地從審美自律性的角度接近雜文,最終也往往會從一個名為“政治性”的出口徘徊而出——無論是主張魯迅雜文實踐在針砭時弊,作為“投槍”“匕首”而帶有敏感性和急迫性的意義上具備了一般的文學創作所沒有的速度、強度和銳度,還是透過魯迅雜文而探討作者與(例如)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態度和政治立場之間的關系,對于雜文的研究似乎都無法停留在雜文劃出的文學空間內(假設這樣一個空間的確存在的話),而不得不走到它的上方、下方或外部。
盡管如此,近年來從各種角度重新探討魯迅雜文的研究并不少見,而在這些研究中,張旭東的巨著《雜文的自覺: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1924—1927)》在至少三種意義上是最獨特的:第一,這本逾八百頁的著作僅僅是作者計劃中的魯迅雜文研究“三部曲”的第一部,從時間跨度上說,僅僅涵蓋了1924年至1927年的寫作。換句話說,如果要完整而正確地對待張旭東的魯迅研究,我們就必須等待剩下的兩部著作出版,否則無法恰當理解作者所謂魯迅雜文從“自覺”到“自由”的發展過程。在最直接和直觀的呈現方式上,這一龐大的研究計劃的事實本身,已經使得《雜文的自覺》在迄今為止針對魯迅雜文的研究中顯得格外矚目。
然而,第二,在這本巨著中,張旭東對于所謂“既有研究”的涉及和討論,嚴格來說僅僅限于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和日本思想家竹內好的《魯迅》。與之相對,作者對于一系列似乎與魯迅沒有關系的理論家和哲學家的引用——包括但不限于黑格爾、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施米特(Carl Schmitt)、德勒茲(Gilles Deleuze)、奧爾巴赫(Eric Auerbach)等——則幾乎俯拾皆是。雖然張旭東始終以一種相對低調或謹慎的行文方式將他論述中對于這些理論家和哲學家的援引和討論限定在“啟發”、“參照”、“類比”或“轉喻”的范圍內,我們仍然很容易設想研究者很可能會將這些論述作為“隨意的聯想”而予以打發——然而,難道我們早已清楚知道什么是“理論”、什么“哲學”、什么是“文學”,清楚知道這些不同領域(抑或是概念?文類?范疇?名稱?事物?)的嚴格邊界,難道我們早已潛在地為魯迅的雜文圈好一塊領地乃至學科邊界,盡管我們對此佯裝一無所知?難道我們已經確信自己能評判對于哪些文本的援引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即便我們試圖討論的對象本身——雜文——據說總是不斷逾越各種邊界(文類的、形式的、政治的、社會規范的、法律的)?嚴格來說,這種可能的質疑和批評,其“隨意性”并不會比《雜文的自覺》中的這些聯想更少,而往往只會更多。
不過,還是讓我們回到既有的魯迅研究在《雜文的自覺》中近乎完全缺席的問題上。在此,哪怕作者出于整體布局的考慮而決定把對于既有研究的梳理安排在尚未出版的兩卷中,作者的這一決定也至少稱得上驚人;因為,不夸張地說,僅僅就關于魯迅雜文的既有研究作出哪怕是掛一漏萬的回顧和整理,就不難發現,無論是針對文類意義上的雜文本身的研究,還是針對具體篇目的研究,值得討論和分析的既有研究都不在少數。而我們如果僅僅停留在學科意義上的“寫作規范”的角度,那么甚至可以說,張旭東對于既有研究的這種態度,在很多研究者那里幾乎是無法接受的,甚至是傲慢的。然而,在斷定作者“傲慢”之前(或許沒有比這更容易的態度了),我們不妨問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問題:為什么如此“傲慢”的作者,偏偏選擇了李長之和竹內好作為詳細討論的對象?或者說,在斷定作者“傲慢”之前,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為什么作者偏要采取這樣一種貌似極端的論述策略,甚至不裝模作樣地給大量的既有研究一點表面的奉承(paying lip service)——眾所周知,這種裝模作樣同時有一個冠冕堂皇的術語,即“學術規范”?
因為在張旭東看來,恰恰是李長之和竹內好在所謂“文學本體論”的意義上試圖接近和把握魯迅的文學寫作,尤其是雜文寫作或作為寫作的雜文。在筆者看來,這也正是使得《雜文的自覺》不同于迄今為止的其他研究的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張旭東試圖以一種非本質化的“文學本體論”為基點,描畫魯迅那里的“雜文發生學”,為雜文如何在魯迅那里成為“文學本身”作出詳盡的分析。在張旭東向我們展示的基本圖景中,經歷了1923年一整年的“沉默”之后,魯迅的文學創作在“始于《華蓋集》而收束于《而已集》的過程中”經歷了“第二次誕生”,“一種‘雜文的自覺’應運而生”,1張旭東:《雜文的自覺: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1924—192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444頁。下文引自此書處皆隨文標注頁碼,不另作注。而這種“雜文的自覺”將進一步在魯迅最后的“上海時期”發展成熟為“雜文的自由”。
聚焦于“自覺”時期的《雜文的自覺》,基本上為魯迅的雜文寫作作出了如下勾勒:雜文從來不是一種確定的文類,甚至不是魯迅有意識地挑選的一種特定的寫作方式或手段;毋寧說,在雜文走向自覺的過程中——張旭東明確了本書標題的英文表述:“the becoming self-conscious of Zawen”(第147頁),也即魯迅對于雜文的寫作自覺和雜文本身的走向自覺——魯迅文學憑借雜文而成為和實現它自己,通過雜文而在文學空間中為自己找到了一個艱難的位置,同時也將“文學”的邊界(無論是傳統文學還是同時代的現實主義乃至現代主義文學)推進到它的極限處。如張旭東在書中反復指出的那樣,與其說是魯迅找到了雜文,不如說是雜文找到了魯迅:正是在魯迅與周圍情境的對峙中,在同時具備身體性(乃至生理性)和精神性的搏斗、抵抗、反擊、掙扎、“橫站”的緊張關系中,雜文越發明確地找到自身的形式和表述,成為“魯迅文學的基本原理、原則、法則和方法”(第19頁)。“雜文的自覺”,意味著雜文在魯迅身上的降臨和發生(s’arrive)。
然而,目前上述論述仍然十分抽象。在接下去的篇幅中,筆者想簡單勾勒張旭東的論述要點,并提示這樣一種分析進路在何種意義上為我們重新理解雜文的美學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參照,同時又呈現了何種困境。
張旭東開宗明義地指出,對于魯迅雜文的閱讀,乃至對于魯迅文學作品的整體閱讀,都不能以魯迅的“觀念立場”為“入口”或“出口”:“魯迅贊同還是反對進化論、對辛亥革命的寄托與失望、是否信奉馬克思主義或服從共產黨文藝路線的組織領導……這些問題本身并不能導向對魯迅文學更深入細致的理解。”(第13頁)相反,推動魯迅進行寫作的根本力量不是某種思想觀念或政治立場,而是一種同時包含對于外部的抵抗和內部的掙扎的力量,雜文便是對于這種力量在文學空間的總命名。例如,張旭東寫道:
魯迅本人的觀念、思想、立場都可以受到外部環境和思想氛圍的影響,但魯迅文學的政治性卻從來無關于外部強力或暗示,而是內生于作者存在、生存、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狀態;它來自那種沉默、抵抗、呼吸、掙扎和希望的動作本身,它也來自魯迅文學在其孤獨的“單子”結構中吸收、凝聚和再現的集體性,即那種民族的、家國的社會性抗爭和文學內部的寓言斗爭。(第27頁)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十分緊湊的文字表明,魯迅一方面通過雜文而回應和抵抗來自外部的壓力,這種抵抗近乎于一種內生的、生物性本能,因而完全是個體性的、私人性的、內在的;另一方面,這種以雜文形式呈現的對于外部的回應和抵抗,又以共振或共鳴的方式寓言地呼應和呼喚著一種集體性或人民性,它并不“代表”某個集體或階層甚或民眾而發言,并不是某個特定政治立場或黨派的“傳聲筒”,而是在最個人的層面甚至在取消“個體性表達”的層面上(我們記得魯迅《野草·題辭》中的那句名言:“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吸收、凝聚和再現”某種集體性:
這種言語方式和文學風格似乎相信,無論自己下筆多么刻薄和不留情面、多么挑戰讀者的審美或道德“舒適區”限度、如何制造對立和決裂,但歸根結底,這種話語方式表達的是作者本人所認同并為之服務的共同體內部的道德良知、情感真實和思想共識;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集體經驗和理想的自我表述。(第79頁)
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雜文在文學本體論的層面上取消了內部與外部、個人與集體、公共與私人,甚至政治與非政治之間的種種對立,通過“寫作”這一獨特的、個體性的、孤獨的行為而為銘刻、表現、翻譯、轉化、介入現實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同時也為新的集體性的自我表達提供了可能。張旭東甚至指出,“寫作”這種通過個體性而表達或呼喚集體性的特殊動作或行為,根本上訴諸了“晚清以來正直、進步、向上的中國人的最大公約數”,而“這個文學公約數在價值共同體意義上,與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歷時性變化所構成的共時性結構及其傾向性大體重合”(第80頁)。
在此,我們很容易想到一個質疑的聲音:這些頗為激進的、幾乎要將魯迅文學在道德、審美、政治的意義上“絕對化”的論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魯迅在《華蓋集》《華蓋集續篇》《而已集》等雜文集中針對當時的各種社會問題、針對自己卷入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筆墨官司”,乃至針對某一天看到的新聞或現象所作出的那些直接而迅速的反應?換句話說,當我們像張旭東那樣仔細地辨別、分析和推敲雜文在文學本體論層面上的可能性條件——順帶一提,《雜文的自覺》中對于魯迅單篇雜文(以及散文、詩歌和小說)作出的文本細讀,其中的洞見和啟發性絕不亞于任何迄今為止關于這些篇目的既有研究——我們是否落入了一個幾乎不可避免的悖論或困境,即我們閱讀的時間、節奏和速度,必然不同于魯迅寫作的時間、節奏和速度,也不同于這些雜文在歷史的情境下發揮其現實“效力”的時間、節奏和速度?對此,張旭東的回答是:并不盡然。此話怎講?
讓我們以張旭東分析《華蓋集》時的一段話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當談到魯迅如何因為“女師大學潮”事件而卷入與陳西瀅等人的論戰時,張旭東寫道:
“擠”的外部性被轉化為“擠”的內部性和生產性;或者說“擠”由一種被動狀態轉入一種主動狀態,由從外向內的逼迫和壓抑轉化為從內向外的創造與表達。(第479頁)
與之相應,《雜文的自覺》中還有其他類似的表述:
魯迅雜文的內在驅動力和形式-風格造型動力,一方面來自對于外部敵意環境的“擠”、“討伐”與“壓迫”的反抗和反制,另一方面則來自一種自覺而自信的再現或反映沖動和使命感。(第83頁)
寫作對于魯迅來講既是為生存、為生命、為生活、為希望、為明天的那種反抗窒息、反抗沉寂和反抗虛無的生死搏斗,同時,它又是一種存在的詩,即把存在及其斗爭情緒化、感官化、具體化和形式化的審美狀態、游戲狀態、回憶的沉思狀態,特別是那種在他最憤怒、最“尖刻”的文字里也會隨時出沒的雋永和靜謐。(第296頁)
魯迅雜文固然是渴望行動并且在行動的當下性、政治性和存在的冒險狀態中存在的,但這種存在同時是,甚至在批評的概念上首先是詩學和語言范疇的存在;換句話說,它是一種在“言”中把言語行為同時否定和保留下來的象征活動。(第308頁)
上述引用遠不是窮盡式的。在這些段落中,張旭東凝練地概括了雜文(=“寫作”)在文學本體論意義上對于魯迅的文學創作所發揮的雙重推動力:一方面,“擠”“壓迫”等語詞表明,促使魯迅進行寫作的直接動因正是來自外部——環境的外部和對于文學而言的一切“外部”——的偶然刺激和挑戰,因而雜文作為回應,足以成為“投槍”和“匕首”;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將自己定型和確立在文學空間內部的努力,雜文并不會隨著外部刺激的消失而消失,反而會形成自身的自律性和穩定性,獲得一種只屬于自身的節奏。在既無限貼近現實與當下、同時又與之保持審美和反思距離的意義上,雜文的時間、節奏和速度同時由它的“外部”和“內部”所決定。
雜文所具備的這種不可思議的自律性和他律性,這種與具體歷史狀況之間的切近和距離,征候性地體現在上面引用的幾段論述中:一方面,雜文“同時”是存在的政治和存在的詩;另一方面,與此同時,雜文也是一種“轉化”,即一種將被動狀態(掙扎和抵抗)轉化為主動狀態(寫作)、將外部轉化為內部的獨特媒介。如果雜文是一種“同時”的、沒有時間間隔的“轉化”,那么這也意味著,在雜文對于外部進行銘刻、表現和回應的每一個時刻,并不存在一個(例如)抵御和儲存外界刺激的意識或形式機制,來讓“外部”得以通過某種方式“進入”文學空間,即不存在如何通過某種文學手法或風格表達或再現現實的問題。
雜文既是外部與內部,同時也是外部向內部的“轉換”——這一奇特的文學本體論描述,在張旭東的論述中被貼切地類比為“表面物理”:
雜文的審美構造是一種“表面物理”(surface physics)結構:它沒有通常意義的“深度”,因為在雜文風格空間里,審美與政治、符號與其意義闡釋、意識與潛意識、“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并不存在常規形態的“現象”與“本質”、“形式”與“內容”的互釋關系,而是同時裸露為兩個表面,一個表面由政治本體論“存在的斗爭”的直接性及其強度即“碰”的表面組成;另一個作為語言感性外觀,作為“存在的詩”直接存在于雜文文本(形象、句式、話語、風格)之中……這兩個表面之間不存在通常意義上的表/里關系,而只有表/表關系……這種表/表關系是對傳統或常規“內容與形式”思維的顛覆,因為雜文的內容就是雜文的形式,反之亦然。(第499頁)
需要注意的是,語言感性外觀的層面和“存在的斗爭”的層面在“雜文的審美構造”中并不構成某種辯證綜合;毋寧說,這兩個原本分別代表“外部”和“內部”的層面,通過雜文并在雜文中被同時“轉化”為雜文所標記出的文學空間“內部”的兩個“表面”——用張旭東的話來說,這便是“魯迅雜文的政治本體論同其審美感性外觀之間的可互換性甚至等價性”(第500頁)。重復一遍:兩者之所以可以獲得某種“等價性”,不是因為雜文以某種特定的形式裝置或審美機制、通過特定的風格或文體,為赤裸裸的、感覺材料一般的“外部”賦予了一定的“文學形式”——我們記得,雜文對于外部刺激的回應和它對于外部的轉化是同時發生的——而是因為雜文近乎“無中生有”地讓外部事件及其包含的情緒、傾向、立場等都如其所是一般定型在文字表達的層面上。反過來說,構成雜文的文學本體論和審美“核心”的這種“空無”或“虛無”,并不是什么具有深刻道德、政治、思想含義的“無”(與竹內好在《魯迅》中的論述相反),而不外乎就是寫作者在生活和生命的意義上因外部因素的刺激而引發的一種身體性動作,只不過這種動作得以借助文字而穩固下來(比較第484頁)。我們必須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張旭東的下面這段論述:
魯迅文學在文體、寫作方法和風格上的形式意義和審美價值,本身是由它們為之服務的政治性的存在斗爭的自覺程度和有效性所決定的。只有在后一種意義上,方能夠談論魯迅文學的形式自由。……恰恰是由“活下去”的生物意志和政治意志(“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決定的、沿著生命自己為自己開辟的道路前進的“更高”選擇。(第89頁)
或許容易引起誤解的是,這段話中所謂“政治性的斗爭的自覺程度和有效性”對于魯迅文學(因而也包括雜文,甚至就是雜文)的“決定”,并不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規定;不然的話,作者不過是以更為精致的措辭重復了文學的環境決定論乃至鏡式反映論的陳詞濫調罷了。恰恰相反,這里的“決定”意味著雜文的文學空間正是通過與“外部”的遭遇、作為對于“外部”的回應才能自我形成。但這一過程絲毫不帶有神秘色彩,因為如引文后半部分所示,雜文對于“外部”的文字定型無非是最根本也最基本的“生物意志和政治意志”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表達,甚至可以說,它是生命自我持存的本能坐落在文學空間中的具體形式。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依照傳統的文體分類而將魯迅的創作生涯描述為從“純文學”創作逐步向雜文寫作過渡,那么這一過渡所反映的決不是魯迅在寫作方法或風格樣式上的選擇或調整,而毋寧說是“雜文的自覺”逐漸走向前臺、“存在的政治”和“存在的詩”在雜文這種特殊的文學-審美構造中如其所是地、互相并置一般地穩定下來的過程。因此,張旭東明確主張說,我們能夠在《華蓋集》等雜文集中找到的表述上的風格和審美要素,事實上都可以在魯迅前期創作的小說乃至論文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對應:
所謂“雜文的自覺”和魯迅文學的“第二次誕生”,并不是對此前魯迅文學生涯的否定或扭轉,不是道路和手法上的改弦更張,而是魯迅到目前為止一切經驗、能量和思考的總體性的激化,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總動員性質的集結、凝聚和結晶,它帶來的是一種更大的文學密度和文學強度。(第535頁)
因此可以說,哪怕沒有抵達其“自覺”的程度,雜文作為文學本體論意義上的根本基礎(一種無基礎的基礎),作為生命對于外部刺激的回應和自我維持、自我主張、自我表達,自始至終都存在于魯迅的寫作實踐之中。在此,非常有啟發性的是張旭東對于魯迅創作于1925年的著名小說《傷逝》的分析。在迄今為止關于這篇小說作出的連篇累牘的解讀中,幾乎尚沒有研究者質疑過這個文本的文類——似乎它確確實實就是一篇小說。然而,在張旭東看來,誕生于“雜文的自覺”時期的《傷逝》恰恰包含著雜文和“小說”之間的張力——具體表現為主人公涓生的一系列具備雜文性質的內心獨白和整個故事發展呈現的“愛情”情節劇之間的張力——而這個憑借小說的形式最終無法承載這種張力的文本,使得《傷逝》寓言性地成為魯迅文學中“小說”的某種終結。例如,張旭東寫道:
雜文內容的語言歸根結底由社會存在的無情邏輯所決定,這種無情邏輯反映在求生欲望、唯意志論和理性選擇這樣的主觀領域,構成雜文《傷逝》的強勢內容。與此相對,小說《傷逝》占有的則是一種弱勢內容,它要么落實于關于社會現實條件的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描摹,要么變成一出關于“愛與死”的情節劇;但無論它作為悲劇還是喜劇出現,抑或在“風俗研究”意義上提供某種社會學的認識和分析,事實上都會縮減為一個缺乏新意、缺乏藝術獨創性,同時也缺乏思想力量的故事。(第394頁)
沿著上文已經涉及的論述脈絡,可以說,之所以《傷逝》的小說形式無法承載雜文在語詞、句法、句子、修辭等層面帶來的張力,正是因為無論是現實主義小說還是現代主義小說,它們在接收和處理外部現實的時候,都不得不訴諸一定的規范、原則和邊界,而正是后者使得這些小說形式得以在概念上穩定為文類——在最低限度上,小說不得不進行敘事(哪怕是現代主義的“反敘事”),不得不具備一定的情節、故事、人物等要素;而這些負擔在雜文寫作中不再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是為什么張旭東能夠屢次將雜文類比為本雅明論述中的“翻譯”)。例如,張旭東寫道:
對雜文的認識并不首先在于雜文作品提供給讀者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它們自身的外表、形式、風格和內部結構;換句話說,雜文的文學肌體和審美強度,本身以它們的特殊形態保有并傳遞著更多的信息。(第469頁)
在筆者看來,這段看似簡潔的論述透露了一個對于理解全書而言至關重要的信息:不是雜文文本的內容,而是它的“外表、形式、風格和內部結構”、它的“特殊形態”,似乎為我們辨識雜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外觀標記。這一判斷也同樣符合我們對于魯迅的雜文寫作的基本認識:似乎我們的確是通過某些非常具有“魯迅特征”或“魯迅范兒”的措辭、修辭、句式而辨認和接近魯迅的雜文。無論是在論述《傷逝》時,還是在討論 雜文寫作在形式上與其他文類的區別時,張旭東似乎確實重述了一般讀者具有的這種閱讀感覺:“相對于其他更為安全或穩妥的文體,相對于種種更具有外在形式結構和體制特征的創作樣式以及依附其上的流行趣味,雜文是唯一只能憑借最基本的寫作單位——詞匯和句法——才能夠成立的創作。”(第791頁)
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推敲張旭東的論述,便會發現上述印象具有根本的誤導性。例如,在分析《而已集》的“題辭”時,張旭東對于“而已”一詞的細讀不僅沒有將魯迅對該詞的特殊用法還原到某種一般性的“雜文風格”,甚至他的分析表明,魯迅的雜文寫作中那些貌似辨識度極高的措辭和句式,事實上無法得到修辭學或語言學式的總結歸納:
“而已”本是一個虛詞和感嘆語,在魯迅雜文寫作的文體風格環境中卻成為極為具體、復雜和沉重的歷史經驗與情緒體驗的寓言標記。它“記錄”的并非常規意義上的可以名狀的情感(如悲哀、憤怒)或態度(如反感、對抗),而是只能在一種無可名狀或不可表達的狀態下的表達的代替品或“權宜之計”。這正是雜文的風格隱喻,更確切地說,是雜文風格的基本方式和最小單位。(第712頁;強調為引者所加)
毋須多言,“而已”一詞的上述用法,很大程度上僅僅適用于《而已集》乃至其“題辭”,因為魯迅并沒有在自己的雜文寫作中為“而已”一詞賦予某種一以貫之的特殊含義。在這個意義上,“雜文風格的基本方式和最小單位”與其說是我們進入和分析雜文的一個確定和給定的“入口”,不如說是有待我們通過闡釋而發明的一個又一個“寓言標記”。然而,筆者想強調的是,在張旭東的論述中,這并不意味著對于雜文的細讀完全取決于讀者任意而武斷的闡釋決斷;相反,在作者看來,凝結在雜文的基本形式和表述中的這種“寓言”性質,恰恰是雜文如其所是地(“照直寫”)銘刻、記錄和表達“外部”的一個必然的側面:
“照直寫”也是雜文的基本原則;它當然不是字面上那么簡單,而是一個嚴密、緊張、帶有“預應力”效果的新文學形式革命范疇內的技巧、風格和審美系統。“照直寫”也是寫作倫理和作者的自我要求,帶有道德、政治和審美上的危險性,因此同雜文形式和風格所包含的寓言性質高度契合。(第590~591頁)
具體而言,這里的“寓言性質”同時又包含上文已經反復提及的兩個維度:一個維度是生命在自我持存意義上的自我主張、自我表達,因而我們始終能夠從這些針砭時弊的文字中讀出“一種肯定當下的結構性的力量和正面價值”(第567頁);另一個維度則是對于潛在的集體性的訴求和呼喚,是個體性表達和共同體的“社會歷史語法和政治語法”之間的暗合,因而我們始終能夠將雜文針對當下情境的直接回應理解為“民族寓言”(杰姆遜語)式的創作。
不過,如果雜文的這種寓言性質無法被還原為任何一個特定的句式、措辭、語詞或句法,正如沒有哪個語詞(包括“而已”)自然地屬于雜文或“純文學”(甚或“非文學”),那么我們仍然無法從根本上繞開“闡釋者的任意性”這個簡單卻關鍵的指責。事實上,張旭東在《雜文的自覺》中試圖從兩個方向上回應這個問題,而筆者認為,正是這兩個貌似互補的方向,最終構成了全書的一個內在困境。
一方面,張旭東通過強調序跋文的重要性,從而強調“編集”這一動作的重要性,試圖在“雜文集”的層面上為本質上突破任何既有邊界的雜文寫作框定一個人為的、可辨認的“邊界”。例如,關于序跋文的重要性,張旭東寫道:
序跋文通過自身對文集整體的賦形能力,通過雜文文體內部的敘事性與自我觀照,把單篇寫作從“即時”、“應時”和“攻守”態勢的偶然性中提升為具有更復雜綿長的象征和寓言意義的“文章”。無論這些單篇文字如何鑲嵌在雜感、時評、聲明、記述、筆墨官司、個人恩怨和意氣之爭的具體情境中,在由序跋文所確定的詩學高度和整體性中,它們都變成了一部更大、更完整、更具有審美和歷史意味的作品的組成部分。(第705~706頁)
而在另一個段落中,“編集”的意義則得到了如下闡釋:
雜文“文章”和結集行為將這些零碎的、重復循環的片段固定、凝聚在文學本體論和審美復雜性的總體層面,雜文風格空間至此方宣告完成。(第592頁)
毋須多言,在關于雜文的既有研究中,作出類似主張和強調的研究 者并不在少數;畢竟,顯而易見,恰恰是“雜文集”這個或多或少在呈現方式上非常直觀而確定的說法,通過巧妙地回避或取消“什么是‘雜文’”這一棘手問題,從而在圖書目錄分類的操作層面上為魯迅的眾多雜文寫作找到了一個不太恰當,卻也并不危及既有分類秩序的位置。同樣地,正是因為“雜文集”這一命名,雜文所涉及的闡釋的任意性危險,得以被規避在一個提前框定了的范圍內。由此產生的一個再明顯不過的結果便是,哪怕是對文學一無所知的讀者,也能準確地依照魯迅的自我定位而將(例如)《華蓋集》里的文章理解為雜文。盡管張旭東的論述與迄今為止的許多研究相比更為精致和準確,但在涉及單篇雜文與“雜文集”之關系的問題上,可以說仍然處在既有研究的延長線上。
另一方面,不同于“雜文集”在書籍形式上為雜文進行的框定,張旭東試圖從另一個方向回應“闡釋的任意性”的問題。從結論上說,第二種回應或許可以被概括為雜文的“自我框定”。讓我們重復一下先前的問題:如果不存在一個穩定的外在形式標記,究竟如何判斷一個句子、句法、語詞、修辭乃至一個語段是否屬于雜文?對此,張旭東的回答是:歸根結底無法判斷也無須判斷,這是因為——如我們已經反復看到的那樣——雜文作為生命自我持存的自我表達和對于外部刺激的直接回應,在書寫的最低限度上形成了自律的文學空間,同時也將自己擴展和滲透到一切“純文學”的文類那里。例如,張旭東寫道:
自覺的雜文的出現并不表現為魯迅寫作在某一特殊文體上的單科獨進,更不是魯迅文學生產的放棄、退縮和自我設限;而恰恰是一種吸收、涵蓋其他文類文體和樣式的總體性“解決方案”。這個“解決”(solution)既是對個人境遇、現實危機和外部挑戰的具體應對和回復,更是文學藝術形式史(formal history)內部及其“范式變革”意義上的“處理”和“安置”。(第672頁)
作為一種“總體性‘解決方案’”,雜文無法也無須在形式外觀上區別于其他文類,因為它是可以“吸收、涵蓋其他文類文體和樣式”同時卻不受制于后者的極其靈活的書寫,它是一種非文類的文類、無文體的文體。在《雜文的自覺》中,張旭東多次將雜文的這種性質稱為“雜文的畫框”或“雜文框架”(比較第212、530、574頁)。需要注意,作為“畫框”的雜文截然不同于被“雜文集”所框定意義上的雜文:如果說后者為諸多單篇雜文劃定了一個人為的邊界和形式,那么作為“畫框”的雜文、“自我框定”意義上的雜文,根本而言就是沒有形式的。歸根結底,什么是“雜文的畫框”?
盡管作者沒有直接在書中涉及,但“畫框”一詞以及它在上下文中的用法,無疑讓我們想到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分析康德《判斷力批判》時提取出的關鍵詞“parergon”(裝飾)。畫框作為一種“裝飾”,既不屬于畫作的內部(因為它總是可以與畫作本身分離開來),又不屬于畫作的外部(它將畫作定位在一個確定的展示位置,將畫作和背景區別開來);更重要的是,德里達指出,“裝飾”恰恰表征著畫作本身的空洞性:
“裝飾”銘刻了某種附加物,某種固有領域外部的東西……但是,“裝飾”的超驗外在性逼近、擠壓、推搡、壓迫邊界本身,并且恰恰在下屬意義上介入到內部之中,即內部是缺失的。內部缺失了某種東西,內部缺少某種東西。由于理性“意識到自己無法滿足自己的道德需求”,理性就不得不訴諸“裝飾”、恩典、神秘、奇跡。理性需要增補性的操作。1Jacques Derrida, The Truth in Painting,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Ian McLeo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56.
同樣地,可以說“雜文的畫框”似乎僅僅為具體文本所表達的內容——它的敘事、抒情、修辭、句式等——添加了某種“作者范兒”(我們記得,“writerly”一詞在《雜文的自覺》中反復出現),但恰恰是這種接近“零度寫作”的、處于“文學”的邊界或“最低限度”處的附加性的“畫框”,改變了文學內容層面的地貌、強度和能量。但是,不同于畫作的“畫框”,“雜文的畫框”可以是一個虛詞、一個重復、一個句式、一個修辭、一段引文,同時也可以是序跋文或“雜文集”;也就是說,立足于作為“畫框”的雜文,那么“編集”意義上的“框定”行為也將消解在雜文的無形式的撒播狀態之中。因此,一旦我們意識到“雜文”作為“畫框”為任何一種敘事、表述、修辭帶來的爆發力和自由度,所謂“闡釋的任意性”的質疑,抑或“什么是雜文”的提問,都僅僅是提問者仍然囿于“本體/裝飾”“固有之物/附加物”“內部/外部”等僵化的二元對立機制內部的表現。
不同于序跋文或“雜文集”,雜文的“自我框定”事實上并不框定任何東西——“雜文的畫框”的說法并不是對于雜文之“編集”的補充說明;毋寧說,歸根結底,所謂“雜文的畫框”僅僅是雜文的文學本體論強度的另一個名稱。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當張旭東將這一論述推到極致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全書核心論述中的一個內在困境。例如,讓我們比較一下書中的下述兩句論斷:
魯迅所有的創作在一定程度或某種意義上都是雜文。(第19頁;強調為引者所加)
在批評論辯的有時候是必要的“過度表述”上,可以說魯迅所有的文字……都是雜文。(第645頁)
并不夸張地說,隨著論述的推進,作者對于將魯迅的所有創作都等同于雜文這一激進論斷的保留和猶豫逐漸消失了。盡管在后一句引文中,張旭東謹慎地將這一論斷限定為“必要的‘過度表述’”,然而,如果我們補足這句話所在的上下文,便不難發現,它非但不是某種“過度表述”,甚至在作者的論述中是一個關于雜文的再恰切不過的表述:
我們不妨把魯迅的小說、散文詩、舊體詩、譯作、書信、日記和文學史研究都看作魯迅雜文的一種外延,即這種源頭性寫作方式的準備、操演、游戲、越界實驗和繁復化。換句話說,它們都可以被看作魯迅雜文的非常態,是那種本質性句法、語氣、文體和風格的間歇、運用、自我模仿或有意的過度表現。……在批評論辯的有時候是必要的“過度表述”上,可以說魯迅所有的文字……都是雜文。(第645頁)
在這段話中,“非常態”一詞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哪怕僅僅是因為,作者在書中多次援引德國法學家施米特對于“例外狀態”的論述表明,恰恰是“非常態”(如“雜文”)能幫助我們認識什么是“常態”和“秩序”(如“文學”)。眾所周知,在后者看來,常規狀態什么都說明不了,而“例外”則可以說明一切。在這個意義上,不妨可以說,恰恰是作為“非常態”或“例外”的譯作、書信、日記和文學史研究等——德里達提醒我們,“parergon”的一層意思便是“非常規”或“例外”1Jacques Derrida, The Truth in Painting,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Ian McLeod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58.——突出地顯示了雜文的性質。而一旦我們將魯迅的譯作、書信乃至日記都歸入雜文,那么確乎可以在字面意思上(而不是在“必要的‘過度表述’”的意義上)斷言,“魯迅所有的文字都是雜文”。
然而,如果我們真的走得如此之遠,以至于試圖從魯迅的日記中辨識雜文的“寓言標記”,那么作者在引言部分給出的一個根本承諾,似乎就永遠無法得到滿足:“魯迅留給我們的文字并不都是文學,但在魯迅文字、文本和著作內部做出文學性和非文學性的區分和判斷,本是文學批評和美學批判的基本工作。”(第8頁)這個指向文學本體論的內在規定性的重要任務,似乎最終將不得不消解在撒播式的、彌漫性的“雜文的框架”之中。